 教研
教研  语文教学之友 2010年第8期
ID: 147247
语文教学之友 2010年第8期
ID: 147247
“内奸”项伯先生有点冤
◇ 佚名
《鸿门宴》是高中传统篇目,这一段故事其实是《史记·项羽本纪》的一个片段,把这一段文字称为此名,是因编写教材的需要。现在,不管是哪个版本的高中语文教科书,都会编选这一段,因为一是这一事件在楚汉战争中有着重要地位,二是其确实写得情节跌宕起伏,人物栩栩如生,语言精当传神,为学生学习的最佳范本。鸿门宴上,项羽没有把刘邦杀掉,以致留下后患,遗恨千古。人们在扼腕感叹之余,除了批评项羽头脑简单、目光短浅、优柔寡断、沽名钓誉等缺点外,更对项伯心甘情愿做敌人的奸细一事口诛笔伐,甚至有人认为项羽的江山就是因为项伯这个内奸泄密才被刘邦抢去的。但是,对于项伯为什么要告密,却少有人去认真探寻背后所有的原因——也有人认为《史记》上写得明明白白,“项伯杀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来告良”,没有探究的必要了。
项伯到底是什么人?《史记》中明确写着:“楚左尹项伯者,项羽季父也。”“左尹”即左令尹,是仅次于令尹的国家军政长官,可见是高级别官员;“季父”就是叔父,又可见是项羽的亲人。从鸿门宴上“项王项伯东向坐”——与项羽并坐尊位(那时东向为尊),可见其在楚军中的地位,也表明他深得项羽的敬重。既然如此,他不为侄子项羽着想,而心甘情愿做内奸,这无论如何都是说不通的。
其实,《史记》内容已经告诉我们,在当时的情况下,项伯这样做也应该有其合理性的:司马迁在此介绍张良情况时,是这样写的“张良是时从沛公。”要特别注意,这里用的是“从”而不是“属”字;在项伯“欲呼张良与俱去,‘毋从俱死也’”时,张良也明确告之(也是告诉我们):“臣为韩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义……”什么意思?《史记·留侯世家》中有这么几段文字,我们先来看一下:
1. 陈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余人。景驹自立为楚假王,在留。良欲往从之,道遇沛公……遂属焉。沛公拜良为厩将。良数以《太公兵法》说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从之,不去见景驹……
2. 及沛公之薛……项梁使良求韩成,立以为韩王。以良为韩申徒,与韩王将千余人西略韩地。沛公之从雒阳南出 辕,良引兵从沛公。
3. 汉元年正月,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王之国,良送至褒中,遣良归韩……乃使良还。行,烧绝栈道。
4. 项王竟不肯遣韩王,乃以为侯,又杀之彭城。良亡,间行归汉王,汉王已还定三秦矣……
《汉书》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从第1段文字看,这是张良才起兵的时候,有自己的一支小队伍,“道遇沛公”便“属焉”,成为了沛公的“厩将”,这时的张良是沛公的部下,是上下级关系。从第2段看,后来形势的发展,张良变为了“义帝”楚王心的部属,在名义上应该是与刘邦平等的了,并且受当时实际掌权者项梁的委派,找到韩国的后代——韩公子衡阳君“成”(张良本身就是韩国大臣的后裔),韩成被义帝(实际上是项梁)立为韩王后,张良一变而成为了韩王的申徒(相国),并与韩王一起带兵攻占韩地,直到沛公“从雒阳南出辕”的时候,张良才又“引兵从沛公”,这时他与沛公的关系不再是“属”而是“从”了。第3段文字内容写的是,到项羽分封诸王(汉元年)后,汉王要到封地巴蜀上任的时候,张良还去送他,汉王刘邦听从张良建议,烧绝栈道,同时也把张良送回到韩王成的身边去。最后一段文字,后来项羽因不放心韩王,先是不让他归回封地,再降他为“侯”爵,最后“杀之(韩王成)于彭城”,这时的张良走投无路,才偷偷地逃跑(“间行”)到刘邦处(“归汉”)。
也就是说,在刘邦还定三秦(汉三年)之前,张良在刘邦那里,除前期很短的一段时间外,其余时间,身份一直是比较自由的客卿,与刘邦是属于关系比较松散的主客关系,而不是关系严格的上下级关系,司马迁用词非常准确,是“从沛公”而不是“属沛公”,直到张良名义上的老板韩王成被项羽杀了之后,张良在名义上“无枝可依”,才偷跑到刘邦那里——“归汉”,成为刘邦名副其实的部下。
现在再回过头来说项伯。在鸿门宴事件之前,作为项羽部队高级官员的他,一直与义帝、项羽、沛公、韩王、张良这些人共事,非常清楚张良与刘邦的这种主客关系,也当然明白张良在刘邦部队里是随时可以离开(愿不愿意又是另一回事)而不会受到“纪律处分”的情形。作为军人的他,自然也会明白“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这件事是高度的机密,但在项伯先生的头脑中,只想到张良是客卿,有来去的自由,会在生死关头选择离开,绝对没有想到张良与刘邦的关系是如此紧密。也正可能是基于这样的想法,为搭救曾对自己有救命之恩的张良,他才做出了“夜驰之沛公军,私见张良,具告以事,欲呼张良与俱去”的蠢事出来。至少在这个时候,我们还不能说项伯是有意泄密给敌人的——“沛公有‘王关中之心’,是项羽的敌人,但张良没有这种想法,张良不是敌人”。头脑有些简单的项伯肯定是这样想的,这时的项伯严格意义上说应该不是“内奸”,至少在主观想法上不是。至于后来被张良利用,受刘邦“兄事之”、“祝寿”、“约为婚姻”种种手段的蒙骗,一步一步走上“内奸”道路,那是他自己先前没有预料到的。说他有意为奸,那也确实有点冤枉他了。
自此,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头脑相当简单的项伯先生,只是为了旧时朋友,确实没有做“内奸”的主观想法,因为性格等多方面的原因,客观上中了计,不知不觉中成为了“内奸”!
(作者单位:江门市外海中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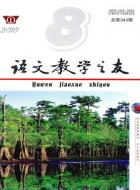
- 语文教师“十二精” / 王开荣
- 流行文化影响下的经典文本教学 / 宋向东
- 打开禁锢学生的枷锁 / 左志云
- 语文教学激趣七法 / 王维政
- 新诗教学“新”路之探寻 / 王兆平
- 集思广益 有“备”无患 / 李 勇 王庆艳
- 发挥追问功能 拓展课堂空间 / 李会昌 潘 虹 金玲娇 汪微霞
- 新课程下的板书亦应有“板”有“眼” / 张连生
- 《风筝》中的文化冲突 / 杜广运
- 例说品味语言的方法 / 胡维中
- 短文也需深教 / 卢雪飞
- 巧用多元评价提高课外名著阅读效果 / 钱凌梓
- 于细微处品妙文 / 谢晓霞
- 文言意动句 翻译方法摭谈 / 张元多
- 似水胜酒,古味虽淡醇不薄 / 李淑红
- 一样的情思 异样的表述 / 傅兆梓
- 南风知我意 吹梦到西洲 / 唐弋菱
- 小议“紫色的灵魂” / 商艳玲
- 微言大义 不平则鸣 / 李旭东
- 运用合作学习实现读写结合 / 赵振翔
- 鲁迅小说中的“豆子情结” / 张正红
- 权谋与文才 / 牛庆钊
- “冤”在何处 / 高 青
- “内奸”项伯先生有点冤 / 佚名
- 一个“笑”字费思量 / 田永生
- 痛苦与抉择的重奏 / 蓝建龙
- 新课程背景下的中学作文教学现状及思考 / 张达富
- 工业时代的“骑士”一曲人性的挽歌 / 张玉连
- “5分钟片段作文创作”的教学策略与思考 / 许 可 邓 荔
- “寻声暗问弹者谁,琵琶声停欲语迟”新释及启示 / 王长路
- 如何缩小 作文“话题” / 杨元保 刘建春
- 成语“山清水秀”“清”字释疑 / 常志伟
- 衣带渐宽终不悔 / 顾霞光
- 随堂练笔:提高作文教学效果的关键 / 龚德伟
- 浅谈议论文中心论点的把握 / 郭万军
- 灵动的翅膀与特定的星空 / 赵立东
- 巧用提问法解答新闻概括题 / 王淑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