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文学教育·中旬版 2010年第9期
ID: 153629
文学教育·中旬版 2010年第9期
ID: 153629
你赋予了小说文本以力量
◇ 姜广平
一
姜广平(以下简称姜):好像你也是一开始写诗的。后来为什么不写诗了?
葛水平:(以下简称葛)如果用一种文本来表达青春年少,我认为是诗歌。我写诗与我的年少有关,我在年少时目力所及处看到的都是山,我的梦越过了山那边展开了的辽阔田地。你知道的,所有的梦都是跳跃的,跳跃的飞得满天空,当我用满含梦想的语句表达对这个世界的喜爱时,我就是诗人。后来我走出了大山,走到县城去读书,去学戏。我跟着一个小剧团常年奔波在乡村演戏,但一直没有唱过主角,跑龙套。演出时,我在台上一站就是很长时间,脑仁子里想的依旧是诗,都是些梦想的语言。时间一久,面对现实,思想似乎成熟了许多,觉得诗歌不能涵盖我对梦想实现不了的不满了,我就不想写诗了,转而开始写散文,简单到觉得散文的字多,多一个字就能够多表述我一份思想,不写诗是因为我的思想沉重了。
姜:我有时候也是觉得多些字好。其实满不是这么回事儿。写诗对你的小说有哪些帮助?
葛:对我小说语言有帮助。是自觉不自觉的帮助,经常地,不经意间,那些埋伏在心里的诗性的语言就抬头了,我能感觉到它们温暖而尖锐地在往上拱。
姜:为什么后来选择了小说?是不是小说更适合你更与你“般配”?
葛:后来写小说,与经历有关,也与朋友的“劝说”有关。我写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散文,由于经历过较多的人和事,听满了看多了,所写散文里就有了故事,故事里还有情节和细节,常常就觉得收不住手。有时候一个生活细节就能够使我生发出无限的感慨来,挥之不去,意犹未尽。我也只好用“系列”的形式去表述。山西有一位作家朋友就对我说,你的许多散文,实际上已具备了小说的种种因素,远不是散文所能承载了的。就规劝我写写小说吧。我就听了他的话,尝试着写了两个小说,就是《甩鞭》和《地气》,写的蛮顺手的。我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好的反响。小说出来后,有人说,你最好的是小说,散文次之,诗歌次次之。也许就像你说的“小说更适合你更与你般配”。不过,我现在真正的是觉得写小说难了,人生悲苦,一个又一个岁月,我能写出多少故事?小说给我的唯一“念系”是,它与我的生命相关,它让我的内心充满虔敬,而且幸福。
姜:一个作家可能命定跟一种文体般配。上次跟作家朱辉聊天,他甚至认为,一个小说家,其实命定地跟篇幅般配。有的作家天生能写长篇,有的作家拿不起长篇。有的作家,中短篇的感觉更好。我想,应该是这样的。
这让我想起你的叙事语言。我觉得你的叙事语言是最为粗朴的,原汁原味儿的,甚至带有那片土地最原始的味道。这种语言,充满了一个健全生命的强大底气与活力。没有献媚取宠,没有搔首弄姿,没有张扬跋扈,也没有无病呻吟。我想,如果没有对生活的最为本质的贴近,可能难以选择到那种语言。从某种本质上讲,你一出道,就显示出了与沈从文等作家的接近与神似。有人以赵树理来与你比较,我觉得赵树理的那种语言显然有力不能逮的地方。至少,赵树理努力在社会化方向上的努力,使他的语言受到了很大的戕害。
葛:我喜欢沈从文的文章,2005年我随中国作协访问团重走长征路到过湖南凤凰。凤凰在我眼里是阴柔的,也是婉约的。在走近凤凰的一刹那间,我的心剧烈跳动,我一直想看到凤凰,看到沈先生生活过的凤凰。我走进凤凰时,我渴望神化的灵迹和宗教的幻境,我甚至渴望我的语言能沾了沈先生的灵气。当我从凤凰走出来的时候,我知道,是一条水吸着湘西女儿的香气,沁了沈先生的心田,才有了他文章中的满目青葱。地域给了一个作家灵敏的心目和灵敏的感悟,我如果真能够接近沈先生,那是我前世的造化。赵树理是一个高度,而这个高度对我来说是永远的。赵树理生活的那个时代有无法克服的灾难袭击着社会,他的社会化的语言在那个时代是可以拯救民众精神苦难的。文学创作一直以来或者说永远都有一个广阔的社会背景和政治背景,那个时代出现的赵树理,他就是一个高度,后人无法超越。
姜:我觉得这样看赵树理可能是一个角度。但这个角度,从文学精神上讲,可能就不那么纯粹。
忍不住想问一句,你那种独特的语感与语言是如何寻得的?
葛:是从自然中寻得的。广大世间,最有魅惑力的是人,是自然。与人交往,仔细地去听他(她)讲话,每个人的语言都有闪光点,当然,一定要到乡间去,乡村的语言就像雨后那些红石板铺就的屋顶,朴拙哲理、光亮夺目。而与大自然相融,你会觉得心境澄然,五内俱清,你能获得一种奇异的灵气。
姜:你不承认自己是“练家子”,但一个作家的基本训练还是有的。在你的小说写出如此境界之前,你的小说写作训练总该还是有的。
葛:我不知道该怎么来回答这个问题。如果要回答,我还是要说,我不是“练家子”。我的小说的基本训练,更多是来自我的经历。我小学毕业去学戏剧,戏剧给了我最初的文学启蒙,舞台上的人物命运时常牵动着我的心,而行云流水般的念白唱词总能给我美好的感觉。我父亲是个工人,曾私造土枪打猎,夜晚举着手电筒偷邻村人家的鸡,甚至从人家茅厕上偷夜壶装销胺炸鱼,他还会点阴阳八卦。我们家就我一个女儿,他把我当假小子使唤,我是他身后的影子,他做的那些事情有时候我也做。我父亲因为这些事情老是被“请”进派出所,我怀里揣着钱一次一次去赎他。最后一次因为和人吵闹我也被“请”进派出所,而我那时已经三十岁了。我父亲出来后对我说,他不计划再进去了。听了这句话我热泪长流。我母亲是个小学教员,给我最贴近记忆的影响是,两年就要调动一次,赶着驴车拉着自己的家当调往另一个村庄,那些情景历历在目,我什么时候想起来什么时候都会激动。经见的事情多了,我就想把它诉诸文字。我没有读过关于小说训练的书,就是凭感觉。所以我想说,是生活训练了我。
姜:怪不得你的小说好像都透着一股子力道。像《地气》、《狗狗狗》和《空地》,都有着一种力量。这些力量,有的是小说中的人物,像王福顺、秋和张保红。有的就是小说文本的力量。当然,文本的力量,也是人物给予的。
葛:我一直以来认为小说给人的张力就是要让读过的人回味很久,这一点也许很难,我认为我是在努力朝着这个方向去做的。小说创作是“私人的”,原本对一个故事也就是知道一鳞半爪,把这个要写的故事“塑造”成一个有历史性或社会性的“全人”,供读者思量和拷问,就必须学会组织起这个故事的血肉,更要紧的是故事的骨头。《地气》中的王福顺、《狗狗狗》中的秋和以及《空地》中的张保红,都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这些人物本身就有一股子力量,我只不过把他们身上有代表性的特征表现出来而已。我的出生地是大山,可以说大山赋予了表现的力量。
姜:特别是那个秋,非常有力道,想以自然的繁殖获得一种生生不息的对抗的力量。
葛:当一个凡俗的女人用她自己的爱和恨来回报这个世界的爱和恨时,我想,她的唯一的方式是生育。酷似花,由盛而衰,而死,献出全部血肉,只为留下后代,而不朽的后代就是她全部痛与苦的未来!
姜:有人在谈《甩鞭》时,讲:“王引兰非要让麻五买下一块地种油菜,为的是在春天让她看油菜花开。这样,在女人对男人的支配之下,地主与土地的关系居然变成了一种美的贸易。这应该不会是当时历史中的真实图景。这是女性作者自身愿望的一种投射。”撇开女性投射这一点不谈,我觉得现在仍然还有人以阶级论的视角来看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有点荒谬。麻五为了王引兰,愿意切断他自己所建立起来的城乡贸易关系与利益,这本来就不能是一种阶级性而只是一种人性啊!
葛:对啊,阶段斗争也有它人性的东西在里面,人性中最美好的东西是“爱”,最讨厌的东西是“利益”。任何一场斗争的起因都有利益在里面作怪,人心深处既有明媚的底色,也有低级的趣味,我就是想写一个女人一生的底色应该是像油菜花般明丽,女人的爱不是简单的俗世中的柴米油盐,有精神上的,放在那样一场历史中,有油菜花田般的底色做衬,后来的痛苦都淡了。
姜:是啊,本来就是每一个女人都不简单,无论她来自城市还是来自乡村。
《甩鞭》无疑是一篇力作。但有人讲《喊山》不及《甩鞭》,不知你如何看。我觉得《喊山》的力道,反而比“甩鞭”来得实沉些。毕竟,“甩鞭”跟主体情节并没有浑然一体。也许,我可能没有洞穿“甩鞭”的深沉的象征意义。所以,同样有了声音,“甩鞭”可能好看,但“喊山”不但要看,还得要听。我觉得陈福民的这句评论实在是好。《喊山》本质上是一个关于声音的故事,是在沉默中爆发的故事。
葛:甩鞭是太行山年节的一个喜庆活动。乡下人那时候买不起鞭炮,过年就辫一个很长的牛皮鞭子,到村庄的山尖上甩,身旁燃了明火。鞭声生生从天空直铺天边,凝成千百年一气,滚滚滔滔,鞭斥天宇的响彻,能把人的心吞得干干净净。现在,它,绝了。甩“鞭”贯穿了整个小说,是我想用它来唤醒冰冻的土地,唤醒一个女人生命中最美好的情感,或者说爱情。而《喊山》的声音,我是想写千百年来时间去得不言不语无声无息,而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女性,尤其是农村女性们的抗争走到现在,依旧给岁月留下的是一双黑色的眼睛。小说的面貌只能由小说来决定,就像千万种树所以为树,因为是树,千万种石所以为石,因为是石。
姜:关于《甩鞭》,我还读到了一种乡村政治的模式。我曾经与阎连科、毕飞宇等作家都聊到过,中国几千年的农业社会,政治格局其实是不大气的;而乡村,则是无真正的政治可言的。像铁孩,应该是乡村政治中的正面人物吧,然而,其人性之恶、无法在诱惑面前转身的阴暗,又无法与正面人物联系得起来。在这里,乡村政治,只是挑战诱惑或面对诱惑的方式。
葛:我同意你这句话:“乡村,则是无政治可言的。”乡村的政治是盲动的,是嫉妒、是私欲、是压抑者在他人身体上的爆发!乡村本来是宁静的,仿佛可以听到空气停留下来,但这一种宁静一旦被搅乱了,他们便出现了无措的混乱,人的思维一旦混乱了,想想看,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乡村政治的不大气处是因为政治的不纯粹,政治的不纯粹给简单的人们带来了精神上的幻觉,没有一个人面对诱惑不心动的,可纯粹的政治又在哪里?政治是一件披给裸体人身上没有补丁的外衣,披上外衣说出话来,每一句都字正腔圆。
姜:很多人注意到了你的女性视角。不知什么原因,我的阅读感觉始终无法建立起这样的价值视角来。是不是我们迟钝呢?我觉得你的所有作品,都不由女性视角来统摄的。很多时候,我们论定作家的时候,大概本不应该以“男”“女”来界定。因为这是最简单同时也可能是最笨拙的界定。整个《喊山》这部书里的所有作品,都无法用这种性别视域来界定。我倒宁愿意相信一句话:“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这里的“天”就是自然。我读你的作品,总觉得是自然假你之手传达出一种质地非常浑朴的文本。我觉得除了《陷入大漠的月亮》偶尔暴露出女性的感觉,那可能是实在藏不住了,写出了女性的失落与幽怨,善良与无奈,当然,还有率真与不得不掩蔽的率真。
葛:我的名字有点中性,许多人见到我后说,你怎么会是一个女人?《上海文学》曾经发过我一组散文,介绍作者时也写了:“葛水平,男,作家,现居山西长治”。我不知道是名字的问题,还是作品的问题,还是我这个人的问题。我是一个女性,肯定!《甩鞭》中王引兰喜欢油菜花,是我喜欢油菜花;《甩鞭》中王引兰喜欢甩鞭,也是我喜欢甩鞭。油菜花——甩鞭,我认为是最能体现我性格的一动一静两种物体。我的文字特点与我写作的神情姿态也决定了我喜欢两个作家的文章,沈从文、陈忠实。你说的对,《陷入大漠的月亮》中确实有我的影子。
姜:《陷入大漠的月亮》在风格上与其他作品迥异,这是一种想尝试新的写法的努力吗?
葛:可以说,是。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想写城市的生活,我虽然在城市里住了很多年,但是,我对城市一直没有感觉。乡村,只要我路过,我就能闻到它的气。
二
姜:《天殇》里将王家的凋零和上官芳的一生都归于“自然”的法则,这是不是就是天殇?或者说,你在展示命运的无法掌控?
葛:我从沁河岸边寻觅到这个故事时,她的存在只是一个影子,是一个美丽的背影,反过来的脸是一张狰狞恐怖的脸,我想这么好的一个女人怎么就这样儿的被岁月淘洗得面目全非了呢?一刻也不停,在地面上奔跑的风无痛无痒地吹过,我的心逐渐深重,我想,我做为一个把文字拼凑成故事的人,有义务给她一个完整的生,完整的善,完整的恶,完整的死。我写的是一个女匪。女匪也是人。我赋予了她人性。她必须生长在一条河边。水比之于陆地上的一切都更具有“命脉”的意义。水是生命的基本元素,善是她的最初也是她的最后。中国历史上的土匪,纵横八千里各色各种,用英国的菲尔·别林斯里的话:土匪有两种“偶尔为之者”和“职业土匪”来说,她什么也不是,她是血亲复仇。有一点我需要说明,我之所以有勇气把她写下来,是因为我始终相信每一种恶的背后都有善的存在,虽是旧事,我却很想重提。叫《天殇》,我只是想展示命运的无法掌控。
姜:当然,有意思的是,这里又是以一个女性上官芳来终结了王家家族的世仇。这可能又给很多读者与评论家们带来了难度:他们又得给这篇小说戴上女性主义的帽子了。
葛:那是评论家的事。
姜:《浮生》听说是你比较喜欢的作品。我也非常喜欢这部作品。在很多东西面前,人无法看清自己,譬如,唐大熊竟然无法看清唐要发就是自己的真正的后代,还有,在很多东西面前,人也无法真正做一回自己,说好不再弄炸药的,还是弄了。
葛:千百年来,农民在泱泱大国的土地上本分而厚道地生活,就像浮生的尘土。他们依靠一双丈量日月的脚丈量幸福与苦重,他们木讷而勤恳地过日子,两手黄泥,一脸汗水,俯身就地,为了寻找自己生命的土壤,伸向泥土的根系都十分发达,填饱肚不生事,阳光下抖擞着身姿富足地微笑。到了肚子不能够填饱的时候,他们才会想起:活着不生事,那叫活命吗!
太行山实在是太古老了,老到山上的石头挂不住泥土风化成麻石,最薄瘠的地方不长树,连草也不长。村庄挂在山上千姿百态,当空的风霜雨雪走过,农民请它们留下来,给他们的生活添加福气,有时候添加来的福不是福也许是祸,但是,他们已经融入了这种生活记忆所抵达的无法不面对的现实。他们也有他们的理想和虚荣,他们的理想中含有焦虑的目光,他们的虚荣常常是挂在脸上的,靠天吃饭,靠地打粮食。靠天靠地还不是他们心中最好,最好是政策好。有一个好政策,乡间的风俗画看上去就不是虚幻的田园牧歌式了。因为无知和良善,他们像掷出骰子一样抛出了自己的命运,为的是想活着好或者更好!当然,也没有比无知和良善更易于制造残酷的活命了!当你看到他们切实的生存状态,你就会知道他们中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要放弃他们赖以生存、视为生命的土地,远离他曾经日夜厮守的村庄和熟悉的农业,宁愿一切荒芜也要豁出去!
我写《浮生》,既没有美好的开头,也没有美好的结尾。我想做的是用自己的思想、目光、脚步,跟随农民去丈量中国农村的土地,并且让尽可能多的人们知道他们生活的艰辛与愿望,关注他们的生息和修养。毕竟,我们几乎所有的人不出三代都是农民!
姜:这可能仍然可以归结到力量之上。但另一种力量,我则觉得非常可怕,一是《黑口》里的五牛,二是《黑脉》里的许中子。这些人物,可能是你试图表达对当下社会的批判意识。
葛:面对现实,我觉得我活得徒具其形,我甚至批判不起来,我是从事脑力劳动的人,我的脑袋能想像的东西,就算让我把良心坏了,能想像出的也不及现实给我的震惊恐惧。我在《黑脉》和《黑口》里写到了死亡,这是我最不情愿写到的。我一直想让我小说中的人物有一个温暖的气场,然而,当我写到煤,我就无法不面对黑色的恐怖与死亡。山西的煤,曾经繁衍了山西人丰饶的苦难和辉煌,也毁损了暗无天光下的卑微生命。我不想矫情,我也不是时代的代言人,我只是想写:死去的人和出生的人一样善良,它带走的是俗世无比丰富生动的幸福,是活着时的爱!我在报纸上看到死亡是煤矿一个数字,由一到二,由二到三,它所呈现的结果是令人吃惊的大数,最后,又接近与除法,人到最后都成了可怜的零数。一个官员的死亡是拿钱换不来的,一个卑微的人,钱,是唯一解决问题的途径。
姜:而柳腊梅的力量,则可能更多的是出于那种无奈之力。这样的力量体现者还有水仙,在面对违法与守法的悖论时,人只能无奈地首先选择生存,虽然明知这样的生存已经没有任何主动选择的可能。
葛:包括我们自己也是,没有办法不把无奈局限在自己的体内,面对社会上的一些现象,一切,终归只能依仗权力。
姜:当然,在这一方面,米秋水的选择更多地带上了悲剧与毁灭的色彩。
葛:我写《守望》这篇小说时,心里有一种疼痛,那种疼痛是对善良的感叹。善良是这个世界上不容侵犯、平凡得高贵的品质,然而,在许多状态下,善良却往往让一个人进入了临危绝境。我个人认为,对于城市的热爱和忠诚,乡下人是它的气流,但是,乡下人总归是乡下人。
姜:虽然,非常巧合的是,这些重要人物都是女性,然而,我却不想论定你为一个女性主义视角的作家。如果要偷懒的话,倒不妨说是一种对底层的具有悲悯情怀的书写与呈现。
葛:我生活在底层,我周围的人和事激励了我的创作热情,我不去写他们,我不知道写什么才能带给我良心安慰。
姜:所以,你将苦难当作了主题,写出了苦难的蚀人心魄的毁灭性的力量。
葛:如果一个人出生在乡村,童年也在乡村,一辈子乡村都给以饱满的形象。而乡村,任何一个催人落泪的故事,都要在时间的流逝中消失,写小说的人,生长的过程,不是随意地看着过去的日子凋零,而是要在过去的日子里找到活着的人或故去的人对生活某种目的或是境界——虔诚的一面。文字不是无限强化它无限的痛苦、无限的漫长,而是要强化它无限的真诚、无限的善良,社会的进步走到现在是它的真善美,不是假恶丑。从心里上说,我不想将苦难当作我小说的主题。
姜:想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就是一个作家的体验与写作的关系。觉得这里的问题必须要谈一谈。我似乎也没有跟更多的作家谈过。上次跟艾伟谈过一次,但艾伟的回答颇让我尴尬,他觉得这不是一个作家应该提出来的问题。然而,我这次还是想再次提出来。我读你的作品,有一种强烈的感觉,那就是体验与对体验的书写,在一个作家的创作历程中太重要了。一个作家如果不将体验参与到写作中,或者直接地在作品中表达,可能,他的写作便是值得怀疑的。
葛:“写作是一种什么行为?有人说是性行为。否则,只能叫写字。”我不记得是谁说过的这段话,其实已经很说明了问题,体验与对体验的关系,笔在我手中,它未必就听我的,它更多的时候是从大脑中的记忆出发,当读者忽视我作品中具有的特色时,那肯定是我作品中的人物和情感不能结合,因为,我没有这方面的体验,我的叙述让文字苍白。我不知道说明白了没有。
姜:我总觉得一个作家的体验越丰富与到位,他的小说技巧与修辞的意识便可以让步,因而写出来的东西也便越接近于某种艺术的真正品质。
葛:我赞同你的话。
姜:当然,很多作家在体验想象或想象式的体验上,也能以凌空蹈虚的方式达到非常实在的强烈效果,但是,时间一长,文学生命便会呈现出一种萎缩的状态。我在你的有关创作谈里看到过,太行山你一辈子也写不完。我在跟红柯对话时,也非常强烈地感觉到他对新疆的热爱与利用。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你恰恰跟红柯表现出了相同的文学品质,那就是尊重了自身的生活体验。
葛:我首先尊重我生活的这片土壤,它给了我大气、磅礴,给了我厚重,让我一出生就看到了朴素、粗砺的生活本质,而不是简单的明山秀水。其次,我才要尊重我自身的生活体验,人的生活没有多重选择的可能,你是一个谦卑老实、木讷厚道的山里人,上天必定要你对大山亲切。我出生在农村,我的生活体验就在农村,我看到农村人时,我的心情绝好,因此,我写农村人的生活时我不会被憋得头胀脸红,可以说,农村能给我的作品富含鲜活的诗意和人性的深度。的确,太行山是一部大书,我一辈子也读不完,照此而言,我一辈子也写不完。
姜:没有丰富的体验或与这样的体验疏离,就可能产生被悬置的感觉。我觉得这才是一种文学的感觉。你自己也讲过,“被土地和大自然悬离的空茫、焦虑、莫名躁动,引诱了人们想往一种厚实、久远的精神居所。乡村中的玉米地,村庄里的猪马牛羊,大堆大堆的麦秸垛,磨亮的锄把、镰刀、粗瓷碗乃至饱满的麦粒,亦成为小小的精神寓托之所。因为它们着实代表着土地、代表着乡村一种澎湃的生命和强旺的生机。”我是这样理解你的作品文本的力道的。对了,关于晋地风情的描写,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支撑起了你的小说。我想问的是,如果小说中缺少了这些风情描写,应该也是成立的,但有了这样的风情描写,当然,就更具有了硬朗的质地,与生活更其逼近了。但是,我又觉得,以地域特色或地方风情简单地概括了你的小说,又可能是一种草率。
葛:一个作家的作品能够代表了一个地方,能够写活了一个地方,更多的成分是这个地方恩养了这个作家的心性。如果有人说,葛水平的小说就是晋地的。我觉得,那是给我的最高的奖赏。
姜:当然,相关的问题是:在当今女性文学创作中,城市化写作成为一种共同的时尚。你为什么不选择这一路数呢?是有意回避吗?
葛:也不是有意回避,主要是我对城市陌生,我融不进去,我没有绝对的城市生活体验,我对那些真正生活在城市里的作家,是心存敬畏的,从心理上讲也不愿也不敢去与他们抢争地盘,因为我与她们之间有一道地域的沟壑。就算是写城市,我也要拐到乡下来,绕一圈再进城去。我不是有意回避城市化写作,而是觉得自己还没有真正成为一个城市人。
三
姜:我希望将《黑雪球》放到最后来说。这篇小说,毕飞宇早就向我推荐过,要我细细读一读。可我直到最近才将这个中篇读完。读完之后,我很久没有出得来,伍海清被灼伤的男人本性,使我想起茨威格的《象棋的故事》。《黑雪球》中关于性的“事后性”爆发,那种恐惧与灼伤,比起《象棋的故事》中的对“象棋”的恐惧与灼伤更甚,日本人在良平,让一个中国男人有了性的恐惧与疏离,比阉割更加残酷。这里的力量可能是当代小说难以觅得的了。
葛:1937年到1945年让日本人的野心在这场侵华战争中延续了足够的长度,中华民族阔大的土地敞开自己宽厚的胸怀接纳了这帮“亲善”部队。满目青山,因风派生出的满目锦绣,日本人的野心在足够的长度中无端践踏了这般青山这般锦绣。我告诉你,我的故乡,山西沁水山神凹,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地方,日本人找到了。10眼窑洞,三十多口人,死人的头颅在河滩上干裂裂滚动,月余不腐。我祖母说:“日本人杀人要笑,两耳叉的猪耳朵帽子晃得瘆人,一笑一晃,人,就像庄稼一样被割去了一茬。”没有任何缘由,我家族中最本分的五婆被日本人轮奸了。我的本家祖母来不及逃命,日本人的刺刀从她的大裆裤中央刺了进去,来不及再看一眼土窑黄坡,肠子像麻绳一样拽了她的命。凹里夏翠莲被轮奸后的小肚子像地锅,她用指甲把自己的脸抓成了马蜂窝,羞辱地嚼烂自己的舌头死了。以往人们可以从清晨的空气中吸吮一点湿润就可以存活的日子一去不返,“土地死了”。一个存活下来的男人,经历了这场战争他不可能像男人一样活着了。有人曾经和我说过,你写日本人发动的侵华战争,为什么不把日本人写得“好”一些?有人性一些?我告诉他,我听到的,有记载的都是日本人在太行山上犯下的杀人罪行,我善不起来,也人性不起来。在写这篇小说时,我尽量压着性子,并告戒自己:把狗日的日本人写得善一些吧。
姜:听你这一说,我流泪满面。真的很难明白,日本人的人性为什么会在那样的年代有了那样的狗胆。可现在,还在参拜靖国神社,还在对慰安妇的问题尽力回避,还在对南京大屠杀不肯面对。也许,这时我只能祈求神的力量,让这个丑恶的民族遭遇报应。《道格拉斯/china》显然也有这方面的努力意识,但是展示得没有《黑雪球》充分。毕竟,这里没有出现恐惧中的日本鬼子。
葛:实际上作品中日本鬼子出现了,而且也给这个平静的小山村带来了极度的恐惧。关于战争题材,我已写过三篇,即《狗狗狗》、《黑雪球》及《道格拉斯/china》,我不想重复自己,也尽可能克制自己的情绪。你可以对照一下,这三篇东西所表现的内涵是不尽相同的,《狗狗狗》表现的是战争对女性的戕害,在秋的身上,我赋予了中国女性极致的美;《黑雪球》表现的是战争对男性精神和生理的摧残,这种摧残会使一个男人丧失作为一个男人的本能,终生背负创伤的烙印,同时还想表达面对异族侵略,各种势力的角逐、分化、融合及至同仇敌忾;而《道格拉斯/china》则表现普通的中国民众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中,能够舍身忘死,以最淳朴的感情包容、接纳异邦朋友。我始终将战争中的人性放在重要的位置,尽可能淡化战争场面。我不想把过多的血腥展示给读者。
姜:你不想过多的展示,然而,事实上伍海清那种人性崩溃与悲剧,比起任何酷烈的战争更让人不敢面对。
葛:这就是我努力所想要展现的人性的深度,人性中最本质的东西往往是本性的扭曲,一个正常人变的不正常了,他(她)的行为是人们意想不到的。秋和伍海清近乎“变态”的行为,是人性极度压抑的状态。
姜:再接下来,还是得问一些具有规定性的问题:中外作家中,谁对你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葛:决定性的影响?你提的这个问题似乎也太绝对了吧。就我个人而言,只要是好的小说都让我心神不宁,也都能够对我产生影响。优秀的作家总有其优秀的地方,他们都是我的榜样,但没有对我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姜:山西作家里,你最服膺哪位作家?
葛:比我优秀的我都服膺。
姜:你对自己的作品如何评价?或者说,当很多人在赞扬你的小说作品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你小说的问题在哪里?
葛:我每篇东西写得都很用心,也很努力,每发表一篇,我都会听取多方面的意见,尤其是批评意见。我小说中的问题也很多,比如在叙事过程中,人物的逻辑关系不太明晰;有时候由于主观情绪的原因,对故事缺乏一定的控制力;另外,在语言表述上有口语(方言)和书面语杂糅等问题。
姜:可能方言与普通话的问题始终是一个问题。很多作家都得面对这样的问题。这可也是一个难以处理好的问题。毕竟纯粹的方言在失去了地域背景的支撑以后,那种原始之美,已经很难表现了。
今后的创作,在题材的选择上会不会作一些其他的选择?是不是还想写山西农村,或者还是写煤矿?
葛:会有其他选择,比如城市题材,但是,农村和煤矿不会丢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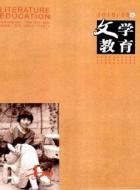
- 你赋予了小说文本以力量 / 姜广平
- 《史记》神话研究 / 李瑞仙
- 朝鲜李瀷与清代赵翼对李白诗歌的批评 / 王 成
- 浅析伍尔夫小说《到灯塔去》中的电影表现技巧 / 冯翠娟
- 试论杜甫《秋兴八首》的结构特点 / 于 莉
- 《赵氏孤儿》元明刊本比较谈 / 朱丽霞
- 浅析《西厢记》的人物形象 / 刘 精
- 从新历史主义角度解读《艾凡赫》中汪巴人物形象 / 郭 平
- 评《荆棘鸟》中梅吉与拉尔夫的爱情 / 宋玲玲
- 中美研究生跨文化差异及留学生心理问题分析 / 罗 坚 杨孟斌
- 浅谈朱自清散文的抒情风格 / 程 珏
- 民办高职院校后进生转化问题探讨 / 金剑青 顾佳滨
- 嵇康《声无哀乐论》之管窥 / 胡潆哥
- 职校生心理健康状况透视 / 王存凤
- 大学生心理健康与体育活动 / 饶 丽
- 谈谈《说文》中反映的度制 / 雷景炀
- 校园文化建设是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强大推进器 / 罗 强
- 略论王安石变法 / 王守坤
- 校园文化建设整体框架最优化变革研究 / 邓孟昆 杨 军
- 《伤逝》中的“故事”与“新编” / 常兰兰 王海燕
- 开展多元化服务 提高图书馆服务质量 / 孙 茹
- 田径运动训练中有效训练手段的选用 / 武洪涛
- 解读傅东华汉译《飘》中的人名地名翻译 / 简 丽
- 国外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启示 / 李 曼 韩 敏
- 如何加强地方高校学生对学校的认同感 / 刘清玲
- 谈网络化校园文化体系的构建和应用 / 杨光辉
- 关于文学修养对理科学生重要性的探讨 / 叶彦炯
- 探讨高校学生社团有效运作的新路径 / 丁秋怡
- 农村中小学信息技术与课程的整合 / 王 雷
- 浅谈现代秘书应具备的知识 / 王晓艳
- 高校学生人际交往问题分析和辅导策略 / 薛俊梅
- 新建本科院校英语教学与教材建设的思考 / 谭 杰
- 试论高校文科专业实习实训基地建设与改革 / 侯 玲
- 听力学习浅论 / 张晓珊
- 英文产品说明书的文体特征分析 / 孙 婷
- 浅谈大学英汉翻译中的遣词用字 / 穆文超 李权芳
- 中职旅游管理专业课程体系的改革 / 井艺虹
- 构建语言支架 发展语言能力 / 唐利红
- 民办高校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困惑与对策 / 刘 静
- 浅谈班组建设 / 聂晓峰
- 大学英语听力教学探索 / 李权芳 穆文超
- 试论美育对艺术类学生品格养成的作用 / 苗春苗 杨宪敏
- 初中英语新课程改革 / 农志方
- 成人舞蹈教学初探 / 冯 微
- 婴儿时期的音乐教育与音乐心理 / 邹 帆
- 钢琴即兴伴奏课程学生学习现状的调查研究 / 黄洪焱 庞 荣
- 屈伸在藏族舞教学中的重要性 / 乌日娜
- 物动心感,情动声发 / 林菲菲
- 幼儿自主性绘画活动中生成性资源的形成 / 李亚娟 王熙娟 谭 明
- 浅谈清初“四王”及其画风对后世的影响 / 王晓娟
- 浅谈架上绘画对图像的利用 / 段 静
- 《双飞蝴蝶主题变奏曲》的艺术魅力 / 陈海燕
- 借助电影艺术提高中学生的文艺修养 / 刘瑞香
- 小议语言艺术与音乐的关系 / 梁晓爽 武 军 蔡 博
- 加强幼师专业学生美术教育的探讨 / 沈春娟
- 浅谈高师的视唱练耳 / 王钟莹
- 高考美术教学之我见 / 蔡春贵
- 艺术家的情结和个性对艺术风格的影响 / 熊伟翔
- 凤翔木版年画的造型观 / 孙英丽
- 高职语文课堂教学方法创新分析 / 刘文涛
- 对学前教育专业舞蹈教学的思考 / 鞠小萌
- 基于新课程背景下的高中历史教学探究 / 唐永宏
- 浅谈新课程理念下的初中历史教学 / 宁跃云
- 诵读经典学古文 继承传统习语言 / 吴 妍
- 如何构建有效的语文阅读教学课堂 / 李秀荣
- 注重课堂情感投入 彰显语文教学魅力 / 秦金良
- 新课程下语文教师角色的转换 / 马文隽
- 中学语文教学如何贯穿说话训练 / 吕永杰
- 情感在语文教学中的独特魅力 / 张 毅
- 论高职院校大学语文的审美教育 / 刘丽娜
- 语文教学应当强化生命教育 / 刘 晔
- 初唐四杰对七言歌行体的新拓展 / 王彦杰
- 浅谈提高语文课堂有效性的途径 / 王艳芳
- 区分巧合因素 提高鉴赏能力 / 林建国
- 作文教学中兴趣激发三部曲 / 赵小峰
- 初中语文教学中的审美教育 / 李盛山
- 浅谈如何培养中学生语言表达能力 / 张献平
- 浅谈初中古诗词意境教学 / 吴海燕
- 对初中思想品德课复习方法的思考 / 李 军
- 论美国宗教教育的载体和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 李素素
- 促进学生自主学习语文的几点策略 / 陈爱玲
- 小学语文教学过程的心理学研究 / 孙 鹏
- 初中德育教育应坚持三条原则 / 臧强义
- 基于最大熵原理的教学目标分类研究 / 张仕琼
- 谈中学语文教学中的人文情怀 / 张亚利
- 《荷叶圆圆》教学反思 / 路 平
- 语文教学中学生阅读能力的培养 / 姚 雨
- 公选课教学中大学生问题意识淡薄探析 / 戴 俊 屈迟文
- 谈谈小学语文教学的推进 / 俞 静
- 让学生和作文相恋 / 陈惠莲
- 论高职院校教育质量的提升 / 王爱文
-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教育中的启示 / 赵 洁
- 学习型个人的塑造与研究 / 王冬杰 王克斌 封玉新 杨建华
- 高职计算机的多媒体教学 / 吾尔尼沙.阿不都热依
- 教育人本管理的产生及实现途径 / 张明举
- 浅议农村小学教育的均衡发展 / 周礼根
- 小学高年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 / 吴秀伟
- 从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看教师教育观念的转变 / 孙丽丽
- 中职政治教学新方法探析 / 曲春园
- 浅谈高中教学中的全球史观 / 黄冬冬
- 素质教育视野下的教师素质探讨 / 王 玲
- 在教学中体现愉快教育理论原则之我见 / 徐少荣
- 浅谈西部教育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 次 仁
- 新课标背景下体育教师教育专业化发展 / 胡志华
- 学无止境 师当奋进 / 田月凤
- 如何在现当代文学教学中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 / 张玉琴
- 小学体育教学内容选择之我见 / 杨卫国
- 小议新疆学生对季节的盲点 / 马新清
- 我对语义教学的一点看法 / 刘 杰
- 如何提升初中体育教学 / 张洪海
- 小议学生学习写作的黄金阶段 / 寇志芹
- 浅析信息技术课的分层教学 / 林 青
- 态势语言在体育教学中的应用 / 王 祺
- 浅析高职计算机教学改革 / 王 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