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文学教育·中旬版 2010年第9期
ID: 153641
文学教育·中旬版 2010年第9期
ID: 153641
《赵氏孤儿》元明刊本比较谈
◇ 朱丽霞
[摘要]《赵氏孤儿》一剧在《元刊杂剧三十种》和《元曲选》中都有收录,但比较发现:在形式上明刊本增加了宾白和第五折;在内容方面它增加了人称代词,加强了心理描写,改变了叙述范围,从而使得作家和角色的主体意识得到增强,这种改变与时代及作家本人的创作倾向息息相关。
[关键词]《元刊杂剧三十种》;《元曲选》;主体意识
《元刊杂剧三十种》和《元曲选》都收录了《赵氏孤儿》一剧,然而,从元到明,该剧在曲牌、曲词、故事的主要矛盾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变化正是作家与改编者不同思想倾向的流露。
一、剧作家主体意识的呈现
《赵氏孤儿》的作者为纪君祥,而《元曲选》的编订者藏晋叔对杂剧进行了多处改写,可称之为第二作者,从元、明两种刊本中可以看出二人创作倾向的差异。
在形式上,藏晋叔编订《元曲选》时对元刊本《赵氏孤儿》一剧的改编有两点最为明显:增加宾白和第五折。
关于元代杂剧到底有没有宾白,一直有着不同的认识。藏晋叔认为“宾白则演剧时伶人自为之,故多鄙俚蹈袭之语” 。这一见解被王国维所否定,他在《宋元戏曲史》中从“曲白相生”的角度说明了“白”的存在,认为如果剧作家仅作曲而不作白则故事情节难以紧凑。[1]这一认识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同。然而,今人南京大学学者解玉峰在《二十世纪元曲研究刍议》一文中指出“元杂剧作家只作套曲而不作宾白并非是不可能的,这在关汉卿等早期杂剧作家中甚至可能是一种普遍现象。”并且“明初朱有墩在其《曲江池》等杂剧之首每每标曰“全宾” ,这是否能说明有些杂剧是宾白不全或者缺少宾白”。笔者是同意这一置疑的。因为在元杂剧早期是“曲本位”的,文人作家往往通过作曲来展现自己的才华与抱负,而对于宾白这种相对俚俗的表达不够重视。况且,元刊本只是演员演出的一个脚本,对于伶人来说可能只需要一点提示就可以了,宾白是否需要记载下来这本身就是有疑问的。但是,不管争论的结果如何,摆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在现存元刊本杂剧中,确实是宾白不全甚至是缺少宾白的,而它才是目前研究最为可靠的依据。
在《元刊杂剧三十种》中,《赵氏孤儿》一剧基本上没有宾白,也没有人物上场的提示,在舞台上,观众从演员的服饰、脸谱的区别,借助听觉上的曲词就完全可以了解“戏”的内容了。但是,如果仅从剧本上观则较难理清剧中人物及事件的关系。如《赵氏孤儿》虽是一人主唱,但每折主唱的人物不同:第一折的主唱为韩厥,第二、三折为公孙杵臼,第四折为长大后的赵氏孤儿,没有提示很容易弄混淆。吴梅说“故宾白在元杂剧确乎为点清眉目而作”。[2]没有它,就很难理清杂剧的眉目。固然没有宾白的元刊本似乎是着眼于舞台的,但明刊本《赵氏孤儿》对人物上场及动作的提示、对脚色的交代也给演员提供了更多的方便。这样,剧本除了作为演出的依据之外,它也走向了文人的案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明刊本与其说是演员演出的脚本不如说它是为读者提供的范本。尽管离开了舞台,戏剧就走向了灭亡,但这毕竟是藏晋叔的创造。他从为舞台提供范本到着眼于文本欣赏的文人主体,正是他主体意识的呈现。
的确,作为一部“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之林亦无愧色”的大悲剧,如果加上一个大团圆的结局,不仅少了戏剧悬念,也可能消弱它的悲剧力量。就西方的戏剧观念来说,它不是最优秀的,但它却符合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另外,如果不从内容的角度去理解,而从形式上看的话,《赵氏孤儿》用五折去结构一个杂剧剧本,不可谓不是一种突破。王国维说:“唯纪君祥之《赵氏孤儿》则有五折,又有楔子,此为元杂剧变例”,[3]而没有认为这种形式有何不妥。藏晋叔按照自己表达意趣的需要来结构故事,而不受传统体制的限制,这正是他个人的独特之处,体现了他的自我意识。也正是这种意识的存在,从而多了一个独特的剧本,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财富。我们完全可以把它与元刊本作不同的理解(如张哲俊在他的论文《悲剧形式:<赵氏孤儿>元明刊本的比较》中就从不同的角度作了深刻的分析,从而肯定了它的价值)。而且,南戏一部多达几十出的庞大体制未必不是受这些具有突破性的杂剧的影响。如果从这一点出发,明刊本《赵氏孤儿》和它的第五折都是应该肯定的,作家这种主体意识也是值得称赞的。
二、角色主体意识的强化
从元明两种刊本来看,《赵氏孤儿》的角色除了明本第五折中的“外”扮演的魏降外,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但是,藏晋叔通过对曲词的改变,从而使得人物性格、作品风格、作家倾向都发生了改变。通过这些改变,剧中人物和脚色的主体意识都得到了加强。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语言表达。《元刊杂剧三十种》中《赵氏孤儿》的唱词大多是没有涉及具体对象的,演唱者和剧中人物的主体地位都没有很明显的体现。而明刊本中增加 “你”“我”“他”等人称代词,不仅使得角色更为分明,而且使戏剧作为代言体的“代言”功能得到了张扬。这在剧本中有很多例子,如第四折【中吕·斗鹌鹑]】:
元刊本:【斗鹌鹑】这场上是那个孩儿?这市曹里是谁家上祖?这个更救不得儿孙?这个更救不得父母?这手绢是谁家宗祖图?从头儿对你儿诉:这人是犯法违条?这人是衔冤负屈?
明刊本:【斗鹌鹑】我则见这穿红的匹夫,将着这白须的来殴辱;兀的不恼乱我的心肠,气填我这肺腑。(带云)这一家儿若与我关系呵。(唱)我可也不杀了贼臣不是丈夫,我可便敢与他做主。这血泊中躺的不知是那个亲丁?这市曹中杀的也不知是谁家上祖?
在这段曲词中,元刊本几乎没用人称代词而是连用几个问句,虽然也有不平之气流露出来,然而总给人一种“事不关己”之感,孤儿只是在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对画面内容提出质疑,而他的情感却得不到有效得表达。经藏晋叔改编之后,连用了五个“我”字,这样虽然也是对画面的不平之叹,但同时他也把自己的感情融入了其中。孤儿此时的愤怒得到了更加明显的表达,且将自己置身于整个事件的中心。这样,孤儿是非分明,见义勇为得精神也得到了凸现,代言功能得到了很好 发挥。同时,一个“我”字,又将“末”的主唱地位体现了出来。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同样是第四折【中吕·幺篇】:
元刊本:既那厮背着一人,便合交灭了九族。刬地将天下军储国满黎庶,交那厮区处。原来你作主,你佑护,交地将诸侯欺负,原来你交他弑君杀父!
明刊本:他他他把俺一姓戮,我我我也还他九族屠。那怕他牵着神獒,拥着家兵,使着权术。你只看这一个,那一个是为谁而卒,岂可我做儿的倒安然如故!
在元刊本曲词中,用人称代词“你”和“他”,然而描写的范围太大,着重从国的方面控诉屠岸贾的罪行。到藏本中则加入了人称代词“我”,从而使得情感的抒发更真挚,而且拉近了人物与事件的距离,从“国”落实到“家”,落实到写两家的仇恨,且着重强调了“我”的心情。这样,不仅“我”的地位与主体意识得到了加强,而且“大报仇”的主题也得到了更好的阐释。
“我”本来就是主体地位的表征,通过“我”的介入,使剧本中主人公与演唱者的主体意识得到了强化,这是明刊本的一个重要特征。
(二)心理描写。心理活动是最个人化的东西,对心理的成功描写,无疑可以使主人公的精神气质和主体地位得到更好的体现。元、明刊本《赵氏孤儿》有在这方面有很大的区别:元刊本有十二曲为明刊本所无,而明刊本仅有四支曲子为元刊本所无。在这四曲中,就有一曲是对人物的心理描写,另外还有对心理描写的改编。如第二折【南吕·二煞】:
元:那个麒麟阁上功臣种,我不信大虫门前有犬脚踪,成人长大立纲宗。把屠岸贾万剐犹轻,报不了三百口家属苦痛。也不索做斋供,把腔子里血拗将来泼在半空,祭你那父亲和公公。
明:他把绷扒吊拷般般用,情节根由细细穷。那期间,枯枝朽骨难禁痛,少不得从实攀供。可知道你个程婴怕恐。我从来一诺千金重。便将我送上刀山与剑峰,断不可有始无终。
另外增加了【三煞】一曲:
这两家作下敌头里,但要访得孤儿有影踪,必然扒太平庄上兵围拥,铁桶般密不透风。则说老匹夫请先入瓮,他须知榜揭处天都动。偏你这罢职归田一老农,公然敢剔蝎撩蜂。
明刊本的这两支曲子,交代了公孙杵臼当时的处境,并设想可能遇到的酷刑,表明他对事情的后果早有心理准备,表现出了屠岸贾的残酷与狠毒。在这一对比中,人物性格就很明显的表现了出来。而且,主人公从设想中的长大后的孤儿转移到了演唱主体者本人公孙的身上,这样就取得了演唱者与角色的一致,从而使表现力增强。不论是脚色还是剧中人物的主体意识都得到了强化。
同样是对人物的心理描写,明本还把对人物的被动描写改为主动,用此手法来加强主人公的地位。如第二折【南吕·梁州第七】中写公孙杵臼“非是我乐耕种”,明本改为“怎如俺守田园学耕种”。前者强调的是外部环境的影响,主人公的主观情绪没有显现出来;改本则用反问句式,表现他目前的轻闲舒适,情感上由被动变为主动,精神境界也就更高了一个层次。
(三)描写范围。元刊本曲词在抒情时往往重背景,明本则重具体事件,表达上更充实,剧情更饱满,更能贴近观众的心,人物形象也能得到更好的凸现。如第一折【仙吕·油葫芦】:
元刊本:现如今,天下荒荒起战尘,各将边界分,信谗言播弄了晋乾坤。目今世乱英雄困,看何时法正天心顺。那汉虐上苍,损下民。试将碧悠悠阳福高天问,腆着个青脸子不饶人。
明刊本:他待要剪草防芽绝祸根,使着俺把府门。俺也是于家为国旧时臣。那一个藏孤儿的便不合将他隐,这一个杀孤儿的你可也心何忍。有一日,怒了上苍,恼了下民,怎不怕沸腾腾万口争谈论,天也显着个青脸子不饶人。
从元本到明本,由对天下大势的摹写改为杀孤救孤的具体事件,由对英雄的哀叹改为对韩厥具体处境的描写,由对苍天救人的期待改为对人民的愿望,描写的重心完全发生转移,突现的是人的力量而不天意。范围缩小,表现力才会更强。应该说这样的改动是作家有意为之,是元明两代作家的思想倾向及认识不同所致。
《赵氏孤儿》为历史剧,情节据《史记》而来,然而不同的表达方式就表明了作家的不同思想与倾向。曲为抒情而设,是作家意趣的寄托,明刊本对元本的改编,或者与纪君祥、藏晋叔这两位剧作家的处境不同有关。
据《录轨簿》载,纪君祥大概为元代前期作家,他所处的时代,民族矛盾尖锐,剧作家习惯用整个民族的情感代替个人的情感体验,因而个人意识不强。臧晋叔自幼聪敏,博闻强记,为万历八年进士,曾任南京国子监博士。他能诗善书,精晓音律,不屑于遵守官场礼法。在任国子监博士时,他常与当时的名人俊士游历山川,评述古今,相互酬唱,时至深夜,因而被劾罢官。在汉族统治下他没有了民族矛盾的牵挂,倒是较高的文化修养、对官场的深刻认识和个人对礼法的蔑视,更增强了他的主体意识,这一点也从他的作品中流露了出来。
前面从两个方面来说明明刊本相对于元刊本主体意识得到强化,其实这两个方面是一致的。因为角色的主体意识其实正是作家主体意识的表征。如果继续追究两种版本中的其它作品,相信还可以找到更多的证据。
参考文献:
[1]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2]吴梅《顾曲麈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66、67页。
[3]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作者简介:朱丽霞(1981—),女,湖北新洲人,文学硕士。现任职于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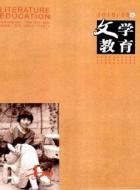
- 你赋予了小说文本以力量 / 姜广平
- 《史记》神话研究 / 李瑞仙
- 朝鲜李瀷与清代赵翼对李白诗歌的批评 / 王 成
- 浅析伍尔夫小说《到灯塔去》中的电影表现技巧 / 冯翠娟
- 试论杜甫《秋兴八首》的结构特点 / 于 莉
- 《赵氏孤儿》元明刊本比较谈 / 朱丽霞
- 浅析《西厢记》的人物形象 / 刘 精
- 从新历史主义角度解读《艾凡赫》中汪巴人物形象 / 郭 平
- 评《荆棘鸟》中梅吉与拉尔夫的爱情 / 宋玲玲
- 中美研究生跨文化差异及留学生心理问题分析 / 罗 坚 杨孟斌
- 浅谈朱自清散文的抒情风格 / 程 珏
- 民办高职院校后进生转化问题探讨 / 金剑青 顾佳滨
- 嵇康《声无哀乐论》之管窥 / 胡潆哥
- 职校生心理健康状况透视 / 王存凤
- 大学生心理健康与体育活动 / 饶 丽
- 谈谈《说文》中反映的度制 / 雷景炀
- 校园文化建设是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强大推进器 / 罗 强
- 略论王安石变法 / 王守坤
- 校园文化建设整体框架最优化变革研究 / 邓孟昆 杨 军
- 《伤逝》中的“故事”与“新编” / 常兰兰 王海燕
- 开展多元化服务 提高图书馆服务质量 / 孙 茹
- 田径运动训练中有效训练手段的选用 / 武洪涛
- 解读傅东华汉译《飘》中的人名地名翻译 / 简 丽
- 国外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启示 / 李 曼 韩 敏
- 如何加强地方高校学生对学校的认同感 / 刘清玲
- 谈网络化校园文化体系的构建和应用 / 杨光辉
- 关于文学修养对理科学生重要性的探讨 / 叶彦炯
- 探讨高校学生社团有效运作的新路径 / 丁秋怡
- 农村中小学信息技术与课程的整合 / 王 雷
- 浅谈现代秘书应具备的知识 / 王晓艳
- 高校学生人际交往问题分析和辅导策略 / 薛俊梅
- 新建本科院校英语教学与教材建设的思考 / 谭 杰
- 试论高校文科专业实习实训基地建设与改革 / 侯 玲
- 听力学习浅论 / 张晓珊
- 英文产品说明书的文体特征分析 / 孙 婷
- 浅谈大学英汉翻译中的遣词用字 / 穆文超 李权芳
- 中职旅游管理专业课程体系的改革 / 井艺虹
- 构建语言支架 发展语言能力 / 唐利红
- 民办高校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困惑与对策 / 刘 静
- 浅谈班组建设 / 聂晓峰
- 大学英语听力教学探索 / 李权芳 穆文超
- 试论美育对艺术类学生品格养成的作用 / 苗春苗 杨宪敏
- 初中英语新课程改革 / 农志方
- 成人舞蹈教学初探 / 冯 微
- 婴儿时期的音乐教育与音乐心理 / 邹 帆
- 钢琴即兴伴奏课程学生学习现状的调查研究 / 黄洪焱 庞 荣
- 屈伸在藏族舞教学中的重要性 / 乌日娜
- 物动心感,情动声发 / 林菲菲
- 幼儿自主性绘画活动中生成性资源的形成 / 李亚娟 王熙娟 谭 明
- 浅谈清初“四王”及其画风对后世的影响 / 王晓娟
- 浅谈架上绘画对图像的利用 / 段 静
- 《双飞蝴蝶主题变奏曲》的艺术魅力 / 陈海燕
- 借助电影艺术提高中学生的文艺修养 / 刘瑞香
- 小议语言艺术与音乐的关系 / 梁晓爽 武 军 蔡 博
- 加强幼师专业学生美术教育的探讨 / 沈春娟
- 浅谈高师的视唱练耳 / 王钟莹
- 高考美术教学之我见 / 蔡春贵
- 艺术家的情结和个性对艺术风格的影响 / 熊伟翔
- 凤翔木版年画的造型观 / 孙英丽
- 高职语文课堂教学方法创新分析 / 刘文涛
- 对学前教育专业舞蹈教学的思考 / 鞠小萌
- 基于新课程背景下的高中历史教学探究 / 唐永宏
- 浅谈新课程理念下的初中历史教学 / 宁跃云
- 诵读经典学古文 继承传统习语言 / 吴 妍
- 如何构建有效的语文阅读教学课堂 / 李秀荣
- 注重课堂情感投入 彰显语文教学魅力 / 秦金良
- 新课程下语文教师角色的转换 / 马文隽
- 中学语文教学如何贯穿说话训练 / 吕永杰
- 情感在语文教学中的独特魅力 / 张 毅
- 论高职院校大学语文的审美教育 / 刘丽娜
- 语文教学应当强化生命教育 / 刘 晔
- 初唐四杰对七言歌行体的新拓展 / 王彦杰
- 浅谈提高语文课堂有效性的途径 / 王艳芳
- 区分巧合因素 提高鉴赏能力 / 林建国
- 作文教学中兴趣激发三部曲 / 赵小峰
- 初中语文教学中的审美教育 / 李盛山
- 浅谈如何培养中学生语言表达能力 / 张献平
- 浅谈初中古诗词意境教学 / 吴海燕
- 对初中思想品德课复习方法的思考 / 李 军
- 论美国宗教教育的载体和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 李素素
- 促进学生自主学习语文的几点策略 / 陈爱玲
- 小学语文教学过程的心理学研究 / 孙 鹏
- 初中德育教育应坚持三条原则 / 臧强义
- 基于最大熵原理的教学目标分类研究 / 张仕琼
- 谈中学语文教学中的人文情怀 / 张亚利
- 《荷叶圆圆》教学反思 / 路 平
- 语文教学中学生阅读能力的培养 / 姚 雨
- 公选课教学中大学生问题意识淡薄探析 / 戴 俊 屈迟文
- 谈谈小学语文教学的推进 / 俞 静
- 让学生和作文相恋 / 陈惠莲
- 论高职院校教育质量的提升 / 王爱文
-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教育中的启示 / 赵 洁
- 学习型个人的塑造与研究 / 王冬杰 王克斌 封玉新 杨建华
- 高职计算机的多媒体教学 / 吾尔尼沙.阿不都热依
- 教育人本管理的产生及实现途径 / 张明举
- 浅议农村小学教育的均衡发展 / 周礼根
- 小学高年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 / 吴秀伟
- 从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看教师教育观念的转变 / 孙丽丽
- 中职政治教学新方法探析 / 曲春园
- 浅谈高中教学中的全球史观 / 黄冬冬
- 素质教育视野下的教师素质探讨 / 王 玲
- 在教学中体现愉快教育理论原则之我见 / 徐少荣
- 浅谈西部教育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 次 仁
- 新课标背景下体育教师教育专业化发展 / 胡志华
- 学无止境 师当奋进 / 田月凤
- 如何在现当代文学教学中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 / 张玉琴
- 小学体育教学内容选择之我见 / 杨卫国
- 小议新疆学生对季节的盲点 / 马新清
- 我对语义教学的一点看法 / 刘 杰
- 如何提升初中体育教学 / 张洪海
- 小议学生学习写作的黄金阶段 / 寇志芹
- 浅析信息技术课的分层教学 / 林 青
- 态势语言在体育教学中的应用 / 王 祺
- 浅析高职计算机教学改革 / 王 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