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文学教育·中旬版 2010年第9期
ID: 153632
文学教育·中旬版 2010年第9期
ID: 153632
《史记》神话研究
◇ 李瑞仙
[摘要]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史记》中涉及到的神话材料,对于呈现零星与不同特征的各个神话材料,采取了一种不算很严格的筛选神话材料的方式,目的是能通过这些材料找出司马迁的态度和思想。在某些可能隐藏神话材料的叙述中,通过考察,发现司马迁对神话做出怎样的改造。在对这些材料进行研究的基础上从司马迁对神话的处理和态度上探讨其思想中人事与天命的复杂关系,并对《史记》神话的特点进行了分析概括。
[关键词]史记;神话;天命
《史记》是一部百科全书似的中国通史,从内容到形式上都是划时代的伟大创新。汉至唐的文史理论家对《史记》评论的阐述中,首先都是从历史学的角度对《史记》予以肯定,然后才是阐发它文章辞采的文学性。在这一点上,古今没有分歧,符合历史的实际。因此不容置疑的是,《史记》首先是历史学。司马迁作为一个历史学家,要面对纷纭复杂的人类社会现象去作全面的解释,他对这些联系人鬼、人神关系的作法所持有的态度,完全从属于他的历史观的范畴。司马迁在《史记》中引用神话以及对神话的改造是有他的意图和思想在其中。在其所处的时代背景下,司马迁是背负着历史责任的,他并是迷信鬼神,他在探寻治乱兴衰的具体叙述中其内心并不相信天意鬼神能支配人事。
神话在发展演变的过程中会发生一些变化,其中比较明显是神话的历史化和仙话。在《史记》神话的研究中,要做的不仅要研究《史记》中的神话材料,还要能够弄清楚司马迁对于神话材料的取舍和处理,然后进一步去探究《史记》中的神话对《史记》的文学性起到什么样的影响,对后世的文学艺术起到什么样的影响。
在神话材料的界定上,《史记》中关于神话历史化;神话仙话后显示出神话色彩单薄的记述;无其他古籍能相参照的有神话色彩的神话材料;只有简单几笔带过纯系书法手段但是有研究价值的神话叙述;以及在对卜筮、星占、望气、灾异、梦兆、相术等迷信手段的叙述中有神话色彩及研究价值的“神异性材料”——即严格说来不能算是神话传说的材料,这些都纳入本文所要研究的范围。在对这些材料进行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司马迁对待不同时期的神话、神异性材料时的态度不同,在这些态度的背后都体现了他思想中人事与天命的复杂关系。
一、《史记》中神话的类型
(一 )始见于《史记》的神话
这一类的神话主要始见于《史记》的记载,可能司马迁并没有创造此类神话,而是通过其他的途径经过自己的改造和需要进行的记述。由于找不到相关文献的记载,本文把此类要探讨的神话称之为始见于《史记》的神话。这一类的神话多是司马迁的一种书法手段,或者是司马迁通过神话色彩的描写来表达自己的一种观点。
1、秦始祖大业的感生神话
秦始祖大业的感生神话最早可考的文献资料是《史记·秦本纪》:“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1]
2、汉高祖的感生神话
汉高祖的感生神话始见于《史记·高祖本纪》:“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2]
3、黄帝登天神话
黄帝乘龙登天的文字描写可以视为优美的神话,场面热闹生动,极富谐趣。“黄帝采首山铜,……故後世因名其处曰鼎湖,其弓曰乌号。”[3]这段神话经过史公的记述,立刻成了新神话,在后世民间也是大有影响的。同时这里可以看到神话的仙话,司马迁把黄帝仙人化了,体现了神话流传演变的一种大势所趋。
4、长桑君、黄石老丈的神话
《扁鹊仓公列传》记载:“舍客长桑君过,扁鹊独奇之,常谨遇之。长桑君亦知扁鹊非常人也。……乃出其怀中药予扁鹊:‘饮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当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书尽与扁鹊。忽然不见,殆非人也。”[4]这里的长桑君便具有神人的色彩。同样在神人那里获得帮助的还有张良,《留侯世家》中记载了张良得兵法的故事,张良在下邳桥遇见老丈,获得《太公兵法》,别后十三年后,张良“从高帝过济北,果见谷城山下黄石,取而葆祠之。留侯死,并葬黄石(冢)。每上冢伏腊,祠黄石。”[5]充满了神异色彩。
5、褒姒的神话
《周本纪》借周太史伯阳之口说褒姒是龙妖子,并对这一故事的来龙去脉作了交待。“周太史阳读《史记》曰:‘周亡矣。’昔自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龙止于夏帝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弃女子出于褒,是为褒姒。”[6]
6、梦境中的神话
以赵世家的四个梦为例。《赵世家》一共写了四个梦,这些梦预言了赵国每一个关键性历史转折过程,充满了神话的意味。
(二)经太史公改造过的神话
由于社会背景以及司马迁自身的思想,司马迁对神话资料进行了取舍。经过改造后的记述很多已经不能再称之为神话,而显示出了神话历史化的特征。还有一部分神话仍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在其他古籍上能看到相关记载,司马迁对其基本是是采取了引用的方式,即使稍作变动,也只是限于表述上,实质内容与之前流传的神话内容并无本质的差异。
1、洪水神话
洪水神话在《史记》中能够看到流传演变的影子,主要集中在《五帝本纪》和《夏本纪》中,其中以《夏本纪》更为详细。
2、部族战争神话
在《史记》中主要体现为黄帝和炎帝的战争、黄帝和蚩尤的战争。
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司马迁用一段文字记叙了战争的始末。“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7]
3、感生神话
(1)商始祖的感生神话
《史记》中最早的感生神话是玄鸟生商。《史记·殷本纪》曰:“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8]
(2)周始祖的感生神话
《史记·周本纪》中记载:“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初欲弃之,因名曰弃。”[9]最早可考的文献资料也是《诗经》。
二、司马迁天命神异思想的复杂性
(一)司马迁思想上的二元论色彩
司马迁对神话资料的选取和处理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他的思想,在对待神话的态度上他有着浓重的二元论色彩,但基本倾向是朴素唯物主义的。神话资料和《史记》中其他的人物史事一样,司马迁也在神话上倾注了自己想要表达的思想,也可以从中窥探出司马迁对于神话究竟持有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司马迁记述神话,并不是因为要探讨神话的本身如何,而是和对待其他材料一样,通过经过自己取舍整理的神话资料来抒发自己的“一家之言”。
(二)司马迁天命与非天命思想共存在《史记》神话中的体现
“天人关系”是西汉初年思想界最根本的哲学问题。天人感应学说认为,天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来主宰人间万物,人间的帝王又是受天命来统治人民,因此,一旦帝王有违背天意的事情,作恶于万民,上天便会用各种天灾变异或生物变异来向帝王和臣民发出警告。所以统治阶级十分重视天人感应学说。在这种背景和氛围中,不能说司马迁对鬼神天命的记载完全是想起到教化和讽喻作用,他的记载也有时代大背景的影响。
司马迁对天的论述也有其局限性,《史记》并没有摆脱神秘思想的影响。司马迁又师事董仲舒,他接受了天命论和天人感应说的思想影响是可以理解的。《史记》中有不少神话材料反映了司马迁的天命论。《史记·律书》:“昔黄帝有逐鹿之战,以定火灾;颛顼有共工之陈,以平水害;成汤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乱。递兴递费,胜者用事,所受于天也。”[10]明确提出了天命观,可以看出司马迁思想上存在着的矛盾与局限,但其仍试图插入人事,注重道德教化的作用。
同时,司马迁对上古史,明显自觉抛弃了传说中的神话成分,表现了他分离神人的思想。首先,神农以前的神话传说司马迁在《史记》中完全给抛弃了。他以《五帝本纪》为全书之首,以黄帝为古史开端关于这一点,在北京师范大学研究所编著的《司马迁研究新论》“论司马迁的历史哲学”一文中有详尽分析。文章认为,战国后期至秦汉,三皇五帝说大盛,而司马迁全不予理睬。其次,司马迁在叙述黄帝至夏的历史时,同样也抛弃了神话成分,但并不完全舍去那些可能是人事的材料,显露出了他企图从神话中发现人类史的朦胧意识。
司马迁精通天文、律例,但古代的科学知识是与宗教迷信、神话传说杂糅在一起的。对于天道性命的有无,司马迁报着既怀疑,又相信的态度。“纪异”,就是对天异灾变加以记载;而“说不书”,即对感应的说法不作记载,这一点在《史记》中表现的看似混乱实际上也有司马迁的巧妙安排。《律》《历》《天官》三书记载了一些天变以及感应的资料,而在载人事的纪传中并不加以发挥,尤其是七十列传,力求实录人事的历史变化,而对虚妄荒诞之说加以摈斥或揭露。司马迁在“天人之际,合二为一”的神学氛围中,不可避免受其影响,但是,从思想上和历史著作的实践上,他有意识地把神从已被神化了的上古史中清理出去,基本否认了“天”对个人命运到国家兴亡等人事的决定作用。司马迁的主要思想倾向,不是讲天人交会,而是讲天人相分。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方法,就是在对天象的实际观测和对人事的实际考察中,对天、人两个方面都获得了唯物主义的见解,这才是司马迁天人观的主流。这些都说明,司马迁的思想仍旧是唯物的,他比较全面地把人类史看成是人类自身的活动,而不是实现神意的工具;人类史是人类社会自身的发展过程,有其规律,并不是上天的安排。这无论是对科学史观的发展过程说还是对整个历史学说,都具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三、《史记》神话的特征
由于司马迁按照“雅驯”的原则严格挑选材料,神话的历史化成为了《史记》神话的最突出的特点。寓神话于史,神话带有历史化的色彩成了《史记》神话最显著的特色。
司马迁用一些神话描写来阐述民族的开拓、发展和融合,这也是历史神话化的一种表现。“讙兜进言共工,尧曰不可而试之工师,共工果淫辟。四岳举鲧治鸿水,尧以为不可,岳强请试之,试之而无功,故百姓不便。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辠而天下咸服。”[11]
四、结语
由于《史记》是部历史著作,《史记》中的神话和司马迁选用的其他材料一样表达着作者的史学思想,很多神话材料以历史化的形态呈现,不仅表现在内容上的历史化,在叙述方式和文字风格上也都有所改造。这些神话材料没有专门的归类和呼应,而是在需要的时候很自然的穿插融合,和作者著作的整体风格融为一体。虽然零散但是也体现了丰富性,并同样体现了司马迁在文学上的成就和风采。
注释:
①【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②袁珂《中国神话传说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
③袁珂、周明《中国神话资料萃编》,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
④袁珂《中国神话史》,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
⑤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96年
⑥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秦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73页
[2]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41页
[3]司马迁《史记·封禅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394页
[4]司马迁《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785页
[5]司马迁《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785页
[6]司马迁《史记·周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47页
[7]司马迁《史记·律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页
[8]袁珂、周明《中国神话资料萃编》,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第152页
[9]袁珂、周明《中国神话资料萃编》,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第148页
[10]司马迁《史记·律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100页
[11]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8页
作者简介:李瑞仙(1984—),籍贯:湖北荆门,单位:咸宁学院,职称:助教方向:汉语言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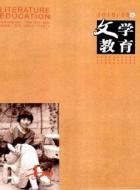
- 你赋予了小说文本以力量 / 姜广平
- 《史记》神话研究 / 李瑞仙
- 朝鲜李瀷与清代赵翼对李白诗歌的批评 / 王 成
- 浅析伍尔夫小说《到灯塔去》中的电影表现技巧 / 冯翠娟
- 试论杜甫《秋兴八首》的结构特点 / 于 莉
- 《赵氏孤儿》元明刊本比较谈 / 朱丽霞
- 浅析《西厢记》的人物形象 / 刘 精
- 从新历史主义角度解读《艾凡赫》中汪巴人物形象 / 郭 平
- 评《荆棘鸟》中梅吉与拉尔夫的爱情 / 宋玲玲
- 中美研究生跨文化差异及留学生心理问题分析 / 罗 坚 杨孟斌
- 浅谈朱自清散文的抒情风格 / 程 珏
- 民办高职院校后进生转化问题探讨 / 金剑青 顾佳滨
- 嵇康《声无哀乐论》之管窥 / 胡潆哥
- 职校生心理健康状况透视 / 王存凤
- 大学生心理健康与体育活动 / 饶 丽
- 谈谈《说文》中反映的度制 / 雷景炀
- 校园文化建设是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强大推进器 / 罗 强
- 略论王安石变法 / 王守坤
- 校园文化建设整体框架最优化变革研究 / 邓孟昆 杨 军
- 《伤逝》中的“故事”与“新编” / 常兰兰 王海燕
- 开展多元化服务 提高图书馆服务质量 / 孙 茹
- 田径运动训练中有效训练手段的选用 / 武洪涛
- 解读傅东华汉译《飘》中的人名地名翻译 / 简 丽
- 国外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启示 / 李 曼 韩 敏
- 如何加强地方高校学生对学校的认同感 / 刘清玲
- 谈网络化校园文化体系的构建和应用 / 杨光辉
- 关于文学修养对理科学生重要性的探讨 / 叶彦炯
- 探讨高校学生社团有效运作的新路径 / 丁秋怡
- 农村中小学信息技术与课程的整合 / 王 雷
- 浅谈现代秘书应具备的知识 / 王晓艳
- 高校学生人际交往问题分析和辅导策略 / 薛俊梅
- 新建本科院校英语教学与教材建设的思考 / 谭 杰
- 试论高校文科专业实习实训基地建设与改革 / 侯 玲
- 听力学习浅论 / 张晓珊
- 英文产品说明书的文体特征分析 / 孙 婷
- 浅谈大学英汉翻译中的遣词用字 / 穆文超 李权芳
- 中职旅游管理专业课程体系的改革 / 井艺虹
- 构建语言支架 发展语言能力 / 唐利红
- 民办高校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困惑与对策 / 刘 静
- 浅谈班组建设 / 聂晓峰
- 大学英语听力教学探索 / 李权芳 穆文超
- 试论美育对艺术类学生品格养成的作用 / 苗春苗 杨宪敏
- 初中英语新课程改革 / 农志方
- 成人舞蹈教学初探 / 冯 微
- 婴儿时期的音乐教育与音乐心理 / 邹 帆
- 钢琴即兴伴奏课程学生学习现状的调查研究 / 黄洪焱 庞 荣
- 屈伸在藏族舞教学中的重要性 / 乌日娜
- 物动心感,情动声发 / 林菲菲
- 幼儿自主性绘画活动中生成性资源的形成 / 李亚娟 王熙娟 谭 明
- 浅谈清初“四王”及其画风对后世的影响 / 王晓娟
- 浅谈架上绘画对图像的利用 / 段 静
- 《双飞蝴蝶主题变奏曲》的艺术魅力 / 陈海燕
- 借助电影艺术提高中学生的文艺修养 / 刘瑞香
- 小议语言艺术与音乐的关系 / 梁晓爽 武 军 蔡 博
- 加强幼师专业学生美术教育的探讨 / 沈春娟
- 浅谈高师的视唱练耳 / 王钟莹
- 高考美术教学之我见 / 蔡春贵
- 艺术家的情结和个性对艺术风格的影响 / 熊伟翔
- 凤翔木版年画的造型观 / 孙英丽
- 高职语文课堂教学方法创新分析 / 刘文涛
- 对学前教育专业舞蹈教学的思考 / 鞠小萌
- 基于新课程背景下的高中历史教学探究 / 唐永宏
- 浅谈新课程理念下的初中历史教学 / 宁跃云
- 诵读经典学古文 继承传统习语言 / 吴 妍
- 如何构建有效的语文阅读教学课堂 / 李秀荣
- 注重课堂情感投入 彰显语文教学魅力 / 秦金良
- 新课程下语文教师角色的转换 / 马文隽
- 中学语文教学如何贯穿说话训练 / 吕永杰
- 情感在语文教学中的独特魅力 / 张 毅
- 论高职院校大学语文的审美教育 / 刘丽娜
- 语文教学应当强化生命教育 / 刘 晔
- 初唐四杰对七言歌行体的新拓展 / 王彦杰
- 浅谈提高语文课堂有效性的途径 / 王艳芳
- 区分巧合因素 提高鉴赏能力 / 林建国
- 作文教学中兴趣激发三部曲 / 赵小峰
- 初中语文教学中的审美教育 / 李盛山
- 浅谈如何培养中学生语言表达能力 / 张献平
- 浅谈初中古诗词意境教学 / 吴海燕
- 对初中思想品德课复习方法的思考 / 李 军
- 论美国宗教教育的载体和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 李素素
- 促进学生自主学习语文的几点策略 / 陈爱玲
- 小学语文教学过程的心理学研究 / 孙 鹏
- 初中德育教育应坚持三条原则 / 臧强义
- 基于最大熵原理的教学目标分类研究 / 张仕琼
- 谈中学语文教学中的人文情怀 / 张亚利
- 《荷叶圆圆》教学反思 / 路 平
- 语文教学中学生阅读能力的培养 / 姚 雨
- 公选课教学中大学生问题意识淡薄探析 / 戴 俊 屈迟文
- 谈谈小学语文教学的推进 / 俞 静
- 让学生和作文相恋 / 陈惠莲
- 论高职院校教育质量的提升 / 王爱文
-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教育中的启示 / 赵 洁
- 学习型个人的塑造与研究 / 王冬杰 王克斌 封玉新 杨建华
- 高职计算机的多媒体教学 / 吾尔尼沙.阿不都热依
- 教育人本管理的产生及实现途径 / 张明举
- 浅议农村小学教育的均衡发展 / 周礼根
- 小学高年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 / 吴秀伟
- 从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看教师教育观念的转变 / 孙丽丽
- 中职政治教学新方法探析 / 曲春园
- 浅谈高中教学中的全球史观 / 黄冬冬
- 素质教育视野下的教师素质探讨 / 王 玲
- 在教学中体现愉快教育理论原则之我见 / 徐少荣
- 浅谈西部教育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 次 仁
- 新课标背景下体育教师教育专业化发展 / 胡志华
- 学无止境 师当奋进 / 田月凤
- 如何在现当代文学教学中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 / 张玉琴
- 小学体育教学内容选择之我见 / 杨卫国
- 小议新疆学生对季节的盲点 / 马新清
- 我对语义教学的一点看法 / 刘 杰
- 如何提升初中体育教学 / 张洪海
- 小议学生学习写作的黄金阶段 / 寇志芹
- 浅析信息技术课的分层教学 / 林 青
- 态势语言在体育教学中的应用 / 王 祺
- 浅析高职计算机教学改革 / 王 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