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文学教育·中旬版 2010年第9期
ID: 153657
文学教育·中旬版 2010年第9期
ID: 153657
《伤逝》中的“故事”与“新编”
◇ 常兰兰 王海燕
[摘要]《伤逝》作为鲁迅唯一的一部爱情小说,其极具现代性的阐释空间使人们往往忽略了其中传统文学的因子,如“私奔”的叙事模式。在与《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等传统爱情小说的比较中,不难发现,正是在“故事”与“新编”的张力之中,《伤逝》获得了如此言说不尽的审美内涵。
[关键词]《伤逝》;“私奔”;传统;现代
一、“私奔”之“故事”
(一)“私奔”模式的延用
传统式“私奔”是指两情相悦的男女因得不到家长和世俗的成全而私自结合并一起从原来的生活环境中脱离的行为过程。然而绵延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私奔”则以成为许多接受新思想的女青年追求个性解放,男女平等以及婚恋自主的代名词从而又被赋予了新的涵义。由此看来,极受五四青年追捧,大力宣传与倡导的“婚恋自由”并非如大家所想象的那样全然具有现代性,或者更准确地说它应该是现代女青年在现代个性解放的引导下所接受的“私奔”传统。然而无论是古典式还是现代背景下的“私奔”模式,都必然会融入以下两种要素;解救和婚恋。解救突出表现在处于强势地位群体的对处于被禁锢和束缚地位的弱势群体的解救,前者多为男性,后者多为女性,所以在解救双方常常会在性别条件的客观促成下发展为婚恋关系,如《伤逝》;但另外一种模式则是男女双方先进行爱恋而后为维持这种关系而不得已进入解救阶段的,如《杜》。任何包含 “私奔”叙事而又能保持较久艺术魅力的文学作品都不可能缺少“爱”与“救”这两个叙事要素,否则就会成为片面描写男妇私情的低层次作品,也就不可能在悠久的文学创作史上经大浪淘沙熠熠闪光今。
(二)私奔叙事的特点
私奔一般会在借用一股外力的支持下得以完成。在古典式私奔模式里,男女双方一般会在一股外力的支持得以成功结合,如《杜》中的“柳遇春”、《莺莺传》里的“红娘”。而《伤逝》里的“涓生”与“子君”得以顺利结合是在更为强大的外力支持下顺利完成的。因为在个性解放的时代大潮中,自由恋爱已被赋予了道德的合法性, 因而“红娘”的角色由强大的时代精神来担当,这种时代精神无疑充当了青年男女勇于追求自由爱情成功私奔的过程中的强力催化剂。
私奔叙事具有警醒,告诫以及引起反思的意义。私奔作为一个在日常生活中出现的反常事件,除了能够满足人们反规心理与破禁欲望以及具有相当的戏剧性外,它还具备了统治者所认同的推行的教化意义。他们往往通过充满悖谬之感的叙事策略(对追求真爱的勇气大加褒奖的私奔故事往往设置以悲剧结局)的来达到双重但相悖的教化目地。冯梦龙的《醒世通言》正是希望通过负心人“李甲”所受报应告诫世上男子莫要始乱终弃,而在对痴情 “十娘”大加褒奖和赞美的同时,也借其被弃跳江而亡悲惨结局对世上怀揣爱情梦想的女子敲响了警钟。《伤逝》则体现了作者对社会现实的深刻反思。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先觉知识分子,普遍感受到思想上所接受的现代意识与心理上所保留的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磨擦所带来的精神苦闷,他们不断地“奋斗”希望找到一条“新的生路”,然而梦醒者依然“无路可走”,作为“中国文化的守夜人”,鲁迅敏锐地感觉到,在历史环境依然较为浓厚地笼罩在中国大地上的时候,不加审视地借用外来思想,对本民族延续了几千年的文化传统进行改造是极为困难和艰险的。广大先觉知识分子对“舶来品”凭借一时激情的叫嚣和幼稚地践行只会如一粒石子在妄图“一石激起千层浪”的初衷下跳进潭水,而后却发现在这潭浑厚的“死水”里只能“扑通”一声沉入潭底,甚至连“半点漪沦”也不曾激起。
(三)叙事视角的差异性
《伤逝》采用的是第一人称“我”的叙事视角因此读者的眼界便被限定在男主人公的认识视野之内。加之《伤逝》以“手记”这种文本形式就使得《伤逝》私人化叙事特点更为突出,如“涓生”在叙述时,无意识地多次运用 “仿佛”“似乎”以及类似的词汇,其出现频率之高恰恰表明了“我”在叙述时的含混与犹疑。除了因遗忘引起对诸多事情再现时的不确切,另外就是“涓生”在有意淡化当时的真实情境,这种有意或无意为之的虚化和掩饰足以给读者再设迷障,所以在这双层局限之下,妄图认识故事的原始面貌几乎不可能。《杜》运用全知视角,将故事清晰明了地直接置于读者的阅读视野之下,这种全方位的叙事使作者无论是故事情节的设置、人物形象的塑造、主题思想的生发都显得真观,紧凑,完满。而采用第一人称的叙事的《伤逝》因融入了较多的私人化叙事使得未被观照的“盲区”大量存在,如一直处于沉默到死地位的“子君”和“涓生忏悔”的虚伪性都真接带给《伤逝》以众多疑义的存在和解读的迷惑性。
二、“新编”之意义
作为一个古老的创作题材,“私奔”在反映婚恋题材的文学作品里是俯拾即是,它们共同反映出从古至今在男权社会下女性所遭受的屈辱,同类题材的大量累积,使得“私奔”成为带有原始意味的母题。《伤逝》与《杜》共同反映了因男性“始乱终弃”而直接导致爱情悲剧发生的这一文学主题。在《杜》中“李甲”因无法兼得名利与爱情最后选择卖妻归家,这是传统意义上的“始乱终弃”,他因自身对专制家庭缺乏反抗之勇气以及他见利忘义的性格弱点至使爱人因“中道见弃”而最终含恨跳江而亡。“十娘”在此时的人生状态下,她的生的价值是通过对自由爱情的追求,对人生命运自主掌控的实现来体现的,然而在得知“李甲”意欲将她转卖于“孙富”时,便顿悟原来她为人生理想的实现所付出的不懈努力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所以相对于“子君”她表现地更为决然和平静。这种暴风雨前的平静让人,无法想象 “十娘”的悲壮和刚烈,只能屏气凝神静观其变。当“十娘”听到“我(李甲)得千金,可藉口以见吾父母;而恩卿亦得所天”[1]之后便在冷笑一声之后顺着“李甲”的心愿就痛快地答应他,第二天她认真梳妆等到银货交割完毕便将万般珍宝投之江中,最后痛骂“孙富”“李甲”二人之后就怀抱宝匣,纵身跳往江中。此时,整个故事的悲剧意味达到了最高点,真所谓“三魂渺渺归水府,七魄悠悠入冥途”![2]
“涓生”与“子君”是因为爱与自由的共同追求结合在一起,在他们共同生活的这一阶段“子君”的人生全部要义就是“涓生”对她的挚爱,所以当她感知到“涓生”的爱正在飘然而逝时,她试图挽回,最后终因无济于世,因为“我已经不爱你了”于是,“子君”在被父亲接走后就默默死去。“她的命运,已经决定她在我所给与真实——无爱的人间死灭了”[3],因为“无爱”,“子君”的生的意义便不复存在,于是她的精神载体也在心灵不断地促逼与拷问下消耗殆尽。涓生对子君的无限忏悔和深深自责,暗示着梦醒者纵然“无路可走”,但却再也难以昏昏入睡的双重矛盾。
这里,现代的叙事手法冲破了传统叙事所无法容纳的新质——既有对父权制的批判、对现代爱情观的反思,也有启蒙与反启蒙的暧昧纠葛,还有新派人物涓生在忏悔中无意间复制着的他力求推翻的那些“故事”……这一切都告诉我们:“新”与“旧”之间尚有一个无比广阔的过渡地带,“新”既脱胎于“旧”又试图挣脱甚至颠覆它,“旧”既孕育着“新”又试图以自己的权威遮蔽它,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怎么想象也不为过。正因为如此,永远会有“故事”之“新编”。只不过象《伤逝》这样具有言说不尽的审美内涵的“故事”“新编”恐怕是除了鲁迅再也无人可以企及的高度。这也是《伤逝》远高于《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魅力之所在!
参考文献:
[1][2]王兆鹏《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明清近代卷)[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4
[3]鲁迅<伤逝>《鲁迅全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作者简介:常兰兰,襄樊市襄樊学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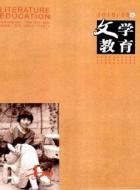
- 你赋予了小说文本以力量 / 姜广平
- 《史记》神话研究 / 李瑞仙
- 朝鲜李瀷与清代赵翼对李白诗歌的批评 / 王 成
- 浅析伍尔夫小说《到灯塔去》中的电影表现技巧 / 冯翠娟
- 试论杜甫《秋兴八首》的结构特点 / 于 莉
- 《赵氏孤儿》元明刊本比较谈 / 朱丽霞
- 浅析《西厢记》的人物形象 / 刘 精
- 从新历史主义角度解读《艾凡赫》中汪巴人物形象 / 郭 平
- 评《荆棘鸟》中梅吉与拉尔夫的爱情 / 宋玲玲
- 中美研究生跨文化差异及留学生心理问题分析 / 罗 坚 杨孟斌
- 浅谈朱自清散文的抒情风格 / 程 珏
- 民办高职院校后进生转化问题探讨 / 金剑青 顾佳滨
- 嵇康《声无哀乐论》之管窥 / 胡潆哥
- 职校生心理健康状况透视 / 王存凤
- 大学生心理健康与体育活动 / 饶 丽
- 谈谈《说文》中反映的度制 / 雷景炀
- 校园文化建设是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强大推进器 / 罗 强
- 略论王安石变法 / 王守坤
- 校园文化建设整体框架最优化变革研究 / 邓孟昆 杨 军
- 《伤逝》中的“故事”与“新编” / 常兰兰 王海燕
- 开展多元化服务 提高图书馆服务质量 / 孙 茹
- 田径运动训练中有效训练手段的选用 / 武洪涛
- 解读傅东华汉译《飘》中的人名地名翻译 / 简 丽
- 国外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启示 / 李 曼 韩 敏
- 如何加强地方高校学生对学校的认同感 / 刘清玲
- 谈网络化校园文化体系的构建和应用 / 杨光辉
- 关于文学修养对理科学生重要性的探讨 / 叶彦炯
- 探讨高校学生社团有效运作的新路径 / 丁秋怡
- 农村中小学信息技术与课程的整合 / 王 雷
- 浅谈现代秘书应具备的知识 / 王晓艳
- 高校学生人际交往问题分析和辅导策略 / 薛俊梅
- 新建本科院校英语教学与教材建设的思考 / 谭 杰
- 试论高校文科专业实习实训基地建设与改革 / 侯 玲
- 听力学习浅论 / 张晓珊
- 英文产品说明书的文体特征分析 / 孙 婷
- 浅谈大学英汉翻译中的遣词用字 / 穆文超 李权芳
- 中职旅游管理专业课程体系的改革 / 井艺虹
- 构建语言支架 发展语言能力 / 唐利红
- 民办高校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困惑与对策 / 刘 静
- 浅谈班组建设 / 聂晓峰
- 大学英语听力教学探索 / 李权芳 穆文超
- 试论美育对艺术类学生品格养成的作用 / 苗春苗 杨宪敏
- 初中英语新课程改革 / 农志方
- 成人舞蹈教学初探 / 冯 微
- 婴儿时期的音乐教育与音乐心理 / 邹 帆
- 钢琴即兴伴奏课程学生学习现状的调查研究 / 黄洪焱 庞 荣
- 屈伸在藏族舞教学中的重要性 / 乌日娜
- 物动心感,情动声发 / 林菲菲
- 幼儿自主性绘画活动中生成性资源的形成 / 李亚娟 王熙娟 谭 明
- 浅谈清初“四王”及其画风对后世的影响 / 王晓娟
- 浅谈架上绘画对图像的利用 / 段 静
- 《双飞蝴蝶主题变奏曲》的艺术魅力 / 陈海燕
- 借助电影艺术提高中学生的文艺修养 / 刘瑞香
- 小议语言艺术与音乐的关系 / 梁晓爽 武 军 蔡 博
- 加强幼师专业学生美术教育的探讨 / 沈春娟
- 浅谈高师的视唱练耳 / 王钟莹
- 高考美术教学之我见 / 蔡春贵
- 艺术家的情结和个性对艺术风格的影响 / 熊伟翔
- 凤翔木版年画的造型观 / 孙英丽
- 高职语文课堂教学方法创新分析 / 刘文涛
- 对学前教育专业舞蹈教学的思考 / 鞠小萌
- 基于新课程背景下的高中历史教学探究 / 唐永宏
- 浅谈新课程理念下的初中历史教学 / 宁跃云
- 诵读经典学古文 继承传统习语言 / 吴 妍
- 如何构建有效的语文阅读教学课堂 / 李秀荣
- 注重课堂情感投入 彰显语文教学魅力 / 秦金良
- 新课程下语文教师角色的转换 / 马文隽
- 中学语文教学如何贯穿说话训练 / 吕永杰
- 情感在语文教学中的独特魅力 / 张 毅
- 论高职院校大学语文的审美教育 / 刘丽娜
- 语文教学应当强化生命教育 / 刘 晔
- 初唐四杰对七言歌行体的新拓展 / 王彦杰
- 浅谈提高语文课堂有效性的途径 / 王艳芳
- 区分巧合因素 提高鉴赏能力 / 林建国
- 作文教学中兴趣激发三部曲 / 赵小峰
- 初中语文教学中的审美教育 / 李盛山
- 浅谈如何培养中学生语言表达能力 / 张献平
- 浅谈初中古诗词意境教学 / 吴海燕
- 对初中思想品德课复习方法的思考 / 李 军
- 论美国宗教教育的载体和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 李素素
- 促进学生自主学习语文的几点策略 / 陈爱玲
- 小学语文教学过程的心理学研究 / 孙 鹏
- 初中德育教育应坚持三条原则 / 臧强义
- 基于最大熵原理的教学目标分类研究 / 张仕琼
- 谈中学语文教学中的人文情怀 / 张亚利
- 《荷叶圆圆》教学反思 / 路 平
- 语文教学中学生阅读能力的培养 / 姚 雨
- 公选课教学中大学生问题意识淡薄探析 / 戴 俊 屈迟文
- 谈谈小学语文教学的推进 / 俞 静
- 让学生和作文相恋 / 陈惠莲
- 论高职院校教育质量的提升 / 王爱文
-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教育中的启示 / 赵 洁
- 学习型个人的塑造与研究 / 王冬杰 王克斌 封玉新 杨建华
- 高职计算机的多媒体教学 / 吾尔尼沙.阿不都热依
- 教育人本管理的产生及实现途径 / 张明举
- 浅议农村小学教育的均衡发展 / 周礼根
- 小学高年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 / 吴秀伟
- 从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看教师教育观念的转变 / 孙丽丽
- 中职政治教学新方法探析 / 曲春园
- 浅谈高中教学中的全球史观 / 黄冬冬
- 素质教育视野下的教师素质探讨 / 王 玲
- 在教学中体现愉快教育理论原则之我见 / 徐少荣
- 浅谈西部教育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 次 仁
- 新课标背景下体育教师教育专业化发展 / 胡志华
- 学无止境 师当奋进 / 田月凤
- 如何在现当代文学教学中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 / 张玉琴
- 小学体育教学内容选择之我见 / 杨卫国
- 小议新疆学生对季节的盲点 / 马新清
- 我对语义教学的一点看法 / 刘 杰
- 如何提升初中体育教学 / 张洪海
- 小议学生学习写作的黄金阶段 / 寇志芹
- 浅析信息技术课的分层教学 / 林 青
- 态势语言在体育教学中的应用 / 王 祺
- 浅析高职计算机教学改革 / 王 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