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文学教育·中旬版 2010年第7期
ID: 153456
文学教育·中旬版 2010年第7期
ID: 153456
略论李清照《词论》的词学史意义
◇ 黄 艳
[摘要]李清照的《词论》作为文学史上第一篇系统的词学专论,从词本位的角度,提出了词“别是一家”的观点,可以说是词学史词学史上第一座理论丰碑。但是,《词论》从它产生的时代起,就颇遭非议。本文拟对《词论》产生的背景进行简单梳理、溯源,以期能对其价值作更清晰的认识。
[关键词]别是一家;系统;继承;超越
宋代词人李清照,以优秀的创作实践和理论贡献铸就了她在词史上永恒的璀璨。她尽管只有四十多首词作传世,却以绝对优势登上了中国第一女词人的宝座;而在词学理论成就方面,其《词论》因锐气十足而屡遭批评、指责,批评者大多认为是“不自量力、狂妄过之”的言论,而忽视了独特的历史价值。本文拟通过对《词论》的其理论形成背景作简单的溯源,便于更全面认识和评价其在词学批评史上的作用和地位。
一、《词论》产生的时代背景
词从唐代由民间起源, 到李清照的时代,走过了几百年的历程。这几百年间, 词由民间创作发展到文人创作, 经历了晚唐五代的繁荣期, 也经历了宋初几十年的低沉期。李清照《词论》产生的时期,正是宋词发展史上出现新的变革的阶段。这种变化表现在形式上,是慢词长调的兴起。慢词较小令可以容纳更多的内容,为词题材范围的扩大和表现手法的多样化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个进步。而表现在内容上,则是诗文革新运动的影响波及词坛。人们早已不满足于花间词风,要求打破词专作香软之语的传统,作家们纷纷进行变革:柳永将市民生活中间的感受纳入词中;范仲淹、王安石用词写边塞、怀古题材;到了苏轼,又掀起了一个更大的变革,他对传统题材和表现手法都有所否定,提出“以诗为词”。此时的词坛可谓争艳斗奇,各家尽显风采。然而究竟什么是词,该怎么作词,这些词家的词作写得怎么样,对这些问题的探讨都只是摘句式的较涣散的个别批评。如:晁补之《评本朝乐府》、李之仪《跋戚氏》、《书乐府长短句后》、《跋山谷二词》、黄庭坚《小山词序》、《跋东坡乐府》、张耒有《东山词序》、陈师道《书旧词后》[1]等均对词学批评理论有所涉足,但均未摆脱摘句品评的基本模式。
李清照的《词论》,可谓是应时而生。全文虽不足七百字,但内容丰富,立论尖锐,历述词史、评点词家,并指出词“别是一家”的理论,词的特质进行了探讨和界定。文章首先从音乐和词的关系入手,对词坛作家进行一一点评,并对词的创作提出了协音律、尚文雅、协音律、尚浑成、尚铺叙、主情致等方面艺术要求,完成了从零碎的只言片语到系统理论的飞跃,不可置疑地成为了第一篇系统的词学专论,也成为了词学批评史上的第一座无法逾越的丰碑。
二、《词论》对传统词学观的承继与超越
《词论》提出词当“别是一家”的词学观念,既是对传统的词学观念的继承,又在对前代传统的词学观念的高度概括和总结的基础上有着重要的发展和更新。
词最早产生于宴乐场合、伶工歌姬之口,地位十分低下。欧阳炯在《花间集序》中说:“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妖娆之态。”“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倡风”[2],认为词是歌妓伶人演唱以资宴饮之欢的,上承齐梁宫体,下附里巷倡风,以绮靡为本。词的内容也囿于男欢女爱、闲愁别绪,风格多婉转缠绵、奢靡软媚,所以被视为“伶工之词”和难登大雅之堂的“艳科”。晚唐五代至宋初词人,又多以婉约为本,恪守“诗庄词媚”的审美观念,形成了文人词“艳媚”的传统观念。经过三个多世纪的演变,到宋代,词体已经相当成熟,但“词为诗余”、“褒诗贬词”的传统观念却仍然一直占据着主流。学者们为了推尊词体,都尽力想把词和诗攀上关系,苏轼更是提出了 “以诗为词”的口号。当然,苏轼在开拓词境、推尊词体上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但是在当时情形下,词也面临着受诗文侵越而失去个性的危险,而宋诗又尚义理,好议论,味同嚼蜡,以之入词必然使词的魅力大打折扣。因此恰恰就在苏轼革新词的内容的同时,也引起了当时词人们意见的分歧,于是围绕着如何确认词的体性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争。一派当然是以以苏轼为代表,他们认为词由诗发展而来,倡导词的诗化;一派认为词和诗是不同的,应维护词的本色。如《王直方诗话》云:“东坡尝以所作小词示无咎(晁补之) 、文潜(张耒) ,曰:‘何如少游?’二人皆对云:‘少游诗似小词,先生小词似诗。’”[3]虽然他们所说的还很笼统。但二人却不谋而合感觉到诗词应该有所不同。稍后李之仪为吴思道词作跋时说:“长短句于遣词中最为难工,自有一种风格,稍不如格,便觉龃龉。”[4]李之仪的所谓长短句“最为难工”、“自有一种风格”显然也是与诗比较相对而言。还有相传为陈师道《后山诗话》中的一段话:“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今代词手,惟秦七,黄九尔,唐诸人不逮也。”[5]这段评论也提出了词“本色”概念。从这些评论,我们可以看出人们对词的体性、诗词差异等问题已普遍关注,且也有所探讨。李清照的《词论》,把他们的这些有关诗词之别的朦胧经验感受和零星见解发展成了明确的理性认识和较为系统的本色理论,是对时代理论的继承和概括,具体表现在她对词的音乐性和审美的论述上。
在音乐方面,《词论》提出明确提出词须协律的要求,严分诗词在音乐方面的区别 提出诗文的创作依据平侧的格律标准,而填词则须有五音、五声、六律、清浊轻重的诸多音律规范,两者之间井水不犯河水, 彼此无甚关联,并举出《声声慢》、《雨中花》等词牌为例,说明它们都有各自严格的词体音律标准,倘若依据平侧的诗文格律来界定,则会混淆不清。如果像王安石、曾巩诸人把诗文格律照搬到填词当中,便会“ 人必绝倒,不可读也”。李清照提出此说, 就是要维护词的合乐可歌的外在特性,并且以此为依据,确立词体独特的地位和价值。
正如吴雄和先生在《唐宋词通论》中所说“《词论》为词溯源至开元、天宝间的乐府、声诗,此后流变日繁,协律却始终是词别于诗的首要特点。”[6]李清照认为,词比诗要更严于音律,这也是符合词的特点。诗和词都要有音乐性。近体诗虽然出于音声和谐的要求而讲究平仄格律,但它毕竟只诉诸于口诵;而词是歌词,可歌性是它的特点,因而,词在写作时,对汉字声调上的要求自然会更细,更严。李清照在《词论》中强调“盖诗文分平侧,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就是为了词能协律、可歌。虽然词的音乐性,由于年代久远和词谱的散佚,今天已不太容易考证,但却不能忽视它的重要性。
在对于词的审美艺术要求上,《词论》要求词要重铺叙、尚典重,既有情致又重故实,有富贵态:“晏苦无铺叙,贺苦少典重;秦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黄即尚故实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价自减半矣。”词须有情致,这是传统的词学家们所恪守的一个词学观念,但重铺叙、尚典重、有故实等理论是在宋朝特定的文学背景下产生的。唐五代到宋初,词是不大讲究故实的。到宋朝中期,“ 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的做法,在诗人中流传。特别是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大倡“点铁成金”,认为“诗词高胜要从学问中来”,于是讲究故实形成一种风气,这种风气不能不影响到词。这种“从学问中来”的词,自然是典重的。李清照主张重典重、尚故实,可以说是受当时文坛风气的影响。从李清照的创作实践来看,她并不主张写词像写诗那样,大用其“故实”,她是主张在词的创作中借鉴宋代诗人们的经验而已,李清照首次明确提出,这是对传统词学观的发展和超越。
综上所述,《词论》在特殊的理论背景下,实现了对传统词学观念的继承和超越,以本体论的澄明之思结束了当时词坛的混沌现状,鲜明的提出了“词别是一家”的观点,发了词体独特的审美特性,捍卫了词的独立地位。只有对其产生的理论背景有所把握,我们才能对其在词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意义作出更公允的评价。
参考文献:
[1]唐圭章,《词话丛编》中华书局2005年10月版
[2]徐培军,《李清照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四月版
[3]陈良运,《中国历代词学论著选》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4]吴熊和,《唐宋词通论》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3月第二版
[5]何文焕,《历代诗话》中华书局2004年9月版
[6]游国恩,《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七月版
[7]韦海英,《江西诗派诸家考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版
作者简介:黄艳,女,贵州大学人文学院2008级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唐宋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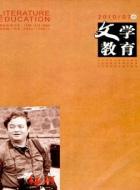
- 从“第二性”到四季斑驳 / 刁俊娅
- 我抓住了两个世界 / 姜广平
- 张爱玲缺失性体验对《小团圆》的影响 / 张茫茫
- 简析安娜与繁漪的爱情悲剧 / 魏淑源 吴志钟
- 重耳在流亡中成为为一代霸主的原因 / 刘煜超
- 扬州“八怪”新考 / 刘 景
- 哈代的宗教思想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响 / 王美霞
- 论王统照早期小说的苦难主题 / 丁文英
- 浅析张爱玲作品的特点及其艺术成就 / 陈 光
- 余秋雨文化散文的语言特色赏析 / 黄益菜
- 高师毕业生就业情况分析与对策研究 / 谢素华 黄 鹂
- 挣扎和觉醒 / 唐丽丽
- 简洁的叙述 含蓄的象征 / 陶 凤
- 科学发展观视域下的高校学生工作探析 / 唐丽洁 宋 冰
- 困境中的苦闷选择 / 杜 静
- 浅析《死水》中的丑 / 路宏建
- 释“东西” / 何 娜
- 关于森田疗法的理论及在实践中的运用 / 丁一家
- 南方,故乡 / 郭 华
- 欧.亨利小说中的现实主义及其表现方式 / 张 磊
- 亦舒小说特点初探 / 刘丽娜
- 探析产品障碍设计的设计方式 / 刘秋云
- 三岛由纪夫诡异的文学世界与奇异的心理世界 / 丁跃斌
- 坚守传统文化精神 / 刘爱军
- “两型社会”建设背景下高职人才培养浅析 / 王 鹰
- 浅谈大学生创业素质的含义和内容 / 卢明霞
- 浅谈“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 / 张晓姗
- 关于高校学生管理的几点思考 / 官孙平
- 试析大学的形象建设 / 李玲玲
- 对打工文学的再认识 / 敖荣祥
- 材料学专业本科生课程创新能力的探索 / 王献彪
- 大学生素质拓展训练体系构建 / 张 恒 周 欣
- 一位水与钢铸就的女性 / 张亚利
- 城市规划展览馆展示的空间设计探悉 / 胡国梁
- 薇拉.凯瑟笔下的生态乌托邦 / 牟 佳
- 刍议大学生综合素质 / 牟道富
- 中等职业学校体育对学生心理发展的作用 / 李玉萍
- 略论李清照《词论》的词学史意义 / 黄 艳
- 新时期公民借助媒体引发的新问题探究 / 韦璐明
- 新形式下高校基层管理人员应具备的素质 / 王 瑛 郭亦鹏
- 浅议大学生消费观的培养 / 穆冬梅
- 高职英语口语课堂中的愉快教学 / 温 燕
- 浅析影响青少年体质下降的因素 / 高 林
- 试论欧美关系的新发展 / 郭石磊 苏 薇
- 浅谈新闻翻译中几个需注意的问题 / 王 玉
- 如何提高非英语专业大学生的英语听力理解能力 / 欧 丹 李何赟
- 运用网络,提高小学英语课堂效率 / 马 丹
- 再论英汉情感隐喻之共性 / 王 眉
- 从中西文化差异谈大学英语教学 / 左 健
- 目前农村小学开设英语课的现状及对策 / 邓建兰
- 高职英语教学组织形式探究 / 李媛慧
- 浅议对外汉语语音教学 / 刘 娟
- 浅谈歌唱中的情感 / 刘伟平
- “依赖表现”的中日对照 / 谢 群
- 大学英语课堂生生互动模式的探索 / 吴 西
- 浅谈中学生音乐欣赏能力的培养 / 张亚静
- 让学生制作出更好的陶艺作品 / 万 莉
- 中职《商务英语函电》教学思考与策略探究 / 古兰波
- 略谈数码时代的美术基础教学 / 谭细雄
- 浅谈小学美术创造力的培养 / 黄 韬
- 职中生舞蹈训练中的品质锻炼 / 何 娟
- 中外合作办学中的英语教学简论 / 杨 婕
- 手绘效果图课程中的马克笔植物画法 / 李 亮
- 如何有效的练习练习曲 / 于 岚
- 浅析钢琴学习中家长的作用 / 李 佳
- 非语言交际在外语教学中若干应用的思考 / 米 乐
- 任务驱动法在文科教学中的有效应用 / 吕宪栋 刘 伟 钟 健
- 知—情结合:优化高职英语课堂的新思路 / 张晓红
- 美术教育中加强中国传统美术教育的重要意义 / 黎 亮
- 医学英语教学现状及改革探讨 / 梁 洁 叶 砾 颜仕尧
- 中学生作文互动评改实践例谈 / 刘灿伟
- 新课改下初中语文教学模式反思 / 池灵巧
- 如何在课堂中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的能力 / 陈穗芳
- 浅谈中小学汉语言文学教学 / 张有英
- 加强学校管理促进教育发展 / 唐国玉
- 浅谈兴趣的培养\课堂教学及课内外结合 / 乐水英
- 在阅读教学中寻求美 / 陆丽娟
- 丰富语言积累培养健康情感 / 吕小勇
- 背景知识架构的特异性在阅读教学中的运用 / 张 晨
- 浅谈小学高年级语文复习教学 / 王 申
- 再谈语文课堂人文素养的养成教学 / 李宗轩
- 让语文教学插上信息技术的双翼 / 刘文捷
- 探讨“因材施教”的几个问题 / 唐 亮
- 浅谈中学思想政治教育新思路 / 李苗苗
- 素质教育与语文教学 / 方 杰
- 和谐社会视域下的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 / 王 娟 庞明珍
- 从图式理论到诗歌教学的“4321”模型 / 王 春
- 守恒法在化学计算题中的应用 / 杨先芳 李小刚
- 高职广告设计课程中创意思维运用的教学探索 / 杨 帆
- 中学思想政治课如何实施素质教育 / 丁 霞
- 随机教育在中职德育工作中的实施 / 刘长春
- 如何培养学生的诚信观念 / 吴功学
- 浅谈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 罗中春
- 学导式教学模式在健美操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 招惠芬 林昭绒
- 提高小学生计算能力的实践与思考 / 邝四莲
- 提高农村学校教育教学质量之我见 / 曹登玉
- 浅谈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管理 / 崔 娜
- 运用电教媒体创设乐学氛围 / 秦芳兰
- 浅谈高校辅导员在班级建设中的引导作用 / 彭 斌
- 信息技术在服装设计教学中的运用 / 刘文英
- 学习兴趣促使学习习惯的形成 / 杨丽玲
- 小议怎样上好一堂信息技术课 / 秦秀丽
- 浅谈孟子的德育思想 / 任成华
- 如何转变教师在体育教学中的观念 / 李 兵
- 提高学习Phot..op的兴趣几个途径 / 陈周强
- 论高中政治教学中的创新培养 / 谭炳辉
- 纽曼高等教育思想浅析 / 马露奇
- 激励理论在学校体育教育管理中的运用 / 漆 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