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文学教育·中旬版 2010年第7期
ID: 153448
文学教育·中旬版 2010年第7期
ID: 153448
对打工文学的再认识
◇ 敖荣祥
[摘要]打工文学这一概念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被提出以来,人们对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就一直意见不一。本文在以往论者的基础上,对打工文学的概念及其内涵和外延作进一步的论述,并将打工文学纳入广阔的改革开放大潮的文化语境之中研究,阐明打工作家对于打工者内部“身份自我认同”的重要性。
[关键词]打工文学;农民工;底层社会
在新世纪的文坛上,打工文学的创作渐成气候,并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批评与创作之间形成了积极而持续的互动,使这一现象成为当下一股重要的文学思潮。如何讲述“底层的故事”已经引起了学界的广泛讨论,这是新世纪以来当代中国一个重要的文学命题。
然而,打工文学这一概念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被提出以来,人们对这一概念的内涵于外延的界定,就一直意见不一。文学评论家白烨认为“必须是打工者群体写的,才算‘打工文学’作品。”[1]与这种观点相类似的是雷达,他认为“‘打工文学’是以打工者作者为主题的描写都市生活和经验的。”[1]但李敬泽对此持不同意见,他认为如果仅仅把打工文学看作是打工者自己写的文学在学理上讲不通,他认为“将‘打工文学’仅看作打工者创作的文学,好像我们过去认为无产阶级文学一定要无产阶级抒写一样,是极其狭隘的。”[1]洪志刚认为打工文学应该是一个题材的概念,这样界定可能比较科学,他认为“既包括打工者的创作的文学,也包括作家写打工生活的文学。”[1]只要是反映打工生活的作品,无论谁写的,洪志刚认为都可以纳入“打工文学”的范畴。深圳市文联副主席杨宏海给打工文学下的定义是:“‘打工’是广东方言,‘打工文学’是指反映‘打工’这一社会群体生活的文学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报告文学、散文、剧作等各类文学体裁。从广义上讲,打工文学既包括打工者自己的文学创作,也包括一些文人作家创作的以打工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但如果要对打工文学做一个稍为严格的界定,那么我认为所谓打工文学主要是指由下层打工者自己创作的以打工生活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其创作范围主要在南中国沿海开放城市。”[2]王祥夫则认为:“打工文学是由内容决定而不是作家的身份决定”[3]上述观点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打工文学的特点。从以上观点比较,杨宏海对打工文学的理解是似乎比较完整,但该概念有两个问题并没说清楚。一是地域限定问题。在我国其他地方而不是沿海开放城市创作的作品算不算打工文学?二是作者的身份含糊不清,这个身份的理解对于打工文学史相当重要的。“下层打工者”与“一些文人作家”如何界定?原来是“下层打工者”后来成为“文人作家”的作者又如何归类?“下层打工者”指的又是哪些?是指 “蓝领”工人?白领算不算?
笔者认为对地域限定并不重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不仅仅在沿海开放城市有打工者,在我国北部、东部也同样存在打工者,打工文学并不止沿海开放城市可以拥有,只是这个地方时最早产生打工文学或者打工作品比较多罢了。其次是作者身份问题,有的论者觉得身份并不重要(如前面李敬泽和王祥夫的观点),需要指出的是,打工者内部也有很大的差别的,在大型国企中担任高级管理人员和那些底层的、靠出卖体力劳动的打工者差异是巨大的。打工文学与以前写的《包身工》不同,它强调的是打工者的心路历程、他们的遭遇与命运,是打工者自己写自己的真实体验,它体现了一种底层打工者的自我关怀和自我认同,离开这一身份,很难得到打工者内部的共鸣。很难想象,一个年薪千万元的大型国企老总写出来的文学作品也能被称为“打工文学”。正如打工诗人许强说“在子夜里没有流过泪的人,不是真正的打工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打工者的身份显得尤其重要了,指的就是底层从事体力劳动的群体。至于由“下层打工者”后来成为“文人作家”的作者,只能说其曾经是打工作家。
打工诗人郑小琼的《铁·塑料厂》,充满了对底层打工者的同情,此文获得了《人民文学》杂志颁发的“新浪潮散文奖”。郑小琼笔下打工文学中的工人形象,不再是以往工人阶级以主人公的形象出现在作品中,这些打工者,生活在这个城市,却不是这里的主人,他们为了生活,失去了尊严,受到老板的冷眼。他们“紧张、不满、 劳作、奋进,愤怒着和期待着的这样的一个群体,他们一旦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出现在打工文学作品中,他们在精神不能不大大有别于建国以来截止于八十年代初期的任何时期的农民的文学形象。这些进城打工的农民兄弟,从来没有这么自由过也从来没有这样失落过?一旦脱离了土地的束缚,脱离了农村政权的约束与农村政权给他们的某种保护,在精神上的四顾茫然和无奈进取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不得不翻开的新的一页的主要内容,这就是打工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学最大的启示和贡献。” [3]现代文学史上有不少作家涉足了底层民众悲惨生活题材,然而因为他们不是从这个阵营而来,没有与生俱来的情感依托,他们与底层民众之间有的只是知识分子对社会底层人物的同情和怜悯,要么就像鲁迅和闰土之间有一层“厚障壁”,要么就像鲁迅对阿Q那样“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郑小琼的生命叙事,却饱含着深切的人文关怀和打工身份的自我认同。从这个层面上说,打工作家的身份尤为重要,它决定了打工者内部的“自我认同”。打工文学所揭示的矛盾是城乡矛盾,但不再是地域二元的对立而是在城市一元展开,展现出打工者渴望融入城市却被现实拒斥的局外生存状态,塑造了生活艰辛努力拼搏的打工者群体形象和心理失衡下的行为失范个体。在叙事中打工作家多采用经验叙述和内视角的方式,作品中宣泄着打工者生存的艰难感受和欲望诉求。打工作家如果不发出这样的声音,底层劳动者或许就要沦为时代火车的无声燃料;如果不去感受那份耻辱感,我们这个时代可能就要忘记那份耻辱。因此,打工文学的创作呈现出“底层写”和“写底层”两种不同的写作方式,作为出身底层的打工作家的创作是以打工者群体代言的方式,坚守着感情体验的倾诉,拒绝底层“被改写”的书写状态。文学界也欣喜地发现了来自社会底层的这股表达力量,记录了那些原本被遮蔽的生活经验。一批打工作家的出现,可以看作新世纪中国文坛的重大收获之一,其所具有的社会学价值和美学意义是相当突出的
打工文学自诞生以来,尽管具有时空超越性的作品相对匮乏,有影响力的作品还不多,但来自底层的打工作家奉献出很多贴近生活的现实主义作品,打工作家不再站在知识分子高高在上的启蒙立场去“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是融入自己的血汗和体温,亲身感受生产线上的悲欢离合,发出了底层生命的呐喊。作者与读者的人数且在日趋增长,大批身在流水线作业的工人拿起笔参与文学创作,涌现了林坚、张伟明、安子、周崇贤、黎志扬、黄秀萍、谭伟文、郭海鸿、海珠、郑小琼、柳冬抚等大批打工作家,他们的作品推进了打工文学的发展,也开始引起传媒与影视界的关注。在这个底层声音越来越弱小的今天,打工作家的出现,无疑让人感到欣慰,“底层”作家们用敏感的文学化的心灵,去测试打工生活的艰辛和残忍。而他们的声音得以传出来,恰恰也反映了我们这个社会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所展现出来的包容性,也反映了社会主流意识开始对农民工的关心,这也是打工文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
参考文献:
[1]黄咏梅.打工文学:在爱与痛的边缘徘徊[N].羊城晚报,2005-07-30.
[2]杨宏海.打工文学备忘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3-4.
[3]王祥夫.我看打工文学[J].文艺争鸣,2010(4)
作者简介:敖荣祥,东莞理工学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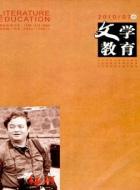
- 从“第二性”到四季斑驳 / 刁俊娅
- 我抓住了两个世界 / 姜广平
- 张爱玲缺失性体验对《小团圆》的影响 / 张茫茫
- 简析安娜与繁漪的爱情悲剧 / 魏淑源 吴志钟
- 重耳在流亡中成为为一代霸主的原因 / 刘煜超
- 扬州“八怪”新考 / 刘 景
- 哈代的宗教思想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响 / 王美霞
- 论王统照早期小说的苦难主题 / 丁文英
- 浅析张爱玲作品的特点及其艺术成就 / 陈 光
- 余秋雨文化散文的语言特色赏析 / 黄益菜
- 高师毕业生就业情况分析与对策研究 / 谢素华 黄 鹂
- 挣扎和觉醒 / 唐丽丽
- 简洁的叙述 含蓄的象征 / 陶 凤
- 科学发展观视域下的高校学生工作探析 / 唐丽洁 宋 冰
- 困境中的苦闷选择 / 杜 静
- 浅析《死水》中的丑 / 路宏建
- 释“东西” / 何 娜
- 关于森田疗法的理论及在实践中的运用 / 丁一家
- 南方,故乡 / 郭 华
- 欧.亨利小说中的现实主义及其表现方式 / 张 磊
- 亦舒小说特点初探 / 刘丽娜
- 探析产品障碍设计的设计方式 / 刘秋云
- 三岛由纪夫诡异的文学世界与奇异的心理世界 / 丁跃斌
- 坚守传统文化精神 / 刘爱军
- “两型社会”建设背景下高职人才培养浅析 / 王 鹰
- 浅谈大学生创业素质的含义和内容 / 卢明霞
- 浅谈“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 / 张晓姗
- 关于高校学生管理的几点思考 / 官孙平
- 试析大学的形象建设 / 李玲玲
- 对打工文学的再认识 / 敖荣祥
- 材料学专业本科生课程创新能力的探索 / 王献彪
- 大学生素质拓展训练体系构建 / 张 恒 周 欣
- 一位水与钢铸就的女性 / 张亚利
- 城市规划展览馆展示的空间设计探悉 / 胡国梁
- 薇拉.凯瑟笔下的生态乌托邦 / 牟 佳
- 刍议大学生综合素质 / 牟道富
- 中等职业学校体育对学生心理发展的作用 / 李玉萍
- 略论李清照《词论》的词学史意义 / 黄 艳
- 新时期公民借助媒体引发的新问题探究 / 韦璐明
- 新形式下高校基层管理人员应具备的素质 / 王 瑛 郭亦鹏
- 浅议大学生消费观的培养 / 穆冬梅
- 高职英语口语课堂中的愉快教学 / 温 燕
- 浅析影响青少年体质下降的因素 / 高 林
- 试论欧美关系的新发展 / 郭石磊 苏 薇
- 浅谈新闻翻译中几个需注意的问题 / 王 玉
- 如何提高非英语专业大学生的英语听力理解能力 / 欧 丹 李何赟
- 运用网络,提高小学英语课堂效率 / 马 丹
- 再论英汉情感隐喻之共性 / 王 眉
- 从中西文化差异谈大学英语教学 / 左 健
- 目前农村小学开设英语课的现状及对策 / 邓建兰
- 高职英语教学组织形式探究 / 李媛慧
- 浅议对外汉语语音教学 / 刘 娟
- 浅谈歌唱中的情感 / 刘伟平
- “依赖表现”的中日对照 / 谢 群
- 大学英语课堂生生互动模式的探索 / 吴 西
- 浅谈中学生音乐欣赏能力的培养 / 张亚静
- 让学生制作出更好的陶艺作品 / 万 莉
- 中职《商务英语函电》教学思考与策略探究 / 古兰波
- 略谈数码时代的美术基础教学 / 谭细雄
- 浅谈小学美术创造力的培养 / 黄 韬
- 职中生舞蹈训练中的品质锻炼 / 何 娟
- 中外合作办学中的英语教学简论 / 杨 婕
- 手绘效果图课程中的马克笔植物画法 / 李 亮
- 如何有效的练习练习曲 / 于 岚
- 浅析钢琴学习中家长的作用 / 李 佳
- 非语言交际在外语教学中若干应用的思考 / 米 乐
- 任务驱动法在文科教学中的有效应用 / 吕宪栋 刘 伟 钟 健
- 知—情结合:优化高职英语课堂的新思路 / 张晓红
- 美术教育中加强中国传统美术教育的重要意义 / 黎 亮
- 医学英语教学现状及改革探讨 / 梁 洁 叶 砾 颜仕尧
- 中学生作文互动评改实践例谈 / 刘灿伟
- 新课改下初中语文教学模式反思 / 池灵巧
- 如何在课堂中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的能力 / 陈穗芳
- 浅谈中小学汉语言文学教学 / 张有英
- 加强学校管理促进教育发展 / 唐国玉
- 浅谈兴趣的培养\课堂教学及课内外结合 / 乐水英
- 在阅读教学中寻求美 / 陆丽娟
- 丰富语言积累培养健康情感 / 吕小勇
- 背景知识架构的特异性在阅读教学中的运用 / 张 晨
- 浅谈小学高年级语文复习教学 / 王 申
- 再谈语文课堂人文素养的养成教学 / 李宗轩
- 让语文教学插上信息技术的双翼 / 刘文捷
- 探讨“因材施教”的几个问题 / 唐 亮
- 浅谈中学思想政治教育新思路 / 李苗苗
- 素质教育与语文教学 / 方 杰
- 和谐社会视域下的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 / 王 娟 庞明珍
- 从图式理论到诗歌教学的“4321”模型 / 王 春
- 守恒法在化学计算题中的应用 / 杨先芳 李小刚
- 高职广告设计课程中创意思维运用的教学探索 / 杨 帆
- 中学思想政治课如何实施素质教育 / 丁 霞
- 随机教育在中职德育工作中的实施 / 刘长春
- 如何培养学生的诚信观念 / 吴功学
- 浅谈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 罗中春
- 学导式教学模式在健美操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 招惠芬 林昭绒
- 提高小学生计算能力的实践与思考 / 邝四莲
- 提高农村学校教育教学质量之我见 / 曹登玉
- 浅谈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管理 / 崔 娜
- 运用电教媒体创设乐学氛围 / 秦芳兰
- 浅谈高校辅导员在班级建设中的引导作用 / 彭 斌
- 信息技术在服装设计教学中的运用 / 刘文英
- 学习兴趣促使学习习惯的形成 / 杨丽玲
- 小议怎样上好一堂信息技术课 / 秦秀丽
- 浅谈孟子的德育思想 / 任成华
- 如何转变教师在体育教学中的观念 / 李 兵
- 提高学习Phot..op的兴趣几个途径 / 陈周强
- 论高中政治教学中的创新培养 / 谭炳辉
- 纽曼高等教育思想浅析 / 马露奇
- 激励理论在学校体育教育管理中的运用 / 漆 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