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文学教育·中旬版 2010年第7期
ID: 153434
文学教育·中旬版 2010年第7期
ID: 153434
浅析《死水》中的丑
◇ 路宏建
[摘要]《死水》充分体现了闻一多的艺术创造力。在诗中,闻一多引丑入诗,用美中写丑的方法,把对丑的否定性情感熔铸在美的意象中,开拓了新诗表现的新领域。本文从丑入手,分析了诗人在《死水》创作中丑的形象性和象征性;美丑对举,化丑为美;美为表象,丑是本质等艺术手法和创作思想。
[关键词]诗歌;死水;艺术方法;分析
《死水》是闻一多的代表作,充分体现了闻一多的艺术创造力。在诗中,闻一多引丑入诗,用美中写丑的方法,把对丑的否定性情感熔铸在美的意象中,从美的意象中表现出诗人憎恶丑的激愤之情,使外在形象和内在情感相反相成,融为一体,开拓了新诗表现的新领域。
一、丑的形象性和象征性
诗歌用形象说话。那么,诗人为什么选取一沟“死水”入诗呢?诗人的好友饶孟侃在《诗词二题》中回忆说:“《死水》一诗,即君偶见西单二龙坑南端一臭水沟有感而作。”闻一多回到思念已久的祖国,目睹腐败、丑恶的社会现实,自然地联想到了这一“臭水沟”,借以宣泄心中的怨愤。因此,《死水》选了一系列可谓丑的形象。如:一沟死水、破铜烂铁、剩菜残羹、油腻、霉菌、白沫、花蚊等,这些形象,是诗人对旧中国黑暗现实细致形象的再现,典型性地表现了闻一多对旧中国的认识,抒发了诗人希望祖国新生的强烈爱国情感。
《死水》通篇使用象征手法,诗人选取的每一个丑的形象,既是写实,又具有象征性。“一沟绝望的死水”象征在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统治下中国的黑暗社会现实;“破铜烂铁”、“剩菜残羹”象征当时一切腐朽的事物;“绿酒”、“白沫”象征当时社会的肮脏和腐朽;“花蚊”、“青蛙”象征着那个社会的同流合污者和歌颂者。诗人将“死水”一系列形象和内涵的意蕴巧妙地融为一体,使诗的内涵更加丰富,意味更加隽永。
二、美丑对举,化丑为美
闻一多早在1922年写的《冬夜评论》中,就明确地指出:“丑在艺术上固有相当的地位,但艺术的神技应能使‘恐怖’穿上‘美’底一切的精致,同时又不失其要质。”闻一多强调要给丑恶穿上美的精致的外衣,而这正是诗人的艺术神技。一沟沉寂的死水,浑浊不堪,腐烂发臭,破铜烂铁充斥其中,残羹剩菜倒入其内。水面上漂浮着油腻的泡沫,滋生着霉菌臭气,飞舞着逐臭的花蚊。这沟不堪入目的死水,真是丑恶之极。但作者没有对丑恶进行自然主义的描写,而是抓住了相反事物之间的特殊关系,捕捉美丑事物之间的相似特征,用艳丽的色彩、华美的物象去点缀、装饰、形容丑的事物,从而经过艺术的修饰、升华,使之进入审美的境界。
例如,诗的第二节,诗人把锈迹斑斑的破铜烂铁说成是绿如翡翠,灿如桃花,把污油腻垢说成是绫罗绸缎,把恶臭难闻的霉菌说成是满天彩霞。诗人对污浊肮脏到了让人绝望的丑陋的描写,采用“翡翠”、“桃花”、“罗绮”、“云霞”这样美好的词语,显然,作者是明知其丑,偏要说美,以美衬丑,形成强烈的对比,使丑恶的事物更能引起人们的憎恶之情,更加令人深恶痛绝。诗歌第三四两节沿袭第二节的写法,把腐臭难闻的死水想象成芳香扑鼻的绿酒,把肮脏腥噪的白沫说成是银光闪闪的珍珠。陶醉于其中的只有追星逐臭的花蚊和恬不知耻,放声“歌唱”的青蛙。诗人用美的表象揭露事物丑的本质,更加反衬出死水的肮脏、丑陋和腐朽。
三、美为表象,丑是本质
在使“死水”披上精致外衣的同时,又不能“失其要质”,即在艺术形式的修饰中不能让客体的丑恶本质消失。一沟“死水”虽然经过艺术处理,从而具有“恶魔之美”,但并不是要求人们去喜欢它、欣赏它,目的使人产生一种审美中的“高贵的反感”,从而达到否定它的审美效果。诗中鲜艳夺目的美象和灿烂纷繁的色彩毕竟不是死水的真相,而是它幻化出的一种令人迷惑的假象。尽管丑恶以“美”的假象巧妙地伪装自己、掩饰自己,但它们仍是死水,“断不是美的所在”。相反,它的假象更能引起人的思索,更能激起情感上的厌恶和理智上的否定,从而促使人们深入地对它进行剖析,使它那丑恶的本质彻底暴露于世。
参考文献:
[1]曹长青,谢文利.诗的技巧[M].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
[2]刘书成.文艺学概论[M].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5.
[3]武汉大学闻一多研究室.闻一多论新诗[Z].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
[4]李玉昆,李滨.中国新诗百首赏析[M].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1.
[5]李泽厚.美的历程[M].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
[6]许霆.闻一多新诗艺术[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
作者简介:宏建(1965—),男,河南郑州人,河南省民政学校讲师、工会主席,大学本科学历,文学学士,主要研究方向:教育管理、中职语文教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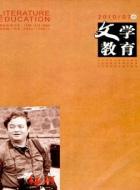
- 从“第二性”到四季斑驳 / 刁俊娅
- 我抓住了两个世界 / 姜广平
- 张爱玲缺失性体验对《小团圆》的影响 / 张茫茫
- 简析安娜与繁漪的爱情悲剧 / 魏淑源 吴志钟
- 重耳在流亡中成为为一代霸主的原因 / 刘煜超
- 扬州“八怪”新考 / 刘 景
- 哈代的宗教思想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响 / 王美霞
- 论王统照早期小说的苦难主题 / 丁文英
- 浅析张爱玲作品的特点及其艺术成就 / 陈 光
- 余秋雨文化散文的语言特色赏析 / 黄益菜
- 高师毕业生就业情况分析与对策研究 / 谢素华 黄 鹂
- 挣扎和觉醒 / 唐丽丽
- 简洁的叙述 含蓄的象征 / 陶 凤
- 科学发展观视域下的高校学生工作探析 / 唐丽洁 宋 冰
- 困境中的苦闷选择 / 杜 静
- 浅析《死水》中的丑 / 路宏建
- 释“东西” / 何 娜
- 关于森田疗法的理论及在实践中的运用 / 丁一家
- 南方,故乡 / 郭 华
- 欧.亨利小说中的现实主义及其表现方式 / 张 磊
- 亦舒小说特点初探 / 刘丽娜
- 探析产品障碍设计的设计方式 / 刘秋云
- 三岛由纪夫诡异的文学世界与奇异的心理世界 / 丁跃斌
- 坚守传统文化精神 / 刘爱军
- “两型社会”建设背景下高职人才培养浅析 / 王 鹰
- 浅谈大学生创业素质的含义和内容 / 卢明霞
- 浅谈“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 / 张晓姗
- 关于高校学生管理的几点思考 / 官孙平
- 试析大学的形象建设 / 李玲玲
- 对打工文学的再认识 / 敖荣祥
- 材料学专业本科生课程创新能力的探索 / 王献彪
- 大学生素质拓展训练体系构建 / 张 恒 周 欣
- 一位水与钢铸就的女性 / 张亚利
- 城市规划展览馆展示的空间设计探悉 / 胡国梁
- 薇拉.凯瑟笔下的生态乌托邦 / 牟 佳
- 刍议大学生综合素质 / 牟道富
- 中等职业学校体育对学生心理发展的作用 / 李玉萍
- 略论李清照《词论》的词学史意义 / 黄 艳
- 新时期公民借助媒体引发的新问题探究 / 韦璐明
- 新形式下高校基层管理人员应具备的素质 / 王 瑛 郭亦鹏
- 浅议大学生消费观的培养 / 穆冬梅
- 高职英语口语课堂中的愉快教学 / 温 燕
- 浅析影响青少年体质下降的因素 / 高 林
- 试论欧美关系的新发展 / 郭石磊 苏 薇
- 浅谈新闻翻译中几个需注意的问题 / 王 玉
- 如何提高非英语专业大学生的英语听力理解能力 / 欧 丹 李何赟
- 运用网络,提高小学英语课堂效率 / 马 丹
- 再论英汉情感隐喻之共性 / 王 眉
- 从中西文化差异谈大学英语教学 / 左 健
- 目前农村小学开设英语课的现状及对策 / 邓建兰
- 高职英语教学组织形式探究 / 李媛慧
- 浅议对外汉语语音教学 / 刘 娟
- 浅谈歌唱中的情感 / 刘伟平
- “依赖表现”的中日对照 / 谢 群
- 大学英语课堂生生互动模式的探索 / 吴 西
- 浅谈中学生音乐欣赏能力的培养 / 张亚静
- 让学生制作出更好的陶艺作品 / 万 莉
- 中职《商务英语函电》教学思考与策略探究 / 古兰波
- 略谈数码时代的美术基础教学 / 谭细雄
- 浅谈小学美术创造力的培养 / 黄 韬
- 职中生舞蹈训练中的品质锻炼 / 何 娟
- 中外合作办学中的英语教学简论 / 杨 婕
- 手绘效果图课程中的马克笔植物画法 / 李 亮
- 如何有效的练习练习曲 / 于 岚
- 浅析钢琴学习中家长的作用 / 李 佳
- 非语言交际在外语教学中若干应用的思考 / 米 乐
- 任务驱动法在文科教学中的有效应用 / 吕宪栋 刘 伟 钟 健
- 知—情结合:优化高职英语课堂的新思路 / 张晓红
- 美术教育中加强中国传统美术教育的重要意义 / 黎 亮
- 医学英语教学现状及改革探讨 / 梁 洁 叶 砾 颜仕尧
- 中学生作文互动评改实践例谈 / 刘灿伟
- 新课改下初中语文教学模式反思 / 池灵巧
- 如何在课堂中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的能力 / 陈穗芳
- 浅谈中小学汉语言文学教学 / 张有英
- 加强学校管理促进教育发展 / 唐国玉
- 浅谈兴趣的培养\课堂教学及课内外结合 / 乐水英
- 在阅读教学中寻求美 / 陆丽娟
- 丰富语言积累培养健康情感 / 吕小勇
- 背景知识架构的特异性在阅读教学中的运用 / 张 晨
- 浅谈小学高年级语文复习教学 / 王 申
- 再谈语文课堂人文素养的养成教学 / 李宗轩
- 让语文教学插上信息技术的双翼 / 刘文捷
- 探讨“因材施教”的几个问题 / 唐 亮
- 浅谈中学思想政治教育新思路 / 李苗苗
- 素质教育与语文教学 / 方 杰
- 和谐社会视域下的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 / 王 娟 庞明珍
- 从图式理论到诗歌教学的“4321”模型 / 王 春
- 守恒法在化学计算题中的应用 / 杨先芳 李小刚
- 高职广告设计课程中创意思维运用的教学探索 / 杨 帆
- 中学思想政治课如何实施素质教育 / 丁 霞
- 随机教育在中职德育工作中的实施 / 刘长春
- 如何培养学生的诚信观念 / 吴功学
- 浅谈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 罗中春
- 学导式教学模式在健美操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 招惠芬 林昭绒
- 提高小学生计算能力的实践与思考 / 邝四莲
- 提高农村学校教育教学质量之我见 / 曹登玉
- 浅谈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管理 / 崔 娜
- 运用电教媒体创设乐学氛围 / 秦芳兰
- 浅谈高校辅导员在班级建设中的引导作用 / 彭 斌
- 信息技术在服装设计教学中的运用 / 刘文英
- 学习兴趣促使学习习惯的形成 / 杨丽玲
- 小议怎样上好一堂信息技术课 / 秦秀丽
- 浅谈孟子的德育思想 / 任成华
- 如何转变教师在体育教学中的观念 / 李 兵
- 提高学习Phot..op的兴趣几个途径 / 陈周强
- 论高中政治教学中的创新培养 / 谭炳辉
- 纽曼高等教育思想浅析 / 马露奇
- 激励理论在学校体育教育管理中的运用 / 漆 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