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文学教育·中旬版 2010年第7期
ID: 153420
文学教育·中旬版 2010年第7期
ID: 153420
简析安娜与繁漪的爱情悲剧
◇ 魏淑源 吴志钟
[摘要]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和曹禺笔下的繁漪这两个艺术形象虽然出于两个不同的国度却有着很大的相似性,是她们存在的相同的男权社会和女性自身的缺陷导致了她们不可避免的悲剧命运。
[关键词]安娜;繁漪;爱情悲剧
重读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与曹禺的《雷雨》,虽然两部作品出于不同国度的两位作家,且两部作品的体裁不同(前者是长篇小说,后者系戏剧作品),但两位女主人公的身世遭际与爱情追求以及最后的悲剧结局却有着惊人的相似性。本文将就这一相似性进行分析比较,进而探讨造成两个女主人公相同的悲剧命运的历史时代原因,以及由于男权文化对女性人格的扭曲而造成的女性自身的缺陷。
一、爱之悲
(一)不幸的家庭生活
如果从高贵的门第、优越的地位和舒适的生活来定义幸福的话,那么安娜和繁漪应该称得上是幸福的。安娜与繁漪都是出身于大家庭,安娜由姑母做主嫁给了一个赫赫有名的部长——卡列宁。而繁漪18年嫁给了大资本家——周朴园。正是这看起来幸福的家庭,却造成了她们终生的不幸。她们在相似的“幸福”家庭中有着相似的不幸生活。安娜的丈夫卡列宁只会玩弄文牍,醉心于官场应酬。在他看来,安娜只是为他生儿育女的工具,陪他出入交际场所的伴侣而已。安娜虽然物质上应有尽有,但精神却是一贫如洗的。
而繁漪的丈夫周朴园是由封建家族的子弟转化为的资本家,他娶了繁漪却不爱她,他们的关系也仅仅是“生了冲儿”,他要求繁漪必须绝对地服从,不服从就被认为有精神病。在这种生活中,繁漪如同一个囚徒,精神严重的受到压抑。
(二)疯狂的爱情追求
她们即使生活在专制的家庭中,呼吸不着一口自由的空气,但她们心中的生命之火却是绝不会被封建牢笼所熄灭的,只要有一点火种,她们便能燃起熊熊大火。[1]
当周萍、偓伦斯基出现时,像一股甘露滋润她们早已干枯的心,她们在心中积蓄已久的被压抑的热情爆发了出来。安娜勇敢的冲破旧的家庭关系,不顾一切地投入了偓伦斯基的怀抱。而繁漪也是置自己的性命、名誉于不顾,以一个后母的身份疯狂的与周萍相爱了。
然而,安娜与繁漪并没有等到真正的爱情。偓伦斯基虽然真心爱过安娜,可渐渐地,他开始为在上流社会失去了地位和前途而感到后悔,便想要抛弃安娜。与偓伦斯基相比,繁漪更加可怜,周萍根本就没有爱过繁漪,他追求繁漪仅仅是为了发泄心中的郁闷,给自己空虚的心灵寻找寄托。他点燃了繁漪心中的火焰又亲手熄灭了它,甚至像他父亲一样抬出封建礼教来压制繁漪,并污蔑她是疯子。
(三)悲惨的人生结局
安娜对于爱情的追求,使自己由上流社会的一个“宠儿”变成了众矢之的,上流社会对她永远关上了大门;她要求离婚,也遭到卡列宁的拒绝。除了爱情,她已别无选择。当安娜发现爱情一去不复返时,毅然投身于滚滚车轮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繁漪则处在一个“母亲不是母亲,情妇不是情妇”的地位,甚至连这样的生活,繁漪也不能拥有,缺乏责任感的周萍离开她、摆脱她,这对繁漪来说无疑是五雷轰顶。面对完结了的爱情,繁漪采取了疯狂的报复,而她也在爱与恨燃尽之后发疯,走到了悲剧命运的尽头。
二、谁之罪?
安娜与繁漪的相似是那么的惊人,但这种相似并不是偶然的。她们代表了这一系列的女性形象。这类女性的悲剧命运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
(一)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任何一幕悲剧的产生都有其时代和社会的因素,安娜和繁漪的悲剧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安娜与繁漪生活的历史时代和环境,都是一个动荡的,正在起着天翻地覆变化的时代。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经过“五四”运动,资产阶级个性解放思潮唤醒了一大批知识女性,她们追求平等的爱。繁漪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中,受过良好的教育,从而使她心中留下了打倒封建专制、要求自由解放的印迹。而19世纪60、70年代是俄国社会的一个转折期,那时“一切都颠倒过来,一切都刚刚开始建立”[2]。旧的制度遭到了剧烈的破坏,俄国的政治、经济、思想观念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旧的封建伦理道德也受到西方资产阶级个性解放、恋爱自由的挑战。安娜就是在这样一个社会大背景下,接受了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精神。
正是有了这些思想的影响,安娜与繁漪都在内心憧憬着自由美好的婚姻。然而现实却是残酷的。不管是在中国还是俄国,男权主义仍占有统治地位。“在父权制社会中,支配群体通过言论来控制现实,他们剥夺了妇女的发言权,使她们长期处于沉默的状态。女性没有话语,因此没有能力按照自己的体验更新解释这个世界。因此一个沉默的群体必然成为被掩埋的群体。”[3]安娜和繁漪就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在婚恋方面,封建婚姻制度、门第观念、父母之命仍然占据着优势,她们没有任何的主动权。安娜与繁漪这两个心比天高的少女连挣扎一下都没有,便成为了封建婚姻制度的牺牲品。[4]
虽然被包办了婚姻,但她们内心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并没有被磨灭,而是更加激起了她们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对自由的渴望。当她们为了追求自由爱情而抗争时,现实又一次给了她们以沉重的打击。在中国封建社会,“男尊女卑”是数千年来盘踞在广大国民意识深层的观念。[5]女人只能顺从,对自己遭遇的屈辱只能忍受,不能有半点的反抗,对繁漪这种红杏出墙、乱伦的行为,简直是大逆不道。而安娜反叛了宗法制度,背叛了丈夫和儿子,被人们认为是不道德的,连正常社交都不能参加,更别提离婚,争取合法地位了。
就是这样一次一次美好的理想与男权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现实的冲突把安娜与繁漪最终推向了死亡与疯狂。
(二)女性自身的缺陷
拜伦曾说过:“男人的爱情是男人的一部分,女人的爱情是女人生命的整个存在”。这句名言,可以说是一针见血地道出了男女两性对爱情的不同心态。
安娜和繁漪的悲剧从她们自身来看,就是她们在追求爱情,追求自我的过程中,把自己的全部感情和整个生命都奉献给了爱情,把她的爱情看作是她们的“生命整个的存在”,而渥伦斯基和周萍则把他的爱情看作为他们的“生命的一部分”。
安娜一再申明“我要爱情,我要生活”,这就意味着她将爱情和美好生活等同起来,把追求爱情当作生活全部意义,因而使得她的生活除了爱情之外别无他求。她全部的赌注都押在渥伦斯基身上,而这一次更把安娜往深渊中推了一把,最终导致不可避免地走向毁灭的悲剧命运。
繁漪也是为爱情付出了一切,为了爱情一再的妥协。把自己弄地母亲不像母亲,情人不像情人,当她得知周萍不爱她时,强忍着周萍厌恶的态度和对自己感情、尊严的伤害,乞求周萍:“带我离开这儿,日后,甚至你要把四凤接来一块住,我都可以,只要,只要你不离开我”[6]“只要你不离开我”——这是繁漪唯一的要求,为了这个要求,她甚至容忍排他的感情中出现第三者。最后知道无法挽回周萍的心,她疯狂的报复,复仇的同时也毁灭了自己。
安娜与繁漪的相似经历说明了这种悲剧实际上是一个时代追求自由与个性解放的女性的悲剧,而这种悲剧又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这类悲剧是父权制社会制度和男权文化观念所植根于女性心灵深处甚至潜意识中的自卑、依附和爱情迷狂所造成的。
参考文献:
[1]曹禺.雷雨序 [M].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1936:9.
[2]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 [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78,356,16.
[3]康国正.女权主义与文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87.
[4] 刘慧英.走出男权的樊篱[M].北京: 三联出版社,1995:68-73.
作者简介:魏淑源(1987—), 女,汉族,河南平顶山人,平顶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助教。
吴志钟(1980—),男,汉族,河北卢龙人,平顶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助教,硕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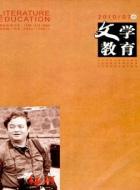
- 从“第二性”到四季斑驳 / 刁俊娅
- 我抓住了两个世界 / 姜广平
- 张爱玲缺失性体验对《小团圆》的影响 / 张茫茫
- 简析安娜与繁漪的爱情悲剧 / 魏淑源 吴志钟
- 重耳在流亡中成为为一代霸主的原因 / 刘煜超
- 扬州“八怪”新考 / 刘 景
- 哈代的宗教思想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响 / 王美霞
- 论王统照早期小说的苦难主题 / 丁文英
- 浅析张爱玲作品的特点及其艺术成就 / 陈 光
- 余秋雨文化散文的语言特色赏析 / 黄益菜
- 高师毕业生就业情况分析与对策研究 / 谢素华 黄 鹂
- 挣扎和觉醒 / 唐丽丽
- 简洁的叙述 含蓄的象征 / 陶 凤
- 科学发展观视域下的高校学生工作探析 / 唐丽洁 宋 冰
- 困境中的苦闷选择 / 杜 静
- 浅析《死水》中的丑 / 路宏建
- 释“东西” / 何 娜
- 关于森田疗法的理论及在实践中的运用 / 丁一家
- 南方,故乡 / 郭 华
- 欧.亨利小说中的现实主义及其表现方式 / 张 磊
- 亦舒小说特点初探 / 刘丽娜
- 探析产品障碍设计的设计方式 / 刘秋云
- 三岛由纪夫诡异的文学世界与奇异的心理世界 / 丁跃斌
- 坚守传统文化精神 / 刘爱军
- “两型社会”建设背景下高职人才培养浅析 / 王 鹰
- 浅谈大学生创业素质的含义和内容 / 卢明霞
- 浅谈“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 / 张晓姗
- 关于高校学生管理的几点思考 / 官孙平
- 试析大学的形象建设 / 李玲玲
- 对打工文学的再认识 / 敖荣祥
- 材料学专业本科生课程创新能力的探索 / 王献彪
- 大学生素质拓展训练体系构建 / 张 恒 周 欣
- 一位水与钢铸就的女性 / 张亚利
- 城市规划展览馆展示的空间设计探悉 / 胡国梁
- 薇拉.凯瑟笔下的生态乌托邦 / 牟 佳
- 刍议大学生综合素质 / 牟道富
- 中等职业学校体育对学生心理发展的作用 / 李玉萍
- 略论李清照《词论》的词学史意义 / 黄 艳
- 新时期公民借助媒体引发的新问题探究 / 韦璐明
- 新形式下高校基层管理人员应具备的素质 / 王 瑛 郭亦鹏
- 浅议大学生消费观的培养 / 穆冬梅
- 高职英语口语课堂中的愉快教学 / 温 燕
- 浅析影响青少年体质下降的因素 / 高 林
- 试论欧美关系的新发展 / 郭石磊 苏 薇
- 浅谈新闻翻译中几个需注意的问题 / 王 玉
- 如何提高非英语专业大学生的英语听力理解能力 / 欧 丹 李何赟
- 运用网络,提高小学英语课堂效率 / 马 丹
- 再论英汉情感隐喻之共性 / 王 眉
- 从中西文化差异谈大学英语教学 / 左 健
- 目前农村小学开设英语课的现状及对策 / 邓建兰
- 高职英语教学组织形式探究 / 李媛慧
- 浅议对外汉语语音教学 / 刘 娟
- 浅谈歌唱中的情感 / 刘伟平
- “依赖表现”的中日对照 / 谢 群
- 大学英语课堂生生互动模式的探索 / 吴 西
- 浅谈中学生音乐欣赏能力的培养 / 张亚静
- 让学生制作出更好的陶艺作品 / 万 莉
- 中职《商务英语函电》教学思考与策略探究 / 古兰波
- 略谈数码时代的美术基础教学 / 谭细雄
- 浅谈小学美术创造力的培养 / 黄 韬
- 职中生舞蹈训练中的品质锻炼 / 何 娟
- 中外合作办学中的英语教学简论 / 杨 婕
- 手绘效果图课程中的马克笔植物画法 / 李 亮
- 如何有效的练习练习曲 / 于 岚
- 浅析钢琴学习中家长的作用 / 李 佳
- 非语言交际在外语教学中若干应用的思考 / 米 乐
- 任务驱动法在文科教学中的有效应用 / 吕宪栋 刘 伟 钟 健
- 知—情结合:优化高职英语课堂的新思路 / 张晓红
- 美术教育中加强中国传统美术教育的重要意义 / 黎 亮
- 医学英语教学现状及改革探讨 / 梁 洁 叶 砾 颜仕尧
- 中学生作文互动评改实践例谈 / 刘灿伟
- 新课改下初中语文教学模式反思 / 池灵巧
- 如何在课堂中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的能力 / 陈穗芳
- 浅谈中小学汉语言文学教学 / 张有英
- 加强学校管理促进教育发展 / 唐国玉
- 浅谈兴趣的培养\课堂教学及课内外结合 / 乐水英
- 在阅读教学中寻求美 / 陆丽娟
- 丰富语言积累培养健康情感 / 吕小勇
- 背景知识架构的特异性在阅读教学中的运用 / 张 晨
- 浅谈小学高年级语文复习教学 / 王 申
- 再谈语文课堂人文素养的养成教学 / 李宗轩
- 让语文教学插上信息技术的双翼 / 刘文捷
- 探讨“因材施教”的几个问题 / 唐 亮
- 浅谈中学思想政治教育新思路 / 李苗苗
- 素质教育与语文教学 / 方 杰
- 和谐社会视域下的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 / 王 娟 庞明珍
- 从图式理论到诗歌教学的“4321”模型 / 王 春
- 守恒法在化学计算题中的应用 / 杨先芳 李小刚
- 高职广告设计课程中创意思维运用的教学探索 / 杨 帆
- 中学思想政治课如何实施素质教育 / 丁 霞
- 随机教育在中职德育工作中的实施 / 刘长春
- 如何培养学生的诚信观念 / 吴功学
- 浅谈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 罗中春
- 学导式教学模式在健美操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 招惠芬 林昭绒
- 提高小学生计算能力的实践与思考 / 邝四莲
- 提高农村学校教育教学质量之我见 / 曹登玉
- 浅谈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管理 / 崔 娜
- 运用电教媒体创设乐学氛围 / 秦芳兰
- 浅谈高校辅导员在班级建设中的引导作用 / 彭 斌
- 信息技术在服装设计教学中的运用 / 刘文英
- 学习兴趣促使学习习惯的形成 / 杨丽玲
- 小议怎样上好一堂信息技术课 / 秦秀丽
- 浅谈孟子的德育思想 / 任成华
- 如何转变教师在体育教学中的观念 / 李 兵
- 提高学习Phot..op的兴趣几个途径 / 陈周强
- 论高中政治教学中的创新培养 / 谭炳辉
- 纽曼高等教育思想浅析 / 马露奇
- 激励理论在学校体育教育管理中的运用 / 漆 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