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文学教育·中旬版 2010年第7期
ID: 153426
文学教育·中旬版 2010年第7期
ID: 153426
论王统照早期小说的苦难主题
◇ 丁文英
[摘要]现代中国的一批文学家对形而上的“人”的本质问题、人类存在的终极问题,以及人性的渊深问题等领域的深层探索、持久询问,是现代中国的一种重要的精神现象。其中,王统照从自身的生命体验和精神需要出发,对人的“存在”、人类存在的终极意义及人的超越性精神追求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索。本文以王统照的早期小说(《春雨之夜》、《霜痕》和长篇小说《一叶》)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小说中的苦难主题。
[关键词]王统照;早期小说;苦难
20世纪初的中国内忧外患,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受西方人本主义启蒙思想的影响,“五四”作家重新审视自我,思考着生存的意义。他们正视人间的苦难,并试图探索出一条精神上的救赎之路。他们从各自不同的生存境遇与精神需要出发,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对人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形而上的思考。其中,王统照在他的早期小说创作中,从自身的生命体验和精神需要出发,对人的“存在”、人类存在的终极意义及人的超越性精神追求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索。
一、对个体生存苦难的观照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文明与灾难交织,一方面“五四”新文化运动给封闭落后的中国带来了文明的曙光,一方面兵祸连年,百姓承受了巨大的苦难,所以表现生存困境就成了那一时期中国文学题中的应有之义。不同作家从他们不同的人生感悟和创作意图出发,对人生困境做着不同的阐释。作为文学研究会的发起成员,王统照自然把探寻的目光投注到个体生命上,在他的早期小说中,描写了许多挣扎在生死线上的小人物,展示了生存的艰难,表达了忧时伤世的情怀。
从1922年起,王统照先后发表了《一栏之隔》、《警钟守》、《湖畔儿语》等小说。用作者自己的话说,“社会情况的描写较多,个人虚幻的情感很不愿意在笔底流露了。”[1](148)《伴死人的一夜》《湖畔儿语》《生与死的一行列》等作品,揭示了下层人物生活的惨状,或写孤儿、寡妇,或写丧失劳动力、无依无靠的老人。最典型的是《湖畔儿语》中的小顺,母亲早已死去,继母无以为生只好在家做起了出卖皮肉的生意。因此每到黄昏,他们父子便游荡在外,父亲到大烟馆鬼混,小顺只能一个人孤零零的在湖边徘徊。然而,不幸接踵而至,父亲又被警察抓走,等待小顺的将是更大的苦难。
关注女性生存的困境是王统照早期小说取材上的一个特点。在王统照的笔下,女性是弱势群体,在父权、夫权等封建伦理下,在恶势力之下,许多女性如风中飘零的黄叶,无力把握自己的命运。《一叶》中的护士云涵,曾有一个和美富裕的家,后来父亲被冤枉致死,家产被人霸占,母亲连气加病,不久吐血身亡。她幸而在教会的中学里毕了业,为了谋生,曾给一个富商做家庭教师。这个人面兽心的富商,利用药力使云涵受到莫大的侮辱,使云涵失去活下去的勇气。《纪梦》里的素君,出身于没落的旗人,父亲无力养家,把她卖给远房亲戚做童养媳,日日受婆婆的辱骂,自己的明天一片黑暗,“于是投湖自尽,毁灭了自己年轻的生命。《遗音》中的“她”,与小学教员真心相爱,为世俗所不容,无奈背井离乡,孤身飘零在外,余生只有在痛苦中度过了。
在作家笔下,人的生存困境常与爱情相关联。王统照以爱情为题材的小说在他的早期创作中占很大比例,如《遗音》、《山道之侧》《钟声》长篇小说《一叶》等。《遗音》写一个小学教师不能与自己心爱的少女结婚,这个孤苦的女性在无奈中离“他”而去,几年后寄来最后一封信,这就是这位教师的得到的最后一封信—“遗音”,此时“他”虽然已有娇妻爱子,但始终忘不了初恋给他带来的伤痛,这似乎成为“他”永远的精神创伤。《鞭痕》里慕侠与曼儿的朦胧的爱情之花就凋谢在动荡的年代里,那道“鞭痕”将永远刻在了曼儿的心中。《钟声》中的T君,爱情的幼苗也被封建家长制所扼杀了。《湖中的月夜》《山道之侧》描写了因爱情破灭而自杀的青年。
二、对个体生存苦难的追问
作家并没有停留在对个体生存困境的表述上,而是把深邃的眼光投向造成这些苦难的根源上。作家用超然的智慧,看到人生困境起源于人自身的弱点。人被异己力量(金钱、权势、贪欲、淫念、暴力欲)所控制,迷失了自我本性,精神扭曲而成非人。这些恶念,有的导致自身悲剧,有的则给他人带来苦难。《雪后》写人的贪欲而导致的战争暴力给纯洁心灵带来的伤害;《沉思》中粗鄙的官吏、自私的记者、虚伪的画家的所作所为,使主人公迷惑不解;《一叶》写家族势力为了财产的问题互相倾轧,最终逼死了天根的父亲;云涵的父亲为小人所害,失去了生命和财产,云涵从此沦为孤儿,后又被恶人糟践。只要这些恶念存在,就会有人间悲剧的发生。《沉思》《一栏之隔》《自然》《在剧场中》等作品都体现了作者对人性的思考。
其次,作家看到了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与冷漠。人与人之间是无法沟通的,即使最亲近的人之间,因隔膜、误解也造成了许多人间悲剧。《沉思》中粗鄙、自私的画家、官吏、甚至自己的恋人,都无法理解琼逸的举动。《山道之侧》中的驴夫无法理解为爱情而死的青年,《自然》中的女主人的感情世界里充满了冷漠和猜忌。“人的心肠,都几乎是冰与铁做成的。” “人谁能彼此作真心的慰藉!”“人们都是有猜疑性的,而且无时不会放射出恶毒的言锋来,刺着他人……”[2]T君的感慨:“人间有几个人可以懂得话里的意思的,隔膜……人间原是张了隔膜的密网,要将人们全个笼在里面的。”[2]
作家认为苦难一方面来自于人类自身,一方面来自于一种不可知的力量。在他的笔下,仿佛有一种个人无法左右、无法逆转的力量控制着人生,他把这种力量归结为命运。也就是说在承认主观能动性的基础上对于一种客观存在的、人无法把握的、不可见力量的实事求是的承认。命运难测在作家的笔下首先表现为生死无常。王统照的许多小说里都笼罩着死亡的阴影。有的是家里的顶梁柱轰然倒塌,留下孤儿寡母苦苦熬岁月。《霜痕》中的《鞭痕》、《遗音》、《醉后》、《警钟守》等,这些作品的主人公都是幼年丧父,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承受着巨大的伤痛。除此之外,王统照在多篇小说中写到了少年人的死亡。《一叶》写到云哥(李天根)童年时青梅竹马的女伴慧姐的死,《月影》写到冯惠卿的同学之4岁幼女的死,《伴死人的一夜》写“我”的年仅22岁的族侄的死。这些死亡使本来完满的生命出现了缺陷。
命运的难测还表现为人无法预料到自己以后会遇到什么不幸、打击、挫折和磨难。即使知道也无从谋虑,更无法躲避,该来的总是要来的。生活并不会按照人的主观推想来前进,意外事变往往会无先兆的出现在人们的面前。一旦这样的事变出现,人们预先设计、编织的异常精致的生活逻辑便会立即被砸的粉碎。王统照长篇小说《一叶》正是人在命运的摆布下无能与无奈的普遍处境的生动写照。这篇小说情节线上的所有善良的人们,无一不是在命运的摆布下无奈地挣扎,最后以悲剧告终。慧姐为封建家长所逼,死于旧式婚姻;护士云涵父母惨死,身受奸污,最终皈依上帝;朋友柏如被诬入狱,身染不治之症;渔夫饱受税捐之苦,儿子死于台风。《一叶》在人与命运的较量中展开的曲折故事框架和洋溢其中的悲剧意识,生动地显示出人的生存困境,呼应着古往今来对人生之谜的思考和困惑。正如成仿吾对《一叶》的评价:“《一叶》成功的地方,在能利用那个插话,表现出在运命中辗转的人类之无可奈何的悲哀,使谁看了,也要感到不知从何而来的悲哀的醺醉。”[3]
三、对超越生存苦难的凝思
作家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对生命困境的观照和追问上,对生命的探询也不仅仅停留在悲叹和感伤,因为悲叹和感伤“不但在这个疾风暴雨的大时代中不相宜,即在十分安定的时代中也不象一回话”。[1]五四前后,面对中国社会的黑暗现实和国外纷至沓来的各种思潮,王统照与文学研究会的许多作家一样,在严肃认真地思考着。一方面思索着人生之谜,一方面面对灰暗痛苦的人生,思索通过什么途径方可使这混沌的人生变得美好。 1918年,王统照考入中国大学外国文学系,一边学习和研究外国文学文化,一边翻译和创作。这时候他接受了外国文学中的自由、博爱、民主主义思想,特别是泰戈尔的爱的哲学,在泰戈尔思想的影响下,王统照极力追求爱与美两者相一致的理想王国。王统照主张用爱和美改造客观世界,以美和爱的构想净化人性,使人类入于祥和、圣洁的世界。这在《微笑》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主人公阿根是个因偷窃被捕入狱的青年,刚入狱时,他憎恨包括自己在内的一切人,鄙视同监犯人的驯良温顺,他蕴藏着反抗力量,设想出狱后复仇。但由于偶尔得到一个女犯人的若不留心地微笑,便悟出那微笑是广博的爱,是整个人类和全部世界的笑容,他从此觉醒,出狱后半年,居然成了个有知识的勤快的工人。在《一叶》里,作者把人生比作一串碧色的念珠,必须用爱的泪水常常润洗,他才会放出灿烂的光华。而《沉思》则从反面表现了这种爱,它说明了没有这种爱,人类会变得自私、冷酷、狭隘。
除了广博的人类之爱以外,王统照的“爱”,更多地表现为人伦之爱,包括父母之爱、兄弟姐妹之爱、朋友之爱等,其核心是母爱,并把它作为拯救这无爱世界的一剂良方。《微笑》中阿根的解救缘自于女囚对他的微笑。有的评论认为,这个微笑太过玄虚、神秘了。其实也不难理解,这个微笑意味着宽慰、关爱、理解、劝勉等情感,这些情感归根究底来自于女性本能的母爱。对身陷情感荒漠的阿根来说,无疑是一剂清凉剂。王统照的《醉后》可以说是他歌颂母爱的代表作。以一个安详温和的母亲作为“爱”与“美”的理想化身,打动了一个迷惘在深渊里的可怜人的心。主人公“他”是一个抑郁不得志的青年,回到故乡后沉湎于酗酒和滥赌之中。一次大醉后他独自跑到一座荒废了的花园里,朦胧中好像看到母亲用手臂护着他,眼里充满了忧郁惠爱的光辉。于是,他的苦痛因此而完全消失。破晓时分,他从幻境中醒来,仍能感到母亲那柔和目光的温暖。从此,他恢复了平和恬静的心境,获得了重新做人的勇气,在明媚的晨光里,他似乎看到一个美妙的世界。慈祥的母亲用泪水洗净了儿子满脸的污垢,使他从深渊中回到人世间。
总之,在王统照早期小说中不难看出他对现代人类生存苦难的忧虑和思考,对超越性精神追求的凝思。虽然这种思考和探索不够深刻,有些主观化、理想化,但这种对人类终极意义的探索精神是可贵的,是自有其价值和地位的。这种探索将给后世的文学家以启发,促使更伟大、更深刻的作品的诞生。王富仁先生认为:“一个作家所追求的一种新的倾向,由于社会和个人条件的限制,并没有在他自身造成空前绝后的伟大作品。这种倾向的真正伟大的作品是在他的后继者那里实现的,但他对于所追求的方向却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在历史上应赋予一定的地位。”[4]用这段话来评价的早期创作,也是非常恰当的。
参考文献:
[1]冯光廉刘增人.王统照研究资料[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
[2]王统照 王统照文集[M].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
[3]刘增人王统照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
[4]宋益乔. 许地山传[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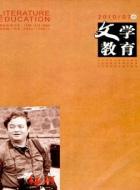
- 从“第二性”到四季斑驳 / 刁俊娅
- 我抓住了两个世界 / 姜广平
- 张爱玲缺失性体验对《小团圆》的影响 / 张茫茫
- 简析安娜与繁漪的爱情悲剧 / 魏淑源 吴志钟
- 重耳在流亡中成为为一代霸主的原因 / 刘煜超
- 扬州“八怪”新考 / 刘 景
- 哈代的宗教思想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响 / 王美霞
- 论王统照早期小说的苦难主题 / 丁文英
- 浅析张爱玲作品的特点及其艺术成就 / 陈 光
- 余秋雨文化散文的语言特色赏析 / 黄益菜
- 高师毕业生就业情况分析与对策研究 / 谢素华 黄 鹂
- 挣扎和觉醒 / 唐丽丽
- 简洁的叙述 含蓄的象征 / 陶 凤
- 科学发展观视域下的高校学生工作探析 / 唐丽洁 宋 冰
- 困境中的苦闷选择 / 杜 静
- 浅析《死水》中的丑 / 路宏建
- 释“东西” / 何 娜
- 关于森田疗法的理论及在实践中的运用 / 丁一家
- 南方,故乡 / 郭 华
- 欧.亨利小说中的现实主义及其表现方式 / 张 磊
- 亦舒小说特点初探 / 刘丽娜
- 探析产品障碍设计的设计方式 / 刘秋云
- 三岛由纪夫诡异的文学世界与奇异的心理世界 / 丁跃斌
- 坚守传统文化精神 / 刘爱军
- “两型社会”建设背景下高职人才培养浅析 / 王 鹰
- 浅谈大学生创业素质的含义和内容 / 卢明霞
- 浅谈“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 / 张晓姗
- 关于高校学生管理的几点思考 / 官孙平
- 试析大学的形象建设 / 李玲玲
- 对打工文学的再认识 / 敖荣祥
- 材料学专业本科生课程创新能力的探索 / 王献彪
- 大学生素质拓展训练体系构建 / 张 恒 周 欣
- 一位水与钢铸就的女性 / 张亚利
- 城市规划展览馆展示的空间设计探悉 / 胡国梁
- 薇拉.凯瑟笔下的生态乌托邦 / 牟 佳
- 刍议大学生综合素质 / 牟道富
- 中等职业学校体育对学生心理发展的作用 / 李玉萍
- 略论李清照《词论》的词学史意义 / 黄 艳
- 新时期公民借助媒体引发的新问题探究 / 韦璐明
- 新形式下高校基层管理人员应具备的素质 / 王 瑛 郭亦鹏
- 浅议大学生消费观的培养 / 穆冬梅
- 高职英语口语课堂中的愉快教学 / 温 燕
- 浅析影响青少年体质下降的因素 / 高 林
- 试论欧美关系的新发展 / 郭石磊 苏 薇
- 浅谈新闻翻译中几个需注意的问题 / 王 玉
- 如何提高非英语专业大学生的英语听力理解能力 / 欧 丹 李何赟
- 运用网络,提高小学英语课堂效率 / 马 丹
- 再论英汉情感隐喻之共性 / 王 眉
- 从中西文化差异谈大学英语教学 / 左 健
- 目前农村小学开设英语课的现状及对策 / 邓建兰
- 高职英语教学组织形式探究 / 李媛慧
- 浅议对外汉语语音教学 / 刘 娟
- 浅谈歌唱中的情感 / 刘伟平
- “依赖表现”的中日对照 / 谢 群
- 大学英语课堂生生互动模式的探索 / 吴 西
- 浅谈中学生音乐欣赏能力的培养 / 张亚静
- 让学生制作出更好的陶艺作品 / 万 莉
- 中职《商务英语函电》教学思考与策略探究 / 古兰波
- 略谈数码时代的美术基础教学 / 谭细雄
- 浅谈小学美术创造力的培养 / 黄 韬
- 职中生舞蹈训练中的品质锻炼 / 何 娟
- 中外合作办学中的英语教学简论 / 杨 婕
- 手绘效果图课程中的马克笔植物画法 / 李 亮
- 如何有效的练习练习曲 / 于 岚
- 浅析钢琴学习中家长的作用 / 李 佳
- 非语言交际在外语教学中若干应用的思考 / 米 乐
- 任务驱动法在文科教学中的有效应用 / 吕宪栋 刘 伟 钟 健
- 知—情结合:优化高职英语课堂的新思路 / 张晓红
- 美术教育中加强中国传统美术教育的重要意义 / 黎 亮
- 医学英语教学现状及改革探讨 / 梁 洁 叶 砾 颜仕尧
- 中学生作文互动评改实践例谈 / 刘灿伟
- 新课改下初中语文教学模式反思 / 池灵巧
- 如何在课堂中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的能力 / 陈穗芳
- 浅谈中小学汉语言文学教学 / 张有英
- 加强学校管理促进教育发展 / 唐国玉
- 浅谈兴趣的培养\课堂教学及课内外结合 / 乐水英
- 在阅读教学中寻求美 / 陆丽娟
- 丰富语言积累培养健康情感 / 吕小勇
- 背景知识架构的特异性在阅读教学中的运用 / 张 晨
- 浅谈小学高年级语文复习教学 / 王 申
- 再谈语文课堂人文素养的养成教学 / 李宗轩
- 让语文教学插上信息技术的双翼 / 刘文捷
- 探讨“因材施教”的几个问题 / 唐 亮
- 浅谈中学思想政治教育新思路 / 李苗苗
- 素质教育与语文教学 / 方 杰
- 和谐社会视域下的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 / 王 娟 庞明珍
- 从图式理论到诗歌教学的“4321”模型 / 王 春
- 守恒法在化学计算题中的应用 / 杨先芳 李小刚
- 高职广告设计课程中创意思维运用的教学探索 / 杨 帆
- 中学思想政治课如何实施素质教育 / 丁 霞
- 随机教育在中职德育工作中的实施 / 刘长春
- 如何培养学生的诚信观念 / 吴功学
- 浅谈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 罗中春
- 学导式教学模式在健美操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 招惠芬 林昭绒
- 提高小学生计算能力的实践与思考 / 邝四莲
- 提高农村学校教育教学质量之我见 / 曹登玉
- 浅谈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管理 / 崔 娜
- 运用电教媒体创设乐学氛围 / 秦芳兰
- 浅谈高校辅导员在班级建设中的引导作用 / 彭 斌
- 信息技术在服装设计教学中的运用 / 刘文英
- 学习兴趣促使学习习惯的形成 / 杨丽玲
- 小议怎样上好一堂信息技术课 / 秦秀丽
- 浅谈孟子的德育思想 / 任成华
- 如何转变教师在体育教学中的观念 / 李 兵
- 提高学习Phot..op的兴趣几个途径 / 陈周强
- 论高中政治教学中的创新培养 / 谭炳辉
- 纽曼高等教育思想浅析 / 马露奇
- 激励理论在学校体育教育管理中的运用 / 漆 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