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10年第6期
ID: 156968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10年第6期
ID: 156968
略谈高中作文教学的基点
◇ 夏爱云
在语文教学多元化的今天,我们尤有必要重读现代教育史上的经典之作。细读《文章作法》《文心》,只觉感慨良多。《文章作法》为刘熏宇先生基于夏丐尊先生的讲义稿修订补充,《文心》为夏丐尊、叶圣陶两位先生合著,二文关于写作方面的核心思想是一致的。现就阅读后的启示略谈高中作文教学的基本落脚点。
一.审视作文序列
《文章作法》一书除第一章为“作者应有的态度”,第二至六章按文体编排,依次为:记事文(相当于今天中学语文教学中所说的社科文)、叙事文(相当于今天通常所说的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小品文。纵观全文,重在根据不同文体介绍相关知识与写作技法,形成一个针对当时初中生写作训练的序列(不过,当时初中生的国文功底只怕比现在的高中生的语文水平只高不低)。以第三章“叙事文”为例,在第一节“叙事文的意义”中第一句就是先给叙事文下个定义:“记述人和物的动作、变化,或事实的推移的现象的文字,称为叙事文。”然后承第一章知识,考虑学生的学习心理,在第二节中先阐明记事文和叙事文的区别,此后依次阐明叙事文的要素(第三节)、叙事文的主想(第四节,即今天所说的主旨、中心思想),最后重点阐明观察点的变动(第五、六节)与叙事文的流动(第七、八、九节)。关于“叙事文的流动”,书中如此阐述:“叙事文的对象是事物的现象的展开,这展开的情形被叙述成文字的时候,就成了文字上的流动。”这相当于今天表述中的文章组织与行文节奏。由第三章来看,叙事文一章以叙事文的写作知识为主框架展开,依次说清相关知识是什么,并佐以具体文段帮助学生理解,由此形成一个关于叙事文的写作训练序列。
这一写作体系思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于继承中有了较大发展,出现了一系列重视文体技法训练的实践研究,比如黑龙江常青老师的“写作基本功分格训练”,引导学生从五味七情辨析入手,按一定规格训练学生的观察力、思维力、想象力和表达力。八十年代初北京的刘朏朏、高原老师的“观察——分析——表达”三级训练法,观察是基础,分析贯始终,表达是目的。这二例在当时实践中其实已初见成效。
行行重行行,直至今日,写作训练其实还是基本停留在民国二三十年代学习西方而来的写作知识体系及教师凭个体认知水平自行操作的层面上。比如,《语文教学通讯》A刊2008年第9期刊登的《作文教学应该有一个系统》一文,文中把作文训练系统归纳为“文字、材料、新意、修改、个性”五个方面。《语文教学通讯》A刊2008年第12期刊登的《也谈作文教学的“系统”》一文,则认为应建立一个“立足教材,分步规划,师生全程参与”的作文教学系统。
两篇文章固然有其实践中的合理性,但是二文的背后不容忽视的第一个事实是:我们的语文教材大多未能较好地发挥应有的构建一个可资使用的写作训练序列的作用。笔者所在的浙江省目前使用的是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2005年6月第2版。教材中的写作安排依附于“阅读与鉴赏”专题,以人文性为主导,突出了开放性和选择性,但整体上却淡化文体意识,编排上无写作能力训练的序列性。实际教学中笔者所在的县市教师互相交流的一个共同做法是:舍弃教材中的“写作”内容,自行安排。认真负责的,想办法有序训练;敷衍对待的,随意想个题目应付一下。反映的第二个事实是:没能更好地整理继承中前进。而要继承写作序列的合理性编排,其一,要厘清序列性的必要。按奥苏贝尔的认知结构同化理论来看,学习过程中,当学生主动地所学的新知识与原有认知结构中的适当知识加以联系,有意义的学习便发生了。这个过程亦为意义的同化。反之,所学知识是无序的,则不易同化。按加涅的智慧技能分层来看,写作技能当属“高级规则”,而学习在习得规则过程中如何更有序地形成网络储存,则更有利于学生在变化的情境中适当地运用规则。从生情出发认清序列性编排有助于学生提高学习效率,方不致于一边“创新”一边丢弃。其二,我们需要整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教育家与普通教育工作者的实践经验,在此基础上指导课标的修改与写作教材的编写。
二.深思写作心理
在《文心》的“题目与内容”一章中,王先生澄清学生习作中可能存在的错误认识,“作文是生活,而不是生活的点缀”,“要求诸练习,只好规定一个日期,按期作文。这是不得已的办法。并不是作文这件事情必须出于被动。而且必须在规定的日期干的”。然后说明命题作文的特点:“题目虽然由我出,你们作文却还是应付真实的生活。”在《文心》的“触发”一章中,提及读书与习作的关系,“读书贵有新得,作文贵有新味。最重要的是触发的功夫。所谓触发,就是由一件事来感悟到其他的事。你读书时对于书中某一句话,觉到与平日所读过的书中某处有关系,是触发;觉到自己的生活有交涉,得到一种印证,是触发……”文中接着写学生乐华此后对触发的感悟,例如由洗衣领想到“领袖”一条:“把衣服穿在身上,最污浊的是领和袖。因为污浊的缘故,洗濯时特别吃亏,每件衣服先破损的大概是领袖部分。领袖是容易染污浊的,容易遭破损的。衣服的领袖如此,社会上的所谓领袖何尝不如此!”其实书中“文章病院”“文章的组织”“习作创作与应用”等章节中莫不从学生心理出发,力求唤醒学生主动写作的心态,以期养成恰当的写作习惯。其实,《文心》一书的小说体编排就是以激趣为旨的。
同样的,《文章作法》中但凡列一条写作知识,就会举一二相应事例。在“叙事文流动的中止”一节中提出概念后,就举了《红楼梦》第三回林黛玉初进贾府王夫人房中所见一节为例。最妙的是其后的评论:“这段文中,除了第一句是叙事文以外,流动全然中止,以后都成了王夫人房中的记事文。若非把这一大节叙上不可,应当将所记的情况都改成由黛玉眼中看出的,而将末了‘基馀陈设,不心细说’的话删去,那么流动就没有停滞了。”这里不但涉及到用例当与不当,还涉及到如何充分使用,更好地促动学生的理解。《文章作法》中举一例作“西湖”的记事文,第一步就是要求学生“先查地理书”。假定得到下面的材料:“(一)西湖在杭州城西,又名西子湖。(二)西湖是东南的名胜。”然后要求学生把自己游西湖的经验列举出来,书中罗列了二十一条假定出现的经验,最后让学生对材料进行精密的整合。这个过程就是精细地引领学生开展写作的操作程序。如果学生能养成这一习惯,读书与生活自然相合,只要题目合乎学生的学习层面与生活特点,又怎会愁“无内容”呢?
如果说训练序列意识与唤醒学生的写作心理主要由学习西方当时的教育哲学思潮而来,那么二书中诸多不经意的细节中涉及的写作习惯的指导,是符合汉语言的认知特点与规律的。例如,《文心》“语汇和语感”一章中王先生的提示:“我们真要语汇丰富,只留意于普通用语是不够的,须普遍地留意于各地各种人的用语才好。此外,还有一种功夫应该做,就是对于词类的感觉力的磨练。”其实读写结合与缘于生活,都是写好作文的必要前提,也符合汉语言的语感养成特点。而二书中关于词语辨析,串词成句等具体做法,也深合汉语语感的养成规律。正如《语文课程标准》中指出:“语文又是母语教育课程,学习资源和实践机会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因而,应该让学生更多地直接接触语文材料,在大量的语文实践中掌握运用语文的规律。”这阐述的正是汉语言学习的特点。
《文章作法》的第三篇附录《我在国文科教授上最近的一信念——传染语感于学生》一文末段如是:“自己努力修养,对于文字,在知的方面,情的方面,各具有强烈锐敏的语感,使学生传染了,也感得相当的印象。为理解一切文字的基础,这是国文科教师的任务。并且在文字的性质上,人间的能力上看来,教师所能援助学生的,只此一事。这是我近来的个人的信念。”这是教师、作家、读者身份兼具下的反思,仅此一语,就需我们今天一想再想。
行文至此,想到一节在浙江萧山听的作文课《感受·唤醒·表达——关于自由写作实践的一次对话》(2006年省优质课一等奖第一名)。教学主环节是:1、让学生听马思聪的《思乡曲》。第一次听,让学生自由感受,然后交流。2、教师向学生陆续展示自己发表在《散文》2005年第6期上的一篇文章《这个世界很美——关于马思聪及〈思乡曲〉》的相关片断,并不断介绍自己的创作心理。3、学生二听《思乡曲》,学生自由写作,写出感受。这节课,其实就是唤醒学生写作意识并教给学生写作策略的一个具体流程。而且教学中提供了学生写作的内容与语言学习的范例。如果长期训练,学生必有收获。
如此看来,我们今天重读《文心》《文章作法》,至少有两个至今不该忘的基石:写作训练需系统有序,写作意识为真实体验!
夏爱云,华东师范大学2007级中文系教育硕士在读,浙江苍南中学教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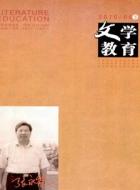
- 集诗兴童心于一身的诗评家张永健 / 梁志群
- 施蛰存与丁玲的同学之谊 / 杨 之
- 从“作文说谎”到“概念先行” / 陈歆耕
- 论余华早期“暴力”小说的两种向度 / 千利江
- 论王家新的诗歌精神 / 陈芳辉
- 韦庄词的抒情艺术 / 刘风
- 毛滂诗歌中的花意象 / 宋 丹
- 读远村诗集《浮土与苍生》 / 刘元英 潘国红
- 对《红字》中女主人公的一种荣格式解读 / 颜健生
- 二十世纪浪漫主义思潮的中国特色 / 刘继红
- 汉语中性别歧视的体现及成因 / 颜 妮 李光莉
- 论马克思法学思想产生的历史基础 / 包静雅 王英秀
- 让课堂因生成而美丽 / 李怀芝
- 鲁迅小说肖像描写例谈 / 开 健
- 提高语文课堂教学效率的几点看法 / 邢旺昌
- 古代诗词实践教学探索 / 王建平
- 语文教材评点应从结果性向过程性转变 / 朱一唯
- 语文教学中的创造性思维培养 / 罗有林
- 在模块整合中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 / 朱锡川
- 享受语文多元对话教学的精彩 / 刘红霞
- 语文教学中的审美策略 / 张 婷
- 教师课堂语言小议 / 齐占海
- 语文教学中如何激活思维之花 / 张 花
- 《归园田居(其一)》教学构思 / 苏玉洁
- 审美教育中的四个实施点 / 邓进时
- 陶行知教育理念例谈 / 赵海琪
- 一堂观察暴风雨的语文课 / 汪敦珊
- 古诗鉴赏应试的策略 / 吴成玉
- 语文综合性学习例谈 / 范雪英
- 如何优化语文课堂教学 / 田茂富
- 语文课堂与多媒体教学之关系探究 / 张孝玉
- 略谈高中作文教学的基点 / 夏爱云
- 课内外结合积累写作知识 / 韦卫赤
- 让音乐与审美共舞 / 黄伟娇
- 作文教学中培养学生思维品质的意义 / 常 鑫
- 激活语文课堂方法谈 / 佟立红
- QQ空间在语文写作教学中的运用 / 郑昌平
- 如何让学生快乐作文 / 代西敏
- 语文有效性教学的相关因素 / 朱忠平
- 母语负迁移与高职英语写作教学 / 高 长
- 作文教学应倡导自主 / 曹旭东
- 利用网络技术优化作文教学 / 张玉莲
- 议论文开头出彩方法例谈 / 曹红勇
- 作文评语的人文性和艺术性 / 刘俊峰
- 写作教学杂谈 / 杜东海
- 材料作文之思 / 吴永福
- 作文《花儿》教学案例 / 李金娥
- 让学生成为课堂阅读的主人 / 徐海军
- 人物描写方法例谈 / 马仁昌
- 李白《月下独酌》的浪漫主义情结 / 张朝学
- 从《春江花月夜》谈对诗歌的鉴赏 / 张雁平
- 论作文教学中的情感因素 / 江 洪
- 我对《侯己的汇款单》的伦理学解读 / 肖格格
- 语文阅读教学的心得体会 / 杜永杰
- 在生活中捕捉写景的灵感 / 袁春容 汪训文
- 《第十二夜》中女扮男装手法的运用 / 闫春晶
- 个性化作文教学的理论探索 / 杨亚红
- 阅读教学中的比较探究 / 王琼予
- 《三块钱国币》的幽默艺术 / 杨卫东
- 作文教学中的几点启示 / 贾 涛
- 阅读要开启学生的灵性 / 宓 娟
- 《山居秋暝》的诗画之美 / 任 远
- 寓言作文创新立意四法 / 许 丹
- 《社戏》的人情美 / 张耀东
- 全方位激发学生阅读兴趣 / 张小玲
- 学会捕捉闪光点 / 罗新方
- 《口技》三美 / 张 刚
- 图式理论及其在英语阅读理解中的应用 / 钱建伟
- 孔子思想的当下解读 / 杜 金
- 文本阅读中的情感教育 / 吕 梅
- 压缩语段题解题研究 / 刘 阳
- 文言文背诵方法指导 / 左松良
- 刘兰芝与焦母矛盾的根本何在 / 余礼权
- 少数民族应该称兄弟民族为宜 / 高思华
- 语文作业优化设计之思考 / 于艳华
- 体现人文关怀是语文教育之本源 / 甘春枝
- 电视公益广告中的审美教育 / 王 优
- 英语新闻标题的修辞特点及汉译 / 王 宁
- 关于公共体育课课程设置的几点思考 / 刘晓辉 李 旻
- 透过“汉语热”看国人的英语学习观 / 林志煌
- 在音乐中亲证 / 汪 青
- “右声说”探究 / 于 虹
- 日语 / 王 君
- 人教版教材指误二例 / 陈玉绿
- 中式英语产生的原因及对策 / 尹明花
- 最是雨中有诗情 / 刘 伟
- 试论“所”字结构 / 陈海英
- 英语中副词形容词运用刍议 / 肖新元
- MB.. / 田 雯 朱汉袆
- 囚绿,诠释了爱 / 殷德中
- 现代信息技术与语言文字规范化 / 陈周伟
- 长长的走道 / 赵海妮
- 让标语撑起一片蓝天 / 唐春艳
- 素质教育背景下班级管理实践与思考 / 王晓静
- 中学德育实效性策略探析 / 王鹏家
- 让爱温暖学困生的心灵 / 周红宁
- 让课改之花在校园绚丽绽放 / 马丽娟
- 做一名让人民满意的教师 / 王海芳
- 上海世博会两章 / 李甫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