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10年第6期
ID: 156941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10年第6期
ID: 156941
毛滂诗歌中的花意象
◇ 宋 丹
毛滂(1060——1124?)⑴,字泽民,自号东堂,衢州江山(今属浙江)人。他主要活跃于北宋中后期文坛,与当时名士苏轼、苏辙,诗僧释参寥、释维琳等皆有文字来往。他诗、词、文俱善,苏轼赞其“文词雅健,有超世之韵”,并以“文章典丽,可备著述科”荐之于朝⑵。后因其晚年出入蔡氏兄弟门,颇招非议。现在的文学史多把他划为苏门文人。毛滂的词颇负盛名,或许是由于毛滂的词名盖过诗名的原故,他的诗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少有人提及。实际上,苏轼当时就称赞他的诗文“闲暇自得,清美可口”,南宋人刘克庄的《后村千家诗》也选有他的《夏夜》诗。毛滂的诗歌在当时及稍后一段时期还是颇具影响力的。而清代四库馆臣对他的诗文也有很高的评价:“其诗有风发泉涌之致,颇为豪放不羁;文亦大气磅礴、汪洋恣肆。得二苏之一鳞半甲,在北宋之末要足自成一家,固未可竟置之不议也。”⑵
毛滂的诗现存近300首,其中古体诗62首、律诗118首、绝句111首,较他的词与文来说,数量颇为可观。他的诗歌既体现了宋诗的某些典型特征,又不失其含蓄蕴藉,不似一般人对宋诗所持有的那种枯槁无味的印象。笔者认为这与毛滂在诗中运用大量的自然意象,并继承屈原“香草美人”的比兴寄托手法有关。本文将专门对毛滂诗歌中频频出现的花意象进行探讨分析。
梅花可算是毛滂最喜爱的一种花,其现存的诗歌中专门咏梅的诗有三首,而涉及到梅花意象的诗歌就更多了。我们知道,宋人对梅之喜爱就好比唐人对牡丹之喜爱,而梅花的疏淡清雅和牡丹的雍容华美正好反映出唐宋人不同的审美趣味。宋人相对于唐人来说就好像人到中年,对人生的体悟更深透,他们往往不再执著于繁华的表象,而是更注重内在的东西,因此他们所追求的美是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美,是一种含蓄美、老境美。而幽香冷艳、疏淡清雅的梅花正好契合宋人的这一审美追求。梅花也是到了宋人的文学作品中才从“春花时艳的感伤绮怨形象最终上升为崇高的人格象征”。⑶在毛滂诗歌中,我们就可看到梅花的形象同隐者高士联系在一起:
非喧非寂彼何人,孤山诗朋良独清。世间名利不到尔,长与梅花作主盟。嗟我于此无一得,曾向峰前留行迹。天涯暮景盍归来,坐对此图三太息。(《题雷峰塔南山小景》)
毛滂在诗中提到的那位“孤山诗朋”就是宋初有名的隐士林逋,他常年隐居于杭州西湖的孤山,种梅养鹤,终身不仕不娶,人称“梅妻鹤子”,而其咏梅名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山园小梅二首》其一)更是使梅花同自己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难怪毛滂要说其“长与梅花作主盟”了。梅花的疏淡清雅同隐士的孤清高洁相互映衬、交相辉映,梅花因隐士而获得了精神内涵,而隐士也从梅花身上找到了精神寄托。故而梅花所象征的孤清自处的隐逸精神则成为诗人所神往的一种精神境界。再如其诗:
小蛮为酌流霞春,醉倚梅花满怀月。……早挂铜章老槐下,短蓑独速上渔舟。(《李白于宣州……》)
拂石须相憩,留云欲共攀。为寻梅发处,先过向南山。(《欲入山访参寥,预令探梅》)
在前一首诗中,诗人借酒消愁,而月下自妍自足的梅花仿佛成了诗人的安慰,于是在诗人心中一份隐逸之情油然而生。后一首诗则写了诗人到深山中探梅的情趣。
不知是出于巧合,还是毛滂对红梅的偏爱,其流传下来的咏梅的三首诗所咏之梅都是红梅:
何处曾临阿母池,浑将绛雪点寒枝。东墙羞颊逢谁笑,南国酡颜强自持。几过风霜仍好色,半呼桃杏听群儿。青春独养和羹味,不为黄蜂饱蜜脾。(《红梅》)
淡中着色似狂颠,心与梅同迹不然。……辩桃认杏何人拙,压雪欺霜政自妍。只恐东君招不得,好修犹在竹篱边。(《曹彦约<昌谷集>,同官约赋红梅,成五十六字》)
雪月共高寒,求多意未阑。林逋五品服,宋璟九还丹。老友松筠健,贤宗鼎鼐酸。任渠蜂蝶闹,难作武陵看。(《再赋四十字》)
三首诗中的梅花都已人格化,不但具有孤清自处的隐士精神,而且还具有傲雪凌霜的君子品格。另外,红色本是很绮丽的颜色,然而诗人所咏之红梅与隐士为伴、雪月为朋、松竹作友,于亮丽之中自有一股清气。但是,或许在诗人心目中梅花的本色应该是洁白纯净的吧,要不怎会说红梅是“淡中着色似狂颠,心与梅同迹不然”呢?“淡中着色”的红梅就好像人处在醉后的颠狂状态,心还是那颗心,只是形态略有不同罢了。这不由得让人联想到诗人,本是怀着一颗美好的用世之心却陷入党争的旋涡不能自拔,似乎应验了其“心与梅同迹不然”的诗谶。
另外,在毛滂表现友情的诗歌中我们亦可看到梅花的身影:
应念萧寒槁木身,殷勤分寄岭头春。冰肌玉骨终安在?赖有清诗为写真。(《蔡天逸以诗寄梅,诗至梅不至》)
《荆州记》里记载:“(陆)凯与范晔相善,自江南寄梅花一枝,诣长安与晔,赠以诗。”诗人在这里化用了南朝宋人陆凯寄梅花给朋友范晔以表达深情厚意的典故,然而却典化无痕,使人觉得恰到好处。前两句诗人用“岭头春”代指梅花,写朋友对自己的关心,其实亦表达了自己对朋友的感激。较有意思的是:诗信到了,梅花却没有收到,所以诗人半开玩笑地问:“冰肌玉骨终安在?”,可又洒脱地自解道:“赖有清诗为写真”,最后一句一方面是自解,一方面也赞扬了朋友的诗写得好。梅花象征友情虽不是首例,然而在这一问一答之中却也表明了诗人潇洒出尘的情怀。
在毛滂的诗歌中我们时常也会发现各种各样的春花,如:
酴醾春晓与谁芳,自是新来雨露香。(《春晓》其二)
杨花满路尚颠忙。(同上)
红蔷薇搭小栏杆。(《春晓》其三)
问讯道人春到否,瑞香花谢倚栏杆。(《寒食日过翠峰塔示法海道人》)
带雨的酴醾花散发着清香、漫天的杨花随风起舞、栏杆旁的红蔷薇开得正艳,好一派生机盎然的春景!一个“新”字、一个“忙”字和一个“搭”字把花的形态和神态都写活了,仿佛在眼前一般。如果说前面三种花是诗人向人们暗示春意正浓、春光正好的话,那么瑞香花的零落则表明春光的易逝了,诗人本来还不确定春天是否已经到来,正准备向道人打听,可猛然间发现塔院栏杆旁的瑞香花都已开过了,使人不由得添了几分淡淡的伤感。同样是写栏杆旁的花,一个“搭”字、一个“倚”字却表现了两种不同的神态,“搭”字表现了蔷薇旺盛的生命力,似有一种向外撑开的趋势;而“倚”字则表明瑞香花明媚鲜妍不再,生命开始逐渐枯萎,似人一般无力地倚在栏杆上。看似不经意的两个字,却摄取了两种花不同的神态,可见诗人的观察入微。而其实无论是写盛开着的春花,还是写凋谢了的春花,同样表明了诗人对春天、对美好事物的热爱和留恋。
总之,在毛滂笔下,无论是梅花也好,春花也罢,还是诸如水仙、兰、菊、橙花、石竹花一类的花,大都开在山间溪畔或寺院中,有一种在寂寞中自妍自足的特点:
水仙弄幽姿,寄余汀洲情。(《溪上》)
竹根逢小春,紫兰茁其芽。造物惜鲜荣,宁肯及幽葩。 (《育阇黎房见秋兰有花作》)
花外种松松外竹,渐无蝴蝶到东篱。(《子温以诗将菊本见遗数日……》其二)
翛然此意不可道,卧看石竹凝孤芳。(《立秋破晓日入山,携枕簟睡于禅静庵中,作诗一首》)
橙花亦娟娟,照水弄清白。孤香少人知,黄蜂自为客。(《过静林寺,用琳老韵作四绝句》其三)
这些花仿佛开在世外,孤清自赏之中自有一种高洁的品质;又仿佛开在诗人心中,作为诗人有缺陷现实人生的一种寄托和补偿。
※基金项目:凯里学院2009年院级科研规划课题,课题号:S0919。
参考文献:
[1]周少雄.毛滂集[M].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
[2]毛滂.东堂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程杰.从魏晋到两宋:文学对梅花美的抉发与演绎[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1(6)
宋丹,女,贵州凯里学院人文学院讲师,华东师范大学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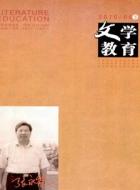
- 集诗兴童心于一身的诗评家张永健 / 梁志群
- 施蛰存与丁玲的同学之谊 / 杨 之
- 从“作文说谎”到“概念先行” / 陈歆耕
- 论余华早期“暴力”小说的两种向度 / 千利江
- 论王家新的诗歌精神 / 陈芳辉
- 韦庄词的抒情艺术 / 刘风
- 毛滂诗歌中的花意象 / 宋 丹
- 读远村诗集《浮土与苍生》 / 刘元英 潘国红
- 对《红字》中女主人公的一种荣格式解读 / 颜健生
- 二十世纪浪漫主义思潮的中国特色 / 刘继红
- 汉语中性别歧视的体现及成因 / 颜 妮 李光莉
- 论马克思法学思想产生的历史基础 / 包静雅 王英秀
- 让课堂因生成而美丽 / 李怀芝
- 鲁迅小说肖像描写例谈 / 开 健
- 提高语文课堂教学效率的几点看法 / 邢旺昌
- 古代诗词实践教学探索 / 王建平
- 语文教材评点应从结果性向过程性转变 / 朱一唯
- 语文教学中的创造性思维培养 / 罗有林
- 在模块整合中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 / 朱锡川
- 享受语文多元对话教学的精彩 / 刘红霞
- 语文教学中的审美策略 / 张 婷
- 教师课堂语言小议 / 齐占海
- 语文教学中如何激活思维之花 / 张 花
- 《归园田居(其一)》教学构思 / 苏玉洁
- 审美教育中的四个实施点 / 邓进时
- 陶行知教育理念例谈 / 赵海琪
- 一堂观察暴风雨的语文课 / 汪敦珊
- 古诗鉴赏应试的策略 / 吴成玉
- 语文综合性学习例谈 / 范雪英
- 如何优化语文课堂教学 / 田茂富
- 语文课堂与多媒体教学之关系探究 / 张孝玉
- 略谈高中作文教学的基点 / 夏爱云
- 课内外结合积累写作知识 / 韦卫赤
- 让音乐与审美共舞 / 黄伟娇
- 作文教学中培养学生思维品质的意义 / 常 鑫
- 激活语文课堂方法谈 / 佟立红
- QQ空间在语文写作教学中的运用 / 郑昌平
- 如何让学生快乐作文 / 代西敏
- 语文有效性教学的相关因素 / 朱忠平
- 母语负迁移与高职英语写作教学 / 高 长
- 作文教学应倡导自主 / 曹旭东
- 利用网络技术优化作文教学 / 张玉莲
- 议论文开头出彩方法例谈 / 曹红勇
- 作文评语的人文性和艺术性 / 刘俊峰
- 写作教学杂谈 / 杜东海
- 材料作文之思 / 吴永福
- 作文《花儿》教学案例 / 李金娥
- 让学生成为课堂阅读的主人 / 徐海军
- 人物描写方法例谈 / 马仁昌
- 李白《月下独酌》的浪漫主义情结 / 张朝学
- 从《春江花月夜》谈对诗歌的鉴赏 / 张雁平
- 论作文教学中的情感因素 / 江 洪
- 我对《侯己的汇款单》的伦理学解读 / 肖格格
- 语文阅读教学的心得体会 / 杜永杰
- 在生活中捕捉写景的灵感 / 袁春容 汪训文
- 《第十二夜》中女扮男装手法的运用 / 闫春晶
- 个性化作文教学的理论探索 / 杨亚红
- 阅读教学中的比较探究 / 王琼予
- 《三块钱国币》的幽默艺术 / 杨卫东
- 作文教学中的几点启示 / 贾 涛
- 阅读要开启学生的灵性 / 宓 娟
- 《山居秋暝》的诗画之美 / 任 远
- 寓言作文创新立意四法 / 许 丹
- 《社戏》的人情美 / 张耀东
- 全方位激发学生阅读兴趣 / 张小玲
- 学会捕捉闪光点 / 罗新方
- 《口技》三美 / 张 刚
- 图式理论及其在英语阅读理解中的应用 / 钱建伟
- 孔子思想的当下解读 / 杜 金
- 文本阅读中的情感教育 / 吕 梅
- 压缩语段题解题研究 / 刘 阳
- 文言文背诵方法指导 / 左松良
- 刘兰芝与焦母矛盾的根本何在 / 余礼权
- 少数民族应该称兄弟民族为宜 / 高思华
- 语文作业优化设计之思考 / 于艳华
- 体现人文关怀是语文教育之本源 / 甘春枝
- 电视公益广告中的审美教育 / 王 优
- 英语新闻标题的修辞特点及汉译 / 王 宁
- 关于公共体育课课程设置的几点思考 / 刘晓辉 李 旻
- 透过“汉语热”看国人的英语学习观 / 林志煌
- 在音乐中亲证 / 汪 青
- “右声说”探究 / 于 虹
- 日语 / 王 君
- 人教版教材指误二例 / 陈玉绿
- 中式英语产生的原因及对策 / 尹明花
- 最是雨中有诗情 / 刘 伟
- 试论“所”字结构 / 陈海英
- 英语中副词形容词运用刍议 / 肖新元
- MB.. / 田 雯 朱汉袆
- 囚绿,诠释了爱 / 殷德中
- 现代信息技术与语言文字规范化 / 陈周伟
- 长长的走道 / 赵海妮
- 让标语撑起一片蓝天 / 唐春艳
- 素质教育背景下班级管理实践与思考 / 王晓静
- 中学德育实效性策略探析 / 王鹏家
- 让爱温暖学困生的心灵 / 周红宁
- 让课改之花在校园绚丽绽放 / 马丽娟
- 做一名让人民满意的教师 / 王海芳
- 上海世博会两章 / 李甫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