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10年第6期
ID: 156944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10年第6期
ID: 156944
对《红字》中女主人公的一种荣格式解读
◇ 颜健生
霍桑的作品往往从人的本性出发,深度挖掘人性的弱点,借以找到心理的契合,为人类寻找救治的方法。《红字》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以信奉加尔文教的新英格兰殖民地波斯顿为背景,描写了教民海丝特·白兰和其教区牧师丁梅斯代尔之间悲剧式的爱情故事,向人们昭示善与恶的斗争过程其实质就是人的心理发展过程,它遵循着从集体无意识到意识的过程,与荣格的观点有相似之处。
一
《红字》叙述的是一对男女青年相爱的悲剧故事。海丝特从英国启程乘船来到新英格兰殖民地波斯顿,丈夫齐林涡斯将紧随其后,不料齐林涡斯在海丝特到达目的地后杳无音信长达两年之久。海丝特被暂时安顿在牧师丁梅斯代尔的教区,过着单身生活,但很快她就和牧师情投意合并坠入爱河,两人秘密地约会尽情享受天伦之乐。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海丝特怀孕生下一女孩,这在信奉加尔文教的新英格兰殖民地被视为大逆不道。教区执事们硬要她说出孩子的父亲,否则,海丝特将永远面临着受刑,坚强的海丝特拒绝指认自己的情夫,她被判通奸的罪名且每天配戴象征“通奸妇”的红色A字在胸前直到说出情夫为止。就在海丝特为自己的“罪孽”受刑之时,丈夫齐林涡斯神秘地出现在牧师的所在地,并秘密执行着他最为残酷的复仇计划,处心积虑地从灵魂和躯体上折磨着牧师丁梅斯代尔。善良的丁梅斯代尔却终日忏悔于自己的“罪行”,加之无勇气与世抗争,结果形容枯槁,心力憔悴,在默无声息中忍受痛苦的折磨。而海丝特偏偏天生就是一付傲骨,敢于藐视神圣的清规戒律、正视监狱和刑台,这不得不让执行上帝旨意的绅士们有些颤抖,他们觉得有必要让这异教的女徒遭受精神上的彻底挫败,给予她坐牢、永无休止的审问、游行、隔离和佩带红字等等。然而,任凭苦难折磨的无限期,海丝特以极大的毅力忍受着屈辱,忍受着人性所能承担的一切,因为她在自己的心中始终坚守着一个承诺,那便是为了真爱甘愿做出牺牲。
二
在捍卫自己尊严的日子里,海丝特经受住“炼狱”般的洗礼,她的心灵之旅经历集体无意识到意识而达到完善。按照荣格的说法,潜藏于有意识的精神生命中的能量是先于生命而存在的,因此最初是潜意识的,个人潜意识相当于一个容器,个体压抑的不为社会与个人所接受的冲动或一些忘记的以及强度太弱的体验都被贮藏在个人潜意识里。 [1]对海丝特来说,表征肉欲的潜能首先来自于力比多(一种天生遗传的自我本能),它就像深藏于心中之火,随时有可能爆发。起初,海丝特竭力保持自我的存在,力图融入到社会的大家庭中。然而当一股来自内心的力量唤醒了她的潜意识时,她踏上了寻找生命归宿—爱的征程。而爱本身是一个没有终点的长途旅行。海丝特在潜意识的支配下把发自内心的表征欲望从齐林涡斯身上转向了丁梅斯代尔,这种转移可以视为是海丝特对神圣爱情成熟认识的标志,它完全有它存在的理由: 其一,它是在丈夫齐林涡斯长期缺席的当下发生;其二,海丝特在遇到丁梅斯代尔后重新迸发爱的火花,这种心理变化是顺理成章的,它的力量来自于内心深处本能的冲动,或是一种内聚化情欲的外泄, 虽有思维定势不完备的缺陷,却是个人的潜意识过程。随着这种潜意识的发展,主体逐渐有了清醒的认识,并认同和接受自身行为,这便是原型的诞生。荣格说“原型实际上就是本能的无意识形象”。[2]原型的诞生又常常与集体意识发生碰撞,虽然其最终结果是集体意识吸收合理的成分得到弥合修补,但经历过程是痛苦的。所以,海丝特要摆脱过去那种模糊的爱情概念,达到认识的高度,就得向世俗挑战,因为“世俗权威不仅通过惩罚制约人的行为,同时还通过灌输给被统治者的一套意识形态做到这一点。这套意识形态一旦烙记在个人心灵之上,便成为我们观察世界的根本立场以及个人意识自身的基础和存在条件。”[3]
既然人人都具有追求心灵完整的自然向度,海丝特追求完美爱情的过程就成了潜意识向意识转移的过程。因为一个人如果没有走过自己的情欲炼狱就等于从来没有战胜过情欲。所以海丝特的爱情发展实质是一种自我的完善,她已厌倦夫权制下以法律形式逼迫妇女就范的传统,毅然决定做出了牺牲自我的准备。她拒绝指认情夫,公然捍卫自己真爱,是集体无意识向意识转变的象征。因为她深知她的这种爱容不得虚假,尽管要让世人领悟这点不是短时可以完成,她都全然不顾。荣格说:“个人的精神中的崭新(newness)只是一种年代久远、变化无穷的成分重新组合而已,敬重人的永恒权利,尊重古人,并承认文化和知识具有连续性。然而我们己纵身跳入进化的急流,它把我们冲向未来,使我们离根愈来愈远,过去一旦被破坏,前进再也停不下来。”[4]海丝特堪称一位卓有见识的先知,一位敢于追求个性解放的斗士。七年来她含辛茹苦,忠贞不渝,誓死保卫自己的爱情,她用鲜血和生命呵护着女儿珠儿,她以常人无法忍受的痛苦生活,为了爱人的名声,她独自承担了全部罪责与耻辱。出于对自己心爱的人的眷恋,她不但在他生前不肯远离他所在的教区,就是在他死后,仍然放弃了与女儿共享天伦之乐的优越生活,重返埋有他尸骨的故地,重新戴上红字,直到死后葬在他身边,以便永远守护、偎依着他。这个勇敢的女人还精心刺绣那红字,着意打扮她的小珠儿,不仅出面捍卫自己教养她的权利,而且尊重孩子狂野的天性,努力培养她成人。正因为海斯特是个纯洁、正直、毫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可敬的女性,后来才会有许多妇女纷纷带着她们所有的哀愁和困惑前来寻求她的忠告。在经历了苦难洗礼之后,海斯特最终唤起人们的集体潜意识,彻底改变了他们对她的态度,她不但不是罪恶的化身,反而成为行为的典范,“红字也不再象征‘通奸妇’,而成为‘天使’、‘能干’、‘敬佩’之类的代名词”。[5]
三
海丝特用爱心感化了人们。“爱化生万物并忍受万物。当一个人找到了迈向自由的道路时,他才能处于认识自己正面对着本能的根基的地位,怎么也摆脱不掉,他的开始不只是他的过去,现在和过去是以他存在的永恒基础与他共存,神话即为上帝的话,亦即来自彼岸的神秘灵感与启示。”[6]海丝特受到良知的启发去探寻爱的真谛,她那外倾的性格为她预设了痛苦的“救赎”,但决不至于摧毁她对爱的信念。她和丁梅斯代尔的默契催生出永恒的期望,两人的心在历经痛苦的煎熬中逐渐达到融合。牧师终于鼓起勇气袒露心中之密,并向全体教民宣布他的反省。在牧师去世后,没人再为红字而寻找事端,大家认为“他们之不走到极端的不虔不信,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内在的美德人,而是因为上帝的眼目看顾他们,而他的手也常在保护他们”。神的特别恩赐赐福他们在迷失中不“至于坠入永死的深渊”。[7]历经心灵的洗礼人们终于发现,“人其实最大的限制就是自体,只有当我们与极限连结时,我们才能感知无限;独特性和局限性是同义词,但如果没有这两者,对无限就不可能有感受。”[8]
心灵的旅行需要经历沧桑,尽管信奉加尔文教的波斯顿教民如何宣扬要奉神的旨意行事,但却无法掩饰他们心中对善良的误解以及对宗教的顶礼膜拜,“宗教的力量即在于他们让自己和别人相信,他们保有外人所不知道的神秘经验,那是维系它们存在的力量及方式”。[9]海丝特之所以敢向宗教发起挑战,决不是完全出于个人的考虑,而是要揭开人格面具,唤醒人的自我本能,以此完成人的心灵之旅,是意识的发展过程。
参考文献:
[1][2][4][6][8][9] 荣格.分析心理学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三联书店,2003 426-433
[3]曹亚军.“海关”及通奸罪的政治解读[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9 Vol.16 No.2 66-72
[5]胡继兰.红色“A”字的联想[J].福建工程学院学报,2007 Vol.5 No.5 35-39
[7]肖婷婷.透过加尔文教义探寻霍桑对《红字》的理解[J].牡丹江大学学报,2008 Vol.17 No.7 22-24
颜健生,男,广西贺州学院外语系讲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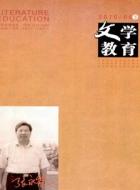
- 集诗兴童心于一身的诗评家张永健 / 梁志群
- 施蛰存与丁玲的同学之谊 / 杨 之
- 从“作文说谎”到“概念先行” / 陈歆耕
- 论余华早期“暴力”小说的两种向度 / 千利江
- 论王家新的诗歌精神 / 陈芳辉
- 韦庄词的抒情艺术 / 刘风
- 毛滂诗歌中的花意象 / 宋 丹
- 读远村诗集《浮土与苍生》 / 刘元英 潘国红
- 对《红字》中女主人公的一种荣格式解读 / 颜健生
- 二十世纪浪漫主义思潮的中国特色 / 刘继红
- 汉语中性别歧视的体现及成因 / 颜 妮 李光莉
- 论马克思法学思想产生的历史基础 / 包静雅 王英秀
- 让课堂因生成而美丽 / 李怀芝
- 鲁迅小说肖像描写例谈 / 开 健
- 提高语文课堂教学效率的几点看法 / 邢旺昌
- 古代诗词实践教学探索 / 王建平
- 语文教材评点应从结果性向过程性转变 / 朱一唯
- 语文教学中的创造性思维培养 / 罗有林
- 在模块整合中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 / 朱锡川
- 享受语文多元对话教学的精彩 / 刘红霞
- 语文教学中的审美策略 / 张 婷
- 教师课堂语言小议 / 齐占海
- 语文教学中如何激活思维之花 / 张 花
- 《归园田居(其一)》教学构思 / 苏玉洁
- 审美教育中的四个实施点 / 邓进时
- 陶行知教育理念例谈 / 赵海琪
- 一堂观察暴风雨的语文课 / 汪敦珊
- 古诗鉴赏应试的策略 / 吴成玉
- 语文综合性学习例谈 / 范雪英
- 如何优化语文课堂教学 / 田茂富
- 语文课堂与多媒体教学之关系探究 / 张孝玉
- 略谈高中作文教学的基点 / 夏爱云
- 课内外结合积累写作知识 / 韦卫赤
- 让音乐与审美共舞 / 黄伟娇
- 作文教学中培养学生思维品质的意义 / 常 鑫
- 激活语文课堂方法谈 / 佟立红
- QQ空间在语文写作教学中的运用 / 郑昌平
- 如何让学生快乐作文 / 代西敏
- 语文有效性教学的相关因素 / 朱忠平
- 母语负迁移与高职英语写作教学 / 高 长
- 作文教学应倡导自主 / 曹旭东
- 利用网络技术优化作文教学 / 张玉莲
- 议论文开头出彩方法例谈 / 曹红勇
- 作文评语的人文性和艺术性 / 刘俊峰
- 写作教学杂谈 / 杜东海
- 材料作文之思 / 吴永福
- 作文《花儿》教学案例 / 李金娥
- 让学生成为课堂阅读的主人 / 徐海军
- 人物描写方法例谈 / 马仁昌
- 李白《月下独酌》的浪漫主义情结 / 张朝学
- 从《春江花月夜》谈对诗歌的鉴赏 / 张雁平
- 论作文教学中的情感因素 / 江 洪
- 我对《侯己的汇款单》的伦理学解读 / 肖格格
- 语文阅读教学的心得体会 / 杜永杰
- 在生活中捕捉写景的灵感 / 袁春容 汪训文
- 《第十二夜》中女扮男装手法的运用 / 闫春晶
- 个性化作文教学的理论探索 / 杨亚红
- 阅读教学中的比较探究 / 王琼予
- 《三块钱国币》的幽默艺术 / 杨卫东
- 作文教学中的几点启示 / 贾 涛
- 阅读要开启学生的灵性 / 宓 娟
- 《山居秋暝》的诗画之美 / 任 远
- 寓言作文创新立意四法 / 许 丹
- 《社戏》的人情美 / 张耀东
- 全方位激发学生阅读兴趣 / 张小玲
- 学会捕捉闪光点 / 罗新方
- 《口技》三美 / 张 刚
- 图式理论及其在英语阅读理解中的应用 / 钱建伟
- 孔子思想的当下解读 / 杜 金
- 文本阅读中的情感教育 / 吕 梅
- 压缩语段题解题研究 / 刘 阳
- 文言文背诵方法指导 / 左松良
- 刘兰芝与焦母矛盾的根本何在 / 余礼权
- 少数民族应该称兄弟民族为宜 / 高思华
- 语文作业优化设计之思考 / 于艳华
- 体现人文关怀是语文教育之本源 / 甘春枝
- 电视公益广告中的审美教育 / 王 优
- 英语新闻标题的修辞特点及汉译 / 王 宁
- 关于公共体育课课程设置的几点思考 / 刘晓辉 李 旻
- 透过“汉语热”看国人的英语学习观 / 林志煌
- 在音乐中亲证 / 汪 青
- “右声说”探究 / 于 虹
- 日语 / 王 君
- 人教版教材指误二例 / 陈玉绿
- 中式英语产生的原因及对策 / 尹明花
- 最是雨中有诗情 / 刘 伟
- 试论“所”字结构 / 陈海英
- 英语中副词形容词运用刍议 / 肖新元
- MB.. / 田 雯 朱汉袆
- 囚绿,诠释了爱 / 殷德中
- 现代信息技术与语言文字规范化 / 陈周伟
- 长长的走道 / 赵海妮
- 让标语撑起一片蓝天 / 唐春艳
- 素质教育背景下班级管理实践与思考 / 王晓静
- 中学德育实效性策略探析 / 王鹏家
- 让爱温暖学困生的心灵 / 周红宁
- 让课改之花在校园绚丽绽放 / 马丽娟
- 做一名让人民满意的教师 / 王海芳
- 上海世博会两章 / 李甫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