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文学教育·中旬版 2011年第5期
ID: 152861
文学教育·中旬版 2011年第5期
ID: 152861
浅析黛玉形象的悲怨文化内涵
◇ 尹红霞
[摘要]《红楼梦》中黛玉形象历来受到文人喜爱,其中所蕴含了深厚的悲怨文化内涵。一是强烈的自然生命悲怨意识;二是孤标傲世的生存范式;三是人生价值的现实失落。林黛玉形象所蕴含的这种古代文人中的“悲”与“怨”,使她始终逃脱不了文人共同的悲剧命运。
[关键词]悲怨:生命;价值
对于悲怨和人生之间的关系,我国古人早就注意到了,但起初并未从文学和审美心理角度加以考察。本来,伴随着人类的进化和社会的演进,人的自我意识不断增强,忧思愁绪即成为人们对外在事物的自觉体验和总结。《易·系辞传》就有“作易者,其有忧患乎?”的说法,这种忧思愁绪亦为整个古代思想所认同: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告子下》人之大患,在吾有身。《老子》第十三章儒道两家都认为忧患愁绪与身俱来,为人生所不可免。孔子还把“诗可以怨”作为传授弟子的一个重要信条,即在理论指导方面首次明确地把悲怨和文学联系起来。儒道两大学派长期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精神支柱,上述认识对国人心理之影响可说是根深蒂固的。
悲怨是人的生命力受到阻碍后的情感表现。中国古代悲怨文学是历史上中国文人承受深重苦难的直接后果,它记录和抒发了人生苦痛和理想破灭后的精神苦闷,从中我们不仅可以感知中国古代文人所特有的基本情操和理想人格,体会到蕴含一腔怨恨的悲剧美,而且还可以看出,它揭示了中国古代文人的命运本质。真正渴欲呼吸近代新鲜空气却又在伦理社会的压抑中悲戚无限的是曹雪芹的《红楼梦》。作家的悲剧性生活经历无疑对这座艺术殿堂的建构有一定的引导作用,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作家处于一个“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的时代。他对这一时代之必然走向衰落具有一种惊人的预感:“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
《红楼梦》中黛玉形象历来受到文人喜爱,其中所蕴含了深厚的悲怨文化内涵。
一、是强烈的自然生命悲怨意识
朱光潜在他的《悲剧心理学》第一章开头即引用了元前五世纪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历史》一书中记载的故事:波斯王薛西斯统率大军远征希腊,途中他检阅了全军阵容,为自己的强大力量得意之余,却又潸然泪下。当他的叔父阿塔班努斯对此表示奇怪时,这位声威显赫的国王回答说:“是的,我思前想后,悲悯之感涌上心头,人的一生何其短促,看这黑压压的一片人群,百年之后,就没有一个人还会活着了。”这是我们看到的西方人对生命短促、人生倏忽喟叹的早期记载,悲哀是其情感的基调。古代孟尝君也曾因生命无常而潸然泪下。人生自然生命的短促与无常是每一位敏感的诗人感慨的主题。从诗三百到曹雪芹的《红楼梦》一直如是。黛玉形象就很好体现了这一点。
黛玉《葬花吟》就满载着文人那“惜春长怕花开早”的敏感,“不啼清泪长啼血”、“啼到春归无寻处”的哀歌。而我们在黛玉的《桃花行》和《秋窗风雨夕》的春恨与秋悲中,似乎就感受和谛听到了李贺《将进酒》中“桃花乱落如红雨”的意境,李商隐《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诗那“留得枯荷听雨声”的余响。第七十回《林黛玉重建桃花社》中,黛玉的《唐多令》词有“嫁与东风春不管,凭尔去,忍淹留”之句,即本于李贺《南园》诗句:“可怜日暮嫣香落,嫁与春风不用媒。”黛玉的悲哭是黛玉的也是曹雪芹的悲哭,更是凝聚着千古文人生命意兴和审美情感的千红一哭、万艳同悲。在《红楼梦》中,在黛玉形象上,我们仿佛可以看到千古文士孤鸿般缥缈的身影,听到他们探索、徘徊的足音和隐约、悠长的生命喟叹。
二、是孤标傲世的生存范式
孔子所陶醉的境界,正是“莫(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而这与道家所追求之自由境界相通。所谓“逍遥游”,完全泯灭物、我、主、客,“形如槁木”,“心如死灰”,超功利,超社会,超生死,而作快乐精神的自由飞翔。正因为这种精神自由,能带来无限的精神愉脱,带来天人合一的无限超脱,故为一代代的文人追求。“目送飞鸿,手挥玉弦”(嵇康),“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王羲之),“日暮天无云,春风扇微和”(陶渊明),“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李白),这些都体现着古文人之精神自由,并且以这种新鲜活泼自由自在的心灵领悟世界,使触着的一切呈露着新的灵魂、新的生命。思想独立、精神自由,又怎会凝滞于外物,又怎会容得尘世之渣滓,又怎会戚戚于贫贱,又怎会汲汲于富贵·黛玉性格之孤僻,几乎众口一词。其清雅绝俗、目无尘滓。她是贾府一个高贵的客人,却无法改变远离故土,寄人篱下的处境,显赫的家世,高贵的门第,给无知的心灵带来了优越感,形成了极强的自尊心,卓绝的才华,出众的天资,又常常使她孤高自许,独行其是,所谓落落寡合,孤傲不羁;所谓不畏人言,蔑视舆论;所谓难以理喻,不近人情,都反应着她“世难容”的地位。或许,人世根本就不容许妙玉这样的人存在。妙玉所代表的孤独文人亦处于这样一种状态,他们的好处即在世不容我,我又何苦容于世·由了愤世嫉俗,由了孤高自许,由了恃才傲物,黛玉所代表的孤独文人具有空前的文化魅力。
三、是人生价值的现实失落
在两千余年专制社会机构中,政治权利至高无上,知识分子始终受到强大的中央集权政治力量的控摄,对于凌驾于自身之上的绝对君权充满了敬畏心理和无限恐惧,从而形成了以“求治”为目标的政治型范式。“儒在庙堂”就是儒生被政治同化的一种说明。个体人格只能在国家的历史形态中获得完满实现,这是儒家信念的一条重要原则。正因信奉这种信念,屈原尽管屡遭放逐,仍然心系怀王,不忍去国。孔子作为古代最杰出的知识分子,他关心的并不是什么人文精神,而是为统治者服务的政治哲学。儒家孔子公然树立起“学而优则仕”的旗帜,并且作为帝王与百姓的中介,传统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最强烈。因为他们既要忧君又要忧民。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说出了知识分子的心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而何时而乐耶·其必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做官朝廷,就想着百姓,贬官江湖,则感念君王。进退皆忧,宠辱不计,始终以天下国家为重,满怀忧患心理。中国古代士大夫从孔子、孟子、屈原开始,便一直处在“天降大任于我”、“天生德于予”的庄严责任感和“天不予我”、“君不信我”的负罪感、自责感的矛盾和忧患中。如果说“大任”要求对外在等级之礼的自觉服从,而“忧患”正是对失去自觉服从机会的悲哀和恐惧。中国士大夫浓浓的忧患意识不过是出于尽职尽责之苦恼。如果天降大任于我,使我得以自觉服从、维护等级制,我便充满自豪和满足:如想服从、维护等级制而不能,我便无限悲哀、终生负罪。
然而,知识分子所自负的才情与政治本身就不是一种东西,而知识分子却要以才情去换取人生价值的实现:学而优则仕。于是才情与政治、与现实往往冲突,传统文人悲怨意识中就渗入了价值失落的内涵。
黛玉形象中的悲怨意识内涵中就渗入了浓浓的这种文人价值的失落感。
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社会,宝钗无时无刻不在表现着自己的“无才”,来表现自己大家闺秀的贤良淑德,然而心性直率的林黛玉却将自己的才华展现无遗。
黛玉的《咏菊》、《问菊》、《菊梦》,题目新,诗意新,立意新,潇湘妃子是夺魁的不二人选,在众人的一片赞赏中,黛玉不加掩饰的接受了好评。饮酒作诗历来都是文人所钟爱的,并且不少文人具有这种开阔的情怀,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李白的“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这种的豪放气息是文人的生活态度,也正是因为这样,他们才会与当时的社会格格不入,致使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李白断送了自己的政治前程,但是他们的诗歌却是长久不衰,流传至今。因为他们都是一样的直率和纯真,对待自己内心的感受是毫不掩饰的表达出来,然而这样的真情流露在当时社会的凡夫俗子看来却是傲气十足,于世难容。
林黛玉形象所蕴含的这种古代文人中的“悲”与“怨”。使她始终逃脱不了文人共同的悲剧命运。
参考文献:
[1]徐子方:《千载孤独——中国悲怨文学的生命透视》,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3
[2]蒋和森:《红楼梦论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3]《中国文化要义》,学林出版社。19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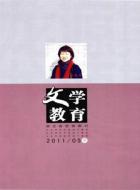
- E.M.福斯特和“奇想”小说 / 郭长娣
- 论陈丹燕上海系列散文 / 赖雅琴 赵芬
- 我国消费金融公司立法现状及缺陷分析 / 黄璇 刘碉琦
- 浅析海子的乡土抒写 / 彭光源
- 《孟子》的交际意识 / 任婧
- 中国海外石油投资法律障碍的解决 / 白云飞 黄思哲
- 我更注重生活本身的力量 / 姜广平
- 浅议“双导”工作在图书管理中的作用 / 谢芳红
- 传播中“罗生门”意义转变探究 / 周婕
- 于连和高家林人物形象比较 / 孙少佩
- 浅析高校外事工作人员的基本素质 / 刘姬
- “潞王陵”研究综述 / 顾伟娜 周丹娅
- 培养与提高学生网站设计的艺术表现能力 / 李镜
- 沙僧:不能被遗忘的人 / 聂俊亮
- ERP技术在测谎研究中的进展 / 欧阳骄 罗著
- 高校深入开展争先创优活动重在把握四性 / 张林仙 吴倩
- 浅析黛玉形象的悲怨文化内涵 / 尹红霞
- 论家庭教育缺陷与青少年犯罪 / 翟真杰
- 试论硕士研究生学习的效能感与倦怠感 / 姜艳
- 中国绿色信贷的法律主体 / 朱剑 甘迎
- “对不起”功能及用法浅析 / 李霞
- 高校学生社会实践申请程序及考核的规范化研究 / 赵笃玲 张进 宗文婷
- 焦虑情绪对高职高专英语学习的影响 / 李云
- 略论院校改革中教员与时俱进的策略 / 刘颖 王单
- 论“无所谓”的发展和演变 / 陆菡
- 浅析体育伦理与高校和谐校园建设的有机结合 / 黄新章 王凤仙
- 从动态对等理论看寒暄语的英译 / 温晓婷
- 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 宗宝璟
- “给力”的背后 / 祝青
- 搭建多元互助平台实施教师分层培养 / 杨苏芬
- 商务英语“专业核心竞争力”提升路径探析 / 袁玺
- 在素质培养实践中推进高校共青团工作 / 李琳 匡列辉
- 大学生应掌握的演讲技巧 / 江淑燕
- 汉语兼语句与英语复合宾语句的对比研究 / 马彩燕
- 有效地利用预测法提高英语听力 / 黄永林
- 新形势下煤矿思想政治工作初探 / 赵永庆 王冬杰 程冬梅
- 初中生学习兴趣培养探析 / 隋爱祥
- 图式理论在高职英语阅读教学中的应用 / 程娟
- 浅谈交互式电子白板在高职教学中的应用 / 赵璐
- 党的建设在机关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作用 / 魏建震
- 体育新闻标题中强势模因的语用功能研究 / 邵艳
- 商务英语教学中互动策略的应用 / 曾葳
- “学案导学”模式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 / 范孝萍
- 民族地区英语专业基础阶段实施学分制的障碍与对策 / 李曦 倪兰芳 修伟
- 传统文化和思维特点对中国英语的影响 / 尹慧玲
- 如何加强中职学校英语教育 / 聂姝雯
- 汉语为载体的网络语言语义结构特征分析 / 山顺章
- 理发店名用语的语用语义考察 / 王冰
- 浅谈音乐创造过程的表现 / 李豫虔
- 探讨新课程下高中自主学习教学模式 / 刘轶群 周晋
- 基于云教育平台的外语移动学习模式研究 / 张薇
- 问题教学法在初中教学中的应用 / 张献和
- 舞蹈作品的命名对其品质提升的作用 / 廖云丽
- 范画在美术教学中的有效应用 / 李春清
- 浅谈儿童钢琴演奏能力的培养 / 姚航
- 以红色为例间析电影中的色彩艺术 / 王贝
- 论民族声乐教学 / 黄敏娇
- 关于对高中课本《大学.节选》研读赏析 / 钟君
- 普通大学生进行体育舞蹈教学后的各项素质变化研究 / 张莉萍
- 语文教学各模块学习方法探究 / 谭宗玺
- 新时期声乐的教学模式探究 / 陈荔
- 浅谈高中语文个性化阅读教学的有效策略 / 敖伟
- 浅谈高师美术学专业生的教学能力的培养 / 邓亮生
- 插上数字化的翅膀,让语文课堂满堂春色 / 柳坚卫
- 谈印象派和摄影 / 王飞
- 诗歌诵读教学探微 / 王志宏
- 校园文化对语文教学资源的影响 / 郭燕芬
- 《四库全书》遍纂的起因 / 姜琳
- 中国民歌在人生礼仪中的运用 / 张俊
- 大学语文与中学语文教材的选文重复问题再探 / 孙娟
- 上好朴实高效的家常课 / 何珞奕
- 晚清海外游历使眼中的西方教育 / 金碧莲
- 舒伯特钢琴即兴曲的浪漫主义演奏风格分析 / 王玮立
- 教师在古诗文教学中如何有效地传承人文精神 / 肖青萍 刘映红
- 医学生汉语应用能力培养对策 / 王春华 陈斌 曾燕
- 浅析《小崔说事》栏目的特色和发展之路 / 陈清晗 李娜
- 语文教学中德育渗透途径浅析 / 刘双龙
- 中学语文课堂有效教学模式初探 / 涂盈盈
- 中职院校音乐教育教学研究 / 安幼幼
- 提高农村学生习作水平的探究 / 刘兴明
- 手机文学中的蒙太奇现象研究 / 高金鹏
- 论普通高校的合唱课教学 / 周伟
- 在政治教育中大力开展人文教育 / 李春梅
- 浅析肖邦叙事曲创作的特点 / 王瑜
- 职业高中财会专业的教育现状与解决对策 / 陈臣英
- 中国与英美语文课程目标比较 / 姚兰
- 激励是一门教学艺术 / 孟丹
- 运用动力原理提高基层部队管理教育水平 / 姚申建 宁顺杰 李枝昌
- 浅论新闻教学与大学生德育建设 / 张俊
- 奏响学生心灵乐章的琴弦 / 何雪凤
-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 朱丽丽
- 书法教学在高校素质教育中的作用与影响 / 高亚男
- 中职教育面临的困境与希望 / 杨亮
- 浅谈学生对历史学习兴趣的培养 / 丁辉
- 略谈高中物理概念学习方法 / 陈鸿远
- 信息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之我见 / 孙钟伟
- 论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策略 / 唐忠勤 高小利
- 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的对立统一 / 吴晓云
- 浅谈精彩课堂的设计 / 何海龙
- 浅谈财务管理沙盘模拟实验教学 / 罗洁
- 新课程改革下学生学习方式的改变 / 曾桥生
- 素质教育中的历史教学 / 黄素辉
- 职业中专学生的班主任德育教育 / 沈振拯
- 做最好的自己 / 倪燕
- 关于高中历史教学改革的几点思考 / 赵曦
- 师生是“学习共同体” / 黄学智
- 体育教师素质初探 / 郭钰
- 刍议班主任走进学生心里的方法 / 陆海浪
- 对高中生物教学的几点思考 / 张民
- 职校体育教学有效性研究 / 马骏
- 培养学生终身体育意识 / 王东旭
- 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 / 余丹 牟映雪
- 祝词贺词文体浅释 / 周桂枝
- 德育思想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渗透 / 林晓菲
- 擦亮武汉城市名片,打造国际都市新形象 / 吴春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