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文学教育·中旬版 2011年第5期
ID: 152854
文学教育·中旬版 2011年第5期
ID: 152854
于连和高家林人物形象比较
◇ 孙少佩
[摘要]于连、高家林都是“个人奋斗者”的典型,反抗与妥协是他们性格的主要特征。幻想——追求——理想的暂时实现——幻灭,是他们人生的共同轨迹。而他们反抗的程度和人生的目标及最后结局的不同,又体现出各自不同的社会历史文化底蕴。
[关键词]于连:高家林;个人奋斗
一、于连是法国王政复辟时期小资产阶级个人奋斗者的典型
他出身于一个由农民转为小工厂主的家庭,身份低微。但他有理想,有抱负,他满怀英雄气概,充满着英雄的幻想。他信奉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不分门第,不讲血统,不问资力,任何人都可以凭借自身的勇敢、才能显身扬名。”于连读过很多的书,但他最喜欢的是两本,一本是卢梭的《忏悔录》,他从卢梭那儿领悟到人是应该有尊严的:第二本是拿破仑的《圣埃伦岛回忆录》,该书记述了拿破仑被囚禁在圣埃伦岛的生活和思想。于连就像这本小说的作者司汤达一样,疯狂地崇拜拿破仑。作为一个没有贵族身份的小工长主的儿子,他觉得拿破仑给他开辟了一条道路,他可以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像拿破仑一样打出一番事业。可他却生不逢时,拿破仑垮台了,波旁王朝复辟了,穿拿破仑军队的红色军装理想破灭,他只能另寻一条出路,那就是穿上教士的黑道袍。为了成功,于连不惜以伪善对付伪善。他对做教士根本没兴趣,甚至还有些仇恨,但为了所谓的受到很多人的尊重和挣很多的钱,他把自己的聪明才智都用来背诵《圣经》:他心里明明只有拿破仑而没有上帝,他却以惊人的勤奋苦苦钻研神学,当众背诵《圣经》和辱骂拿破仑,在虚伪手段的使用上他“进步很快”,但每每他使用虚伪手段时,又觉得是“多么大的困难”。在处处充满着伪善的贝尚松神学院,于连对虚伪恨之入骨,在他虚伪的深处,其实掩藏着一位平民青年正直的一面。
在木耳侯爵府,也是为了成功,为了确立自我,寻找个人幸福。于连顺应形势,顺应环境,把他的聪明才智服务于复辟势力,表现出一种妥协性。他用尽种种手段试图进入上流社会的大门,然而他重重的摔倒了,摔进了敌人的监狱。在狱中,于连由于彻底认清了社会的本质,他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反抗性,他不肯向贵族低头,拒绝上诉,并以死表示对那个阶级的反抗。在法庭上,于连慷慨陈词:“我决不是被我的同阶级的人审判,我在陪审官的席位上,没有看见一个富有的农民,而只是些令人气愤的资产阶级的人。”他一针见血地揭露了统治阶级的险恶用心:“借我来惩戒一般青年——出身低贱,而敢于混迹于富贵人所谓的高等社会”。于连昂首挺胸地走向了刑场。于连的悲剧具有这样的典型意义:在王政复辟时期,一个有进取心的平民青年,试图通过个人奋斗而又不愿与敌人同流合污从而成为上流社会的一员,最终只能是头破血流。
与于连不同,高家林是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初期农村知识分子奋斗者的典型。这个受过现代化春风吹拂的农村青年,强烈渴望从农村走向城市,并因此而开始自己的人生奋斗历程。这期间,他奋斗再奋斗,碰壁再碰壁,觉醒再觉醒,失败再失败,挣扎再挣扎,他的个体奋斗之旅充分展现了在城乡对立的社会结构中,有理想、有追求的农村知识青年理想与现实、生活与命运的充分碰撞。
高家林与于连一样出身低微,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的儿子,他的家是在距离县城十里路的高家村,是大马河州一带一个“满窑没一件值钱东西”的穷户,父母都是勤勤恳恳在黄土地上耕种了一辈子的老实巴交的庄稼人。聊以自慰的是,他是家中的独生子,父母省吃俭用总算供他在县城读完了高中。多年的学校和城市生活开阔了这个农民的儿子的眼界,也塑造了他那富于理想、勇于进取的性格基调。同于连一样,高家林也是一个才华横溢、富于进取的青年,知识面丰富,音乐、绘画样样都行。他的聪明、他的才智也让他像于连一样对自己满怀信心,这种自信也更加激发起他的生活进取心。他要努力通过自己的个人奋斗来改变自身的生存条件,改变自身的社会地位。高中毕业后,逃离农村逃离土地是高家林人生理想的第一步,可“从哪里来哪里去”的社会分工原则堵住了他的理想出口,所幸的是当民办教师给了他与农民不一样的生活机会。正当他以全部的才智与热情投入到乡村的教育事业,以求等待将来更大的发展空间时,马占胜、高明楼等不正之风的代表人物利用职权、损人利己,剥夺了他的民办教师资格,他再次遭受了现实的狠狠一棒。
当农民,决非高家林所愿,但现实没有给他第二条路的选择。在顺德爷爷的感化下,在巧珍姑娘的爱情慰藉下,高家林鼓起了生活的勇气。他开始了在乡村崭新生活篇章。他用科学文化知识来改变农村落后的生活方式,勇敢地追求自由恋爱,骑上自行车与巧珍一起逛县城,搞“卫生革命”等等。高家林的行为在闭塞、落后、贫瘠的西北高原农村刮起了一股旋风,但这一切并没有让他生活的土地发生多么大的震动,他内心对现代文明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又猛烈的撞击心头,他无法与愚昧落后的乡村同呼吸,而面对现实他又无力走出土地的束缚,他常常以“幻想”来实现他的“城市梦想”,即使在他处于最落魄最难堪的生活处境时。他依然坚信自己会走出黄土地。
随着高家林叔叔从部队上复员回当地任劳动局长,高家林的人生之旅“柳暗花明”,又是马占胜、高明楼之流神不知鬼不觉地在一夜之间让高家林从一个普通的农民一跃成为了县委通讯干事,高家林在理想与现实相统一的世界里如鱼得水,取得了事业爱情的双丰收。正当他幸福的向往更灿烂、更广阔的天地时,他又因“走后门”的事情败露,回到了人生的起点。
二、于连和高家林这两个中西文学中个人奋斗者的形象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
低微的出身、强烈的自我意识、坚强的毅力、反抗现存的秩序、追求自由的发展空间,而这一切都企图仅仅凭借他们自身的才智与惊人的意志力去得以实现;反抗与妥协是他们主要的性格特征,他们对自己人格尊严的维护常常表现为对权势者的蔑视和对不公平不合理的现实的倔强的对抗心理,而一旦遇到利用权势可以实现自己的目标时,他们又坦然地利用权势而不惜放弃斗争。当于连被木耳侯爵赏识时,他就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充当复辟阴谋活动的鹰犬,把聪明才智完全服务于复辟了的波旁王朝。由此可见,于连虽然从卢梭那获得了自由、尊严的思想,但卢梭想到的是把整个社会来个颠覆,他的《社会契约论》成了雅各宾党人在法国大革命中的《圣经》,而于连想到的不是颠覆一个社会,而是在有钱人的宴席上给自己加一把椅子,他虽崇拜拿破仑,也有拿破仑似的野心,但是他没有拿破仑的政治理想。他想到的只是怎样给自己开辟一条飞黄腾达的道路。同样,当高家林被不正之风剥夺了他民办教师的权利时,他表现出了强烈的愤怒与抗争,而当不正之风的“好处”光临他时,他只是有些“惴惴不安”,更多的则是“高兴得如醉如狂”。于连和高家林的个人奋斗轨迹都是:幻想——追求——理想的暂时实现——幻灭。
高家林虽然不象于连那样成为了世界文学画廊里个人奋斗者的典型形象,但他也概括了中国新时期社会转折之初农村与城市“交叉地带”的知识青年的苦闷与追求,他不满现状,要求改变自己的生活处境,不想像父辈那样地生活,这种愿望是对因循守旧的古老的生活方式的一种反抗,潜藏着可贵的变革现实的希望,这是历史的要求,这也反映了中国社会改革之初许多像他那样的青年的处境,因而有着一定的典型意义。于连的人生历程太过短暂,年纪轻轻就被社会所扼杀;而高家林的人生之路才刚刚开始。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开放式结构已经取代了高家林时代的计划经济的封闭性,高家林式的的有志青年在新的时代里正在追求着自己的人生价值,但高家林的人物形象依然提醒着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如何正确地引导青年认识国家利益和个人前途的关系,脚踏实地地开拓人生之路,最大限度地发挥像高家林这样有理想、有文化、有知识的农村青年去投入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当中仍是国家当务之急。
参考文献:
[1][法]司汤达:《红与黑》,许渊冲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93
[2]路遥:《路遥全集,早晨从中午开始》,广州出版社、太白文艺出版社。2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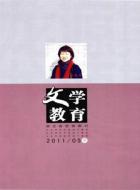
- E.M.福斯特和“奇想”小说 / 郭长娣
- 论陈丹燕上海系列散文 / 赖雅琴 赵芬
- 我国消费金融公司立法现状及缺陷分析 / 黄璇 刘碉琦
- 浅析海子的乡土抒写 / 彭光源
- 《孟子》的交际意识 / 任婧
- 中国海外石油投资法律障碍的解决 / 白云飞 黄思哲
- 我更注重生活本身的力量 / 姜广平
- 浅议“双导”工作在图书管理中的作用 / 谢芳红
- 传播中“罗生门”意义转变探究 / 周婕
- 于连和高家林人物形象比较 / 孙少佩
- 浅析高校外事工作人员的基本素质 / 刘姬
- “潞王陵”研究综述 / 顾伟娜 周丹娅
- 培养与提高学生网站设计的艺术表现能力 / 李镜
- 沙僧:不能被遗忘的人 / 聂俊亮
- ERP技术在测谎研究中的进展 / 欧阳骄 罗著
- 高校深入开展争先创优活动重在把握四性 / 张林仙 吴倩
- 浅析黛玉形象的悲怨文化内涵 / 尹红霞
- 论家庭教育缺陷与青少年犯罪 / 翟真杰
- 试论硕士研究生学习的效能感与倦怠感 / 姜艳
- 中国绿色信贷的法律主体 / 朱剑 甘迎
- “对不起”功能及用法浅析 / 李霞
- 高校学生社会实践申请程序及考核的规范化研究 / 赵笃玲 张进 宗文婷
- 焦虑情绪对高职高专英语学习的影响 / 李云
- 略论院校改革中教员与时俱进的策略 / 刘颖 王单
- 论“无所谓”的发展和演变 / 陆菡
- 浅析体育伦理与高校和谐校园建设的有机结合 / 黄新章 王凤仙
- 从动态对等理论看寒暄语的英译 / 温晓婷
- 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 宗宝璟
- “给力”的背后 / 祝青
- 搭建多元互助平台实施教师分层培养 / 杨苏芬
- 商务英语“专业核心竞争力”提升路径探析 / 袁玺
- 在素质培养实践中推进高校共青团工作 / 李琳 匡列辉
- 大学生应掌握的演讲技巧 / 江淑燕
- 汉语兼语句与英语复合宾语句的对比研究 / 马彩燕
- 有效地利用预测法提高英语听力 / 黄永林
- 新形势下煤矿思想政治工作初探 / 赵永庆 王冬杰 程冬梅
- 初中生学习兴趣培养探析 / 隋爱祥
- 图式理论在高职英语阅读教学中的应用 / 程娟
- 浅谈交互式电子白板在高职教学中的应用 / 赵璐
- 党的建设在机关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作用 / 魏建震
- 体育新闻标题中强势模因的语用功能研究 / 邵艳
- 商务英语教学中互动策略的应用 / 曾葳
- “学案导学”模式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 / 范孝萍
- 民族地区英语专业基础阶段实施学分制的障碍与对策 / 李曦 倪兰芳 修伟
- 传统文化和思维特点对中国英语的影响 / 尹慧玲
- 如何加强中职学校英语教育 / 聂姝雯
- 汉语为载体的网络语言语义结构特征分析 / 山顺章
- 理发店名用语的语用语义考察 / 王冰
- 浅谈音乐创造过程的表现 / 李豫虔
- 探讨新课程下高中自主学习教学模式 / 刘轶群 周晋
- 基于云教育平台的外语移动学习模式研究 / 张薇
- 问题教学法在初中教学中的应用 / 张献和
- 舞蹈作品的命名对其品质提升的作用 / 廖云丽
- 范画在美术教学中的有效应用 / 李春清
- 浅谈儿童钢琴演奏能力的培养 / 姚航
- 以红色为例间析电影中的色彩艺术 / 王贝
- 论民族声乐教学 / 黄敏娇
- 关于对高中课本《大学.节选》研读赏析 / 钟君
- 普通大学生进行体育舞蹈教学后的各项素质变化研究 / 张莉萍
- 语文教学各模块学习方法探究 / 谭宗玺
- 新时期声乐的教学模式探究 / 陈荔
- 浅谈高中语文个性化阅读教学的有效策略 / 敖伟
- 浅谈高师美术学专业生的教学能力的培养 / 邓亮生
- 插上数字化的翅膀,让语文课堂满堂春色 / 柳坚卫
- 谈印象派和摄影 / 王飞
- 诗歌诵读教学探微 / 王志宏
- 校园文化对语文教学资源的影响 / 郭燕芬
- 《四库全书》遍纂的起因 / 姜琳
- 中国民歌在人生礼仪中的运用 / 张俊
- 大学语文与中学语文教材的选文重复问题再探 / 孙娟
- 上好朴实高效的家常课 / 何珞奕
- 晚清海外游历使眼中的西方教育 / 金碧莲
- 舒伯特钢琴即兴曲的浪漫主义演奏风格分析 / 王玮立
- 教师在古诗文教学中如何有效地传承人文精神 / 肖青萍 刘映红
- 医学生汉语应用能力培养对策 / 王春华 陈斌 曾燕
- 浅析《小崔说事》栏目的特色和发展之路 / 陈清晗 李娜
- 语文教学中德育渗透途径浅析 / 刘双龙
- 中学语文课堂有效教学模式初探 / 涂盈盈
- 中职院校音乐教育教学研究 / 安幼幼
- 提高农村学生习作水平的探究 / 刘兴明
- 手机文学中的蒙太奇现象研究 / 高金鹏
- 论普通高校的合唱课教学 / 周伟
- 在政治教育中大力开展人文教育 / 李春梅
- 浅析肖邦叙事曲创作的特点 / 王瑜
- 职业高中财会专业的教育现状与解决对策 / 陈臣英
- 中国与英美语文课程目标比较 / 姚兰
- 激励是一门教学艺术 / 孟丹
- 运用动力原理提高基层部队管理教育水平 / 姚申建 宁顺杰 李枝昌
- 浅论新闻教学与大学生德育建设 / 张俊
- 奏响学生心灵乐章的琴弦 / 何雪凤
-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 朱丽丽
- 书法教学在高校素质教育中的作用与影响 / 高亚男
- 中职教育面临的困境与希望 / 杨亮
- 浅谈学生对历史学习兴趣的培养 / 丁辉
- 略谈高中物理概念学习方法 / 陈鸿远
- 信息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之我见 / 孙钟伟
- 论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策略 / 唐忠勤 高小利
- 思想政治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的对立统一 / 吴晓云
- 浅谈精彩课堂的设计 / 何海龙
- 浅谈财务管理沙盘模拟实验教学 / 罗洁
- 新课程改革下学生学习方式的改变 / 曾桥生
- 素质教育中的历史教学 / 黄素辉
- 职业中专学生的班主任德育教育 / 沈振拯
- 做最好的自己 / 倪燕
- 关于高中历史教学改革的几点思考 / 赵曦
- 师生是“学习共同体” / 黄学智
- 体育教师素质初探 / 郭钰
- 刍议班主任走进学生心里的方法 / 陆海浪
- 对高中生物教学的几点思考 / 张民
- 职校体育教学有效性研究 / 马骏
- 培养学生终身体育意识 / 王东旭
- 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 / 余丹 牟映雪
- 祝词贺词文体浅释 / 周桂枝
- 德育思想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渗透 / 林晓菲
- 擦亮武汉城市名片,打造国际都市新形象 / 吴春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