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11年第2期
ID: 155396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11年第2期
ID: 155396
苏轼的政治人格研究
◇ 刘宇辉
内容摘要:按中学历史知识,王安石是改革派,司马光是保守派。为使学生们有较为准确的认识和理解,本文从史实上给苏轼予以全面审视。
关键词:苏轼 政治人格 审视
据史学家分析,从宋真宗即位时起(997年),北宋王朝就进入了中衰期,内忧外患,朝政日非。领导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王禹偁,就向真宗皇帝进言革新朝政,从而成为有宋一朝酝酿革新思潮的先驱者。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6年),苏轼出生时,宋廷已处于中衰期中叶,到其去世时,宋王朝已到了晚期的中叶而日趋灭亡。苏轼诞生时,由于70余年的弊政累积,宋廷陷入了“冗兵、冗官、冗费”的困境,突显“积贫积弱”两大问题。外不能应付外来的军事威胁,内无法解决入不敷出的财政危机。朝野上下谋求革新,清除弊端的思潮,就更加激昂。于是“变法”、“新政”也就相时而出。可以说,苏轼一生六十六年就生活在这种政治环境中。少年时代,有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青年时代有庆历精神所激励的“士君子”思变求治风潮,“闭门书史丛,开口治乱根”。中年时代有王安石主持的“熙宁变法”,老年时代有司马光主政的“元祐更化”,这些都是由朝政困境所牵引的政治风云变幻。在这种风云变幻中,苏轼厕身于分别大他17岁和15岁的司马光与王安石之间,同朝际会。三人都秉承着“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的精神,面对同样的现实问题,在同一政治舞台上,自觉或不自觉扮演着不同的政治角色,各人都认定自己的办法——政治主张。
一.苏轼的政治主张
时代造就人才,苏轼从青少年时代,就一直受着革新思潮的浸润和熏陶。从王禹偁、欧阳修、范仲淹的诗,文学习中;从庆历新政短命夭折的教训思考中;从深受庆历新政影响且又主张革新的父亲,苏洵,所给予的教养中;苏轼成长为救时治弊的革新主义者。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责任感,使他敢于展示自己的政治主张。
宋仁宗嘉佑六年,二十六岁的苏轼,参加制科考试的夺魁策论,最能反映他的政治主张。这是一组系列性的政论文章,有《进策》25篇,分《策略》5篇,《策别》17篇,《策断》3篇,《礼以养人为本》和《御试制科策》等。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如下诸点:
朝政的核心之弊是“民生不安,财用不足,上下不通,边患不息”四端。
欲除积弊,既要稳妥可靠,也要有毅力和决心。“此病之所由起者深,则其所以治之者,固非鲁莽因循苟且之所能去也。”这实质上是隐指“庆历新政”失败的内因和外因,即主持者思虑不周,皇帝又动摇不定。
对待弊政的态度只能是革新除旧。“方今之世,苟不能涤荡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见其可也”。
革新除旧的方式,绝不是“托古改制”所标榜的“法先王”、“效汉唐”。所谓“天下之士,方且拾掇三代之遗文,补茸汉唐之故事,以为区区之论可以济世,不已疏乎?”这实际上是否定某些借托古改制而施行改革。苏轼认为,改革应是针对现实,思谋良策,何须托古!
前三项弊端的解决对策以《安万民》、《厚财赋》和《课百官》三个专题,分别论证具体解决办法。
如何息边患,在《训兵旅》和《策断》的专题论证中,详述治军之法和对外作战。
史家认为,苏轼的这些论证:
儒家的救时观念,与王禹偁、范仲淹一脉相承,寄希望于明君、贤相、廉官、勤吏,以求治世而造福万民。
民为邦本,革新应以解决民生问题为前提,这是一种最为根本的政治见解。
对解决各项弊端所做的对策富有针对性,有可操作性,绝非书生空谈。
这是一种长治久安的远图主张,富有战略眼光。如《均户口》一策,向京城腹地移民,即可开发地利以生财,又可为京城防御外敌增强后方依托。
敢于触及敏感问题,如主张专任官员以提高效率,以土兵渐代禁军来增强战斗力。这有悖于防止重臣篡权、武人割据的“祖宗成法”,展现了一个改革家的气魄。
由此可以看出,苏轼在振兴朝政上,富有积极的革新愿望,其为政之方的底蕴,颇有厚实的积淀。史载,这组策论,为北宋开制科以来,成绩最优秀者,苏轼也就名震朝野,誉满士林。
二.“熙宁变法”苏轼与王安石的政见分歧
熙宁二年二月,神宗擢用王安石主政,同时成立一个名为“制置三司条例司”的变法领导机构,也由王安石主持以更易法制。于是开始了以财政改革为主体的“变法”。从熙宁二年七月到熙宁六年八月,先后颁布推行了十余种“新法”,史称“熙宁新法”或“熙宁新政”。
由于志在富国强兵,“新法”基本上分属两大类。一类为理财,一类为整军,只不过绝大部分都是理财。普遍认为理财“新法”贯穿着一条红线即“刻意求财”。只有农田水利一项例外,但也有许多“副作用”。所以“新法”遭到朝野臣民的强烈反对,连王安石的两个弟弟居然也属反对者之列。史家认为,王安石的理财思路有其进步意义,他注意到了别人不曾注意的潜在的商品经济效益,把这种可利国的效益收归国有,理应得到赞同和支持。然而之所以被人理解为是“效汉唐”的“敛财之术”,“与商贾争利”,这固然是因为反对者所持有的政治立场不同,实则也与“新法”中的固有疏陋和推行中的种种负面影响不无关系。
据有关史料记载,苏轼也有比一般士人进步的“义利观”。从这点上说,他还不至于断然全部否定“新法”。从理论上说,“新法”的理财思路有其合理的内核,但是可得而论的东西并不一定就可得而行。法不严密,就会产生歧义,思想上难得统一;行之不当,理财有可能沦为“敛财”;从而“新法”非但不能惠民,反而会扰民;朝政非但不能“革新”,反而会招来新的弊端。以王安石“自负”、“器小”“是非谬于常人”的性格,“新法”中潜在的缺陷,苏轼预感到,“新法”有可能会被导致失败。
经过沉默观察和冷静思考,苏轼或是对“新法”打算废除以诗、赋取士的做法,客观地提出善意的批评,认为这会带来偏废文学的后果(见苏轼《议学校贡举状》);或是在《国学秋试策》和《拟进士对御试策》中,用“符坚伐晋以独断而亡”,“燕哙专任子之而败”的典故,以“勤而或乱或治,断而或兴或衰,信而或安或危”的辩证命题,讽喻神宗皇帝“专信”王安石,王安石的“独断”,不一定会使“新法”有理想的效果,说不定会事与愿违。随着“新法”的不断出笼,“新法”推行中的负面影响也日渐增多,反对之声也越来越强烈。苏轼在《上神宗皇帝书》中,对已颁行的“新法”全面阐述自己的看法。
三.苏轼的政治人格
苏轼在熙宁时,与王安石相比,应是疏远小臣。在元祐时,与司马光相比,也非权重近臣。他敢于和这两位掌权大臣唱反调,其后果将是什么,他这样的聪明人,不是不明白。
他在家书中常有“大忤权贵”,“颇为当柄者所愤,孤远恐不自全,日虞罪捩”。又说“不能降意委曲随世,其为齑粉必矣”。他在《上神宗皇帝书》中也说:“臣所惧者,讽刺既众,怨仇实多,必将诋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虽欲赦臣而不可得,岂不殆哉!死亡不辞,但恐天下以臣为戒,无复言者。是以思之经月,夜以继昼,表成复毁,至于再三。”
由此可见,他有过顾虑,有过思想斗争,设想过可能会遭受到的某些危害。后来事态的发展也证实了他的这些预感,元丰三年的“乌台诗案”,就使他下狱130多天,几乎被杀头。可他为什么不能蛰伏呢?非得要“心持公直,行不谋私”呢?他在元祐六年《杭州召还乞郡状》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臣昔于治平中,自凤翔职官得替入朝,首被英宗皇帝知遇,欲骤用臣……及服阕入觐,便蒙神宗皇帝召对,面赐奖激,许臣职外言事……是时王安石新得政,变易法度,臣若少加附会,进用必可。自惟远人,蒙二帝非常之知,不忍欺天负心,欲具论安石所为不可施行状,以裨万一……及陛下即位,起臣于贬所,不及一年,备位禁林,遭遇之异,古今无比。臣每自惟昆虫草木之微,无以仰报天地生成之德,惟有独立不倚,知无不言,可以少报万一……因亦与司马光异论。
在这里,他明白说出他的追求,即“士君子精神”所倡导的,以“犯颜纳说为忠”的政治道德。封建社会里不乏有一种被称为“孤臣”的人。这种人心怀忠诚而不容于某些当权者,即使当权者也并非奸狡之辈,甚或也是贤达之人。之所以为此,乃为恪守信仰,坚持独立政见,不趋炎附势,不见风使舵,直接向君主负责,而不怕孤立,这就是所谓的“孤忠”,苏轼就是这种人。
曾与苏轼为政敌的司马光门生刘安世,晚年曾给他的弟子说起过苏轼:“士大夫只看立朝大节如何,若大节一亏,则虽有细行,不足赎也。东坡立朝大节极可观,才高意广,惟己之是信,在元丰,则不容于元丰,人欲杀之;在元祐,则虽与老先生(指司马光)议论,亦有不合处,非随时上下人也。”
刘安世对苏轼的这个评价非常客观,也甚为准确。他所谓的立朝大节就是坚持独立政见,不随时上下,既不附和王安石,也不迎合司马光。
最后,我想用苏轼的一位挚友,徐积,给苏轼的挽词,来结束此文。“直道谋身少,孤忠为国多”,这就是我想告诉学生们的苏轼的政治人格。
刘宇辉,教师,现居广东深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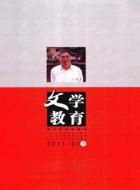
- 《三国演义》中的“军事地图”研究 / 高峰 曹俊生
- 莫泊桑小说中的隐藏艺术 / 吴雯雯
- 致力于近代诗人研究的学者丘铸昌 / 程祖灏
- 古今汉语里的“左右”释义 / 陈红芹
- 文学与时代 / 张笑天
- 留学生汉语因果类复句偏误分析 / 董福升
- 鲜花的力量 / 路文彬
- 论闲愁词的美学特征 / 袁和平 袁娇萍
- 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创作及理论研究现状管窥 / 滕永文
- 苏轼的政治人格研究 / 刘宇辉
- 古代诗词中清酒与浊酒的意象 / 张楠
- 英语文学教学中的跨文化意识培养 / 张欣
- 对古典诗词中桃杏寓意的探求 / 程仙梦
- 林非的散文观及其创作实践 / 罗建维
- 生态式教学模式下的文艺学课程考试 / 罗祖文
- 用激情锻造高效课堂 / 陈锁斌
- 如何让经典真正走进学生心间 / 张所帅
- 课堂教学最优化的有效途径 / 汪厚旬
- 优质语文课堂教学的途径与方法 / 崔燕霞
- 试论英语教学中语言意识的培养 / 宋艳
- 语文教学中如何巧用布白艺术 / 翁晔
- 大学英语分级教学和层次培养改革探讨 / 鲍娟
- 《百合花》:一部革命年代的爱情牧歌 / 田璐莎
- 从外语磨蚀看大学英语教与学 / 彭菲
- 提高语文课堂效率方法谈 / 俞彩娥
- 莫泊桑短篇小说《项链》重读 / 邱兴宇
- 古代诗歌形象鉴赏答题技巧 / 赵丹华 王东亮
- 迷失中的反抗与回归 / 孙淼
- 强化语文作业管理课题实验结论 / 张斌 郑玉琼
- 莫言《民间音乐》的奇与美 / 刘莉 郜国旗
- 语文课在中等卫生职业教育中的特殊地位 / 刘英
- 语文课堂中的幽默妙用 / 毕庆
- 杜甫诗作《燕子来舟中作》诗意解析 / 余建平 刘至彦
- 关于激发学生主体功能的若干认识 / 张丹华
- 浅谈结构主义与生成语言学 / 李凯
- 论《哈姆莱特》对鬼魂形象的刻画 / 崔永杰
- 语文课堂规律性探讨 / 陈水明
- 确立学生主体地位是教改的支点 / 陈兰珍
- 解读《边城》中的美与悲 / 曹瑞霞
- 学生自主预习能力的培养 / 崔秀竹
- 语文教学中如何激发学生情感 / 曹龙春
- 情真意切悼亡妇 / 杨卫东
- 在口语表达中找到自信 / 曾庆华
- 韩国语教学中关于韩国文化教育方案的建议 / 金美娜
- 《一个扑朔迷离的间谍故事》的主题解读 / 张文军
- 亲子阅读的现状与指导策略 / 申健强 王开芳
- 图画书阅读与儿童生命教育 / 王姗
- 解析《梦游天姥吟留别》的“梦” / 周国瑞
- 接受美学对语文阅读教学的启示 / 张民锋
- 语文教学中学生创新素质的培养 / 邸丽媛 李世袭
- 应用文写作应突出学生就业需求 / 高静 宋秀红
- “对话”阅读教学现状的思考和探究 / 盛严宏
- 改善中学生作文现状的可行性对策 / 董旭午
- 把课堂还给学生 / 许俊凌
- 试论应用写作课程研究性学习途径 / 伍桂蓉
- 诗歌朗读的教学艺术 / 袁欣伦
- 应用文教学实践性的几点探索 / 于兴菊
- 让学生插上想象的翅膀朗读 / 杨丹阳
- 初中生语文阅读能力培养之我见 / 徐华
- 怎样有效进行作文个性化教学 / 何莉
- 职校精品课程建设的实践和成效 / 吴仁玉
- 提高学生作文水平浅议 / 王占祥
- 浅谈职业学校学生社团的建设 / 吴文杰
- 基础学段名著阅读策略探微 / 王佩波
- 《六国论》教学设计 / 杨丽妃
- 中等职业学校英语课的有效教学 / 周永霞
- 说说情景交融 / 张清湘
- 浅谈中学生阅读能力的培养 / 郭俊娟
- 评邢桂轮先生的《回望编辑生涯》 / 张静
- 《诲人不倦》教学设计 / 贾桂强
- 让巧媳妇有米可炊 / 赵仁明
- 《听潮》教案设计 / 王凤云 孙云芳
- 我的三个作文观 / 肖信斌
- “流响”为何要“出疏桐” / 仲济民
- 略谈《外国小说欣赏》的教学 / 陆美娟
- 标点符号的修辞作用 / 李墨
- 话说“这个”“那个”之类 / 夏增田
- 如何减少习作中的错别字 / 李补月
- 与白岩松近在咫尺 / 陈筱
- 教育博客在教育中的作用 / 郭宏冰
- 在燃烧中永生 / 吴玉华
- 看物性判断对比和衬托 / 所福亮
- 梦回水高 / 何况
- 幼儿识字的几点经验 / 赵桂香
- 品味四季 / 陈芬
- 文学熏陶与班级管理 / 鲁世新 林日萍
- 浅谈习惯养成教育 / 柳明
- 师生关系的处理技巧 / 何和平
- 新课改下高中体育教学反思 / 池骋
- 如何提高学生学习严肃音乐的兴趣 / 张明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