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11年第2期
ID: 155412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11年第2期
ID: 155412
《百合花》:一部革命年代的爱情牧歌
◇ 田璐莎
内容摘要:茹志鹃的《百合花》是十七年时期革命历史题材短篇小说的代表作之一,它采用当时主流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手法进行英雄叙事。同时,它又是一支“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歌颂了人情人性,具有显著的浪漫主义气息。本文将结合《百合花》,论述“十七年文学”中现实主义思潮和浪漫主义思潮的冲突与融合。
关键词:《百合花》 现实主义 浪漫主义 冲突 融合
茹志鹃的短篇小说《百合花》是十七年时期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代表作之一。从表层看,它是一部合乎主流意识形态的作品,遵循当时大力提倡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则创作而成,谱写了一曲英雄的赞歌,讴歌了浓浓的“军民鱼水情”。然而,通过对这篇小说的深层解读,我们可以发现,《百合花》其实是“十七年文学”的一个异数。作者茹志鹃自己称它为“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它颂扬了纯洁的人类之爱,流露出浓郁的田园牧歌式的浪漫主义气息。只不过作者通过“话语蕴藉”成功地找到了一个合乎于主流文学的叙事载体,顺利地把人性故事掩盖于英雄传奇之下,完成了两者的糅合。同时,《百合花》也体现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种在十七年时期相互排斥、互相悖离的文学思潮的暂时调和。
一.现实主义的英雄赞歌
自从1953年第二次全国文代会确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文艺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以后,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便在新时期以前的当代文坛中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这种压倒性的优势是由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状况决定的。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和近百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急切地需要破旧树新,改革一切不符合新的社会形态的因素。现实主义因其客观真实地反映现实社会的特征高度契合了中国历史社会变革的任务,因此得以在中国扎根发芽、枝繁叶茂。应当说明的是,当时被大力提倡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而是一种革命现实主义,即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为革命斗争服务的现实主义。这实际上是对现实主义创作的一种极大的限制。因此,在新时期以前的当代文学史上,现实主义就被看做是进步的、革命的,而浪漫主义则被贴上了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的标签。在这种理论背景下,为了迎合主流意识形态的选择,受当时严格的文艺政策控制的作家们纷纷转向现实主义创作,无论是小说还是诗歌戏剧,无论是农村题材还是革命历史题材,都呈现出对时代的宏大叙事模式,散发着昂扬向上的革命热情。
《百合花》也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烙印。小说写的是发生在战斗前沿包扎所的故事,一个出身农村的军队士兵“小通讯员”与两位女性“我”和“新媳妇”在激烈战斗环境下的情感关系。茅盾最早从政治意识形态层面对《百合花》进行解读,他把这个故事的主题概括为“反映了解放军的崇高品质(通过那位可敬可爱的通讯员)和人民爱护解放军的真诚(通过那位在包扎所服务的少妇)”,[1]赞颂战士英雄形象和军民鱼水情。虽然《百合花》的主题内涵远不止于此,但是不能否认,这篇小说确实具有政治意识形态层面的思想意义与价值。包扎所没有被子,向群众借,群众们大多借了出来;没有护理人员就让群众顶替;整个包扎所的后勤保障,也是由群众完成的。担架队由群众组成,他们看见手榴弹,连卧倒的常识都不懂,小通讯员为了救护担架队的民众而牺牲了自己。广大人民群众因为知道“共产党的部队,打仗是为了老百姓”的道理,才自觉为前线服务。这些内容的确都反映了人民军队与人民之间已经建立起了深厚的革命感情。
英雄人物的塑造也是“十七年文学”的重要特征。几乎每一部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中都会塑造一位革命英雄,《百合花》也不例外。不同的是,《百合花》中的英雄人物——小通讯员——并不是一位“高、大、全”式的完美英雄,也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和业绩。他更接近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会害羞、会赌气,也有失败而归的经历(借被子不成),甚至也不是牺牲在与敌人的正面交锋中,而是为了救担架队被手榴弹炸死。但是这丝毫不影响他在我们心中的英雄形象,反而因为其可亲、可爱而显得更为真实可感,值得尊敬。小通讯员用他火热的青春、赤诚的爱民之心演绎了一曲英雄的赞歌。
《百合花》正是运用现实主义的手法进行革命叙事,谱写了一曲英雄赞歌,讴歌了深厚的军民鱼水情,才获得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成就了其在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二.浪漫主义的爱情牧歌
在新时期以前的当代文学史上,浪漫主义文学从来就没有与现实主义平分秋色,而总是处于一种伴随状态,这与其自身特点休戚相关。现实主义是理性、客观的,而浪漫主义恰恰相反,它宣扬个人的主体性,注重个人情感表达,抒发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这种个人主义的价值取向与社会主义社会集体主义的主流价值观相抵触,决定了它必定会遭到压抑。与革命现实主义相对,当代文学史上也存在革命浪漫主义一说。革命浪漫主义实际上等同于浮夸之风,是一种伪浪漫主义,也是极“左”思潮蔓延到文艺领域的产物,意义价值不大。
正因为如此,十七年时期的主流文学中极少可以看到浪漫主义的身影,但《百合花》是个例外。《百合花》虽然恪守的是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却颇有一些浪漫主义的特征。
在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以再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为主要题材的革命历史小说担负着历史经典化的政治使命。但即使是这样写实的创作,也有着“可写”与“不可写”的限制。只有在主旨上回答和揭示革命的必要性和必胜性,在题材上实现重大革命事实和艺术虚构的融合,凸显英雄人物,抒发乐观豪放的感情基调的作品,才可以进入主流文学;至于儿女情长、花前月下、个人哀乐都是被排斥和蔑视的。[2]这样的小说倘若脱下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外衣,还会剩下点什么呢?
《百合花》却不同,撇开政治意识形态的东西不谈,它还可以从普遍人性的层面来进行解读。小说作者茹志鹃自己说:“它实实在在是一篇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可见这才是作者写作的本意。这句话的涵义是有些含混的。前一个“爱情”自然是指狭义的男女之爱;后一个“爱情”则应该指的是广义的“爱”和广义的“情”,既包括男女之间的纯洁之爱,也包括一切人间的友爱和温情,更是对人性美、人情美的热爱。这样一来,《百合花》的双重意蕴使它在主流文学的宏大叙事框架下变换着摇曳多姿的个人风格,充满了田园牧歌式的浪漫气息。
《百合花》作为一篇革命历史小说,并没有把精力放在战争场景的展开和描述上,而是反其道而行之,着力描写了被当时大多数作家所忽视的人的细腻情感。通篇小说虽然是以战争为背景,却没有出现一处正面的战争场面。小说的主体是战斗开始前小通讯员把“我”送去前线的包扎所,二人又一同去借被子,从而偶遇了小说另一主要人物——新媳妇,并围绕三个人展开了一系列故事。但即使小说的最后激烈的战斗真的开始了,小说的场景也并没有从包扎所切换到战场,战斗的消息都是由伤员和战斗队带来的。这一切都可以表明,作者的初衷并不是要向我们展示一场壮烈的战争,而是展现战争掩盖之下的人性人情。小说中几位主人公的个性无疑是可爱的。通讯员在送我去包扎所的路上,“一开始就把我撩下几丈远”,“总和我保持丈把远的距离”,以及“我”在他旁边坐下问他话时他脸红,半晌才做出回答,都表现了一个十九岁大男孩的腼腆与羞涩。他借不到被子时说“老百姓死封建”,又让我们看到了他身上另一种真实的可爱。而他照顾到“我”走得慢,就在路边站下等我,了解到新媳妇不借被子的原因后对她的歉疚,以及他拿硬馒头给“我”开饭,则是他对人的关心。新媳妇身上也有活泼、纯真的个性和美。她在“我”去借被子时止不住地笑,到包扎所时问“我”“那位同志弟到哪里去了”,“然后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说“他可受我的气了”,无不体现了她的娇羞和善良。小说中的人际关系也是自然而和谐的。“我”对小通讯员由刚开始时的生气进而变为有几分喜爱,并在战斗开始后紧张地为其担心。新媳妇对通讯员则由善意的捉弄进而变为歉意,询问和关心这位“同志弟”。小说中还隐约涉及到了“我”和小通讯员之间在革命战友身份下隐藏的朦胧好感,以及新媳妇与通讯员之间在军民情谊掩盖下的微妙情感。但是这种若有若无的情感绝不是庸俗的三角恋,而是青年男女纯洁无瑕的精神之爱。
小说的高潮是在小通讯员受伤之后:“我”“强忍着眼泪”,“磕磕绊绊地跑去找医生”;而新媳妇一改先前的忸怩羞涩,“庄严而虔诚地给他拭着身子”,在医生已经宣布治疗无效后,依然逢着他衣服上的破洞,特别是最后“气汹汹”地用自己唯一的百合花被子给他陪葬。直到这里,先前的爱已经升华成了一种对生命逝去的惋惜和敬畏。白色的百合花象征着战争时期人与人之间圣洁美好的情爱,一曲人性美和人情美的牧歌在战火硝烟的背后悄悄升起。
《百合花》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的人物形象并没有被塑造成那个时代普遍的披着政治身份外衣的呆板空洞的模式化人物。他们不仅是战士和群众,更是一个个独立本真的人,他们有着自己鲜明的爱憎和情感,并且用自己的言语和行动创造着世间的美好与温情。这种对个人主体的强调、个体情感的抒发,以及对人情美和人性美的理想化的追求,都与浪漫主义的特征相吻合。
三.冲突与融合
中国文学的传统是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文学思潮的交替发展中形成的,无论以谁为潮头,其正确的走向总是表现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相互吸收和相互弥补,在相辅相成中推动中国文学的前进。这两大文学思潮之所以能够互相借鉴、互相融合,是因为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基点,即对人的关注;而它们的分流,则主要体现为对人的不同认识和表现人性的不同方法。[3]浪漫主义始终强调个人的主体性,高举个性自由的旗帜;现实主义则把人放置于历史洪流和社会环境中进行考察,强调人的社会性。
中国当代文学继承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文学传统,并使之有了进一步发展。“十七年文学”时期,现实主义长期占据中国文学的主潮,而浪漫主义的地位往往遭到抑制,是有深层原因的。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国门较为封闭,同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并不多,很少有新鲜的文学思潮传入我国,这种封闭带来了现实主义大一统的局限。另一方面,随着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等政治思潮的盛行,人的社会性进一步得到强调,人们被要求服从于集体,个人主体意识遭到扼杀。这种政治思潮的干扰使当代文学在对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中出现了变异,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呈现出相排斥、相悖离的倾向,造成了两种潮流的冲突。虽然当时的文艺界存在着革命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提法,当时的文艺政策也大力提倡两者的结合,但是正如前文已经谈过的,革命现实主义是一种变异了的现实主义,革命浪漫主义是一种伪浪漫主义,两者的结合是违背艺术创作规律的。所以尽管如此,也掩盖不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互冲突的事实。两者的互补互融可以推进文学的发展,两者的矛盾冲突也可能会导致文学的倒退,中国文学面临着危机。
在这种情形下,《百合花》的出现无疑是一道曙光。它采用的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它的主题意蕴也符合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因此顺利地进入了主流文学的行列,但是它的深层内涵却焕发着浪漫主义特色,成功地完成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嫁接与融合。这部作品的意义在于打破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大中国最主要的文学思潮之间的僵局,实现了暂时的调和,也为后来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参考和借鉴,使中国文学重新焕发出一线生机。
参考文献:
[1]茅盾:《谈最近的短篇小说》,《人民文学》,1958(6)。
[2]李云霞:《宏大叙事下的抒情诗——从<百合花>看茹志鹃小说创作风格》,《河北建筑科技学院学报(社科版)》,2006(3)。
[3]周艳芬:《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发展概略》,《唐都学刊》,1993(1)。
田璐莎,女,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学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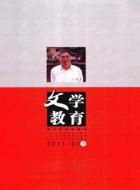
- 《三国演义》中的“军事地图”研究 / 高峰 曹俊生
- 莫泊桑小说中的隐藏艺术 / 吴雯雯
- 致力于近代诗人研究的学者丘铸昌 / 程祖灏
- 古今汉语里的“左右”释义 / 陈红芹
- 文学与时代 / 张笑天
- 留学生汉语因果类复句偏误分析 / 董福升
- 鲜花的力量 / 路文彬
- 论闲愁词的美学特征 / 袁和平 袁娇萍
- 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创作及理论研究现状管窥 / 滕永文
- 苏轼的政治人格研究 / 刘宇辉
- 古代诗词中清酒与浊酒的意象 / 张楠
- 英语文学教学中的跨文化意识培养 / 张欣
- 对古典诗词中桃杏寓意的探求 / 程仙梦
- 林非的散文观及其创作实践 / 罗建维
- 生态式教学模式下的文艺学课程考试 / 罗祖文
- 用激情锻造高效课堂 / 陈锁斌
- 如何让经典真正走进学生心间 / 张所帅
- 课堂教学最优化的有效途径 / 汪厚旬
- 优质语文课堂教学的途径与方法 / 崔燕霞
- 试论英语教学中语言意识的培养 / 宋艳
- 语文教学中如何巧用布白艺术 / 翁晔
- 大学英语分级教学和层次培养改革探讨 / 鲍娟
- 《百合花》:一部革命年代的爱情牧歌 / 田璐莎
- 从外语磨蚀看大学英语教与学 / 彭菲
- 提高语文课堂效率方法谈 / 俞彩娥
- 莫泊桑短篇小说《项链》重读 / 邱兴宇
- 古代诗歌形象鉴赏答题技巧 / 赵丹华 王东亮
- 迷失中的反抗与回归 / 孙淼
- 强化语文作业管理课题实验结论 / 张斌 郑玉琼
- 莫言《民间音乐》的奇与美 / 刘莉 郜国旗
- 语文课在中等卫生职业教育中的特殊地位 / 刘英
- 语文课堂中的幽默妙用 / 毕庆
- 杜甫诗作《燕子来舟中作》诗意解析 / 余建平 刘至彦
- 关于激发学生主体功能的若干认识 / 张丹华
- 浅谈结构主义与生成语言学 / 李凯
- 论《哈姆莱特》对鬼魂形象的刻画 / 崔永杰
- 语文课堂规律性探讨 / 陈水明
- 确立学生主体地位是教改的支点 / 陈兰珍
- 解读《边城》中的美与悲 / 曹瑞霞
- 学生自主预习能力的培养 / 崔秀竹
- 语文教学中如何激发学生情感 / 曹龙春
- 情真意切悼亡妇 / 杨卫东
- 在口语表达中找到自信 / 曾庆华
- 韩国语教学中关于韩国文化教育方案的建议 / 金美娜
- 《一个扑朔迷离的间谍故事》的主题解读 / 张文军
- 亲子阅读的现状与指导策略 / 申健强 王开芳
- 图画书阅读与儿童生命教育 / 王姗
- 解析《梦游天姥吟留别》的“梦” / 周国瑞
- 接受美学对语文阅读教学的启示 / 张民锋
- 语文教学中学生创新素质的培养 / 邸丽媛 李世袭
- 应用文写作应突出学生就业需求 / 高静 宋秀红
- “对话”阅读教学现状的思考和探究 / 盛严宏
- 改善中学生作文现状的可行性对策 / 董旭午
- 把课堂还给学生 / 许俊凌
- 试论应用写作课程研究性学习途径 / 伍桂蓉
- 诗歌朗读的教学艺术 / 袁欣伦
- 应用文教学实践性的几点探索 / 于兴菊
- 让学生插上想象的翅膀朗读 / 杨丹阳
- 初中生语文阅读能力培养之我见 / 徐华
- 怎样有效进行作文个性化教学 / 何莉
- 职校精品课程建设的实践和成效 / 吴仁玉
- 提高学生作文水平浅议 / 王占祥
- 浅谈职业学校学生社团的建设 / 吴文杰
- 基础学段名著阅读策略探微 / 王佩波
- 《六国论》教学设计 / 杨丽妃
- 中等职业学校英语课的有效教学 / 周永霞
- 说说情景交融 / 张清湘
- 浅谈中学生阅读能力的培养 / 郭俊娟
- 评邢桂轮先生的《回望编辑生涯》 / 张静
- 《诲人不倦》教学设计 / 贾桂强
- 让巧媳妇有米可炊 / 赵仁明
- 《听潮》教案设计 / 王凤云 孙云芳
- 我的三个作文观 / 肖信斌
- “流响”为何要“出疏桐” / 仲济民
- 略谈《外国小说欣赏》的教学 / 陆美娟
- 标点符号的修辞作用 / 李墨
- 话说“这个”“那个”之类 / 夏增田
- 如何减少习作中的错别字 / 李补月
- 与白岩松近在咫尺 / 陈筱
- 教育博客在教育中的作用 / 郭宏冰
- 在燃烧中永生 / 吴玉华
- 看物性判断对比和衬托 / 所福亮
- 梦回水高 / 何况
- 幼儿识字的几点经验 / 赵桂香
- 品味四季 / 陈芬
- 文学熏陶与班级管理 / 鲁世新 林日萍
- 浅谈习惯养成教育 / 柳明
- 师生关系的处理技巧 / 何和平
- 新课改下高中体育教学反思 / 池骋
- 如何提高学生学习严肃音乐的兴趣 / 张明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