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文学教育·中旬版 2010年第11期
ID: 153963
文学教育·中旬版 2010年第11期
ID: 153963
语言文化与殖民教育
◇ 王 涛
[摘要]英国在全球数百年的殖民扩张中,殖民手段逐渐成熟,隐蔽,从早期的武力征服到中后期的语言文化殖民,从肉体枷锁到精神桎梏。乔治·兰明的成长小说《在我皮肤的城堡中》为读者充分展现了宗主国英国的语言文化殖民在殖民地巴巴多斯的深远影响:语言文化殖民凸显帝国的强势文化,隐没少数民族的弱势文化,使殖民地人民失去自我,成为驯顺的他者。
[关键词]语言文化;殖民教育;《在我皮肤的城堡中》
一
众所周知,英国是历史上最早进行殖民扩张的国家之一,也是近代最大的殖民国家,它的殖民地曾遍布全球,从欧洲邻国到美洲,亚洲,非洲,以及南半球的澳洲。英国殖民者先利用武力征服,再运用其语言文化等进行奴化教育,妄图使殖民地人民成为驯服的大英帝国子民。直到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各殖民地先后脱离了英国的统治而获得独立,但其殖民教育的深远影响是持续的。《在我皮肤的城堡中》(下文简称《城堡》)的作者乔治·兰明以英国前殖民地西印度群岛上的巴巴多斯的一个小村庄为创作背景,书写出一段加勒比海地区被殖民的历史。
“规训”在殖民教育体系中固然能驯服肉体,然而过分的惩罚或武力压制势必激起被殖民者的强烈反抗。因此,大英帝国深知,欲彻底征服被殖民者,更行之有效且更隐蔽的手段是利用语言文化等手段对殖民地人民进行精神禁锢,从而达到长期统治的目的。
二
英语作为国际语言的霸权地位由来已久。自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来,英国在海外的殖民扩张就开始了。所到之处,为改变当地“野蛮落后”的状态,他们必然教会当地土著居民自己的语言文化,使其成为“文明”人。19世纪初,英国成为世界上最早的工业化国家,其经济发展速度突飞猛进,雄居世界首位。由于英国几个世纪的海外掠夺,贸易和殖民统治,使英语从英国走向世界。英国强大的经济政治实力为英语在殖民地乃至全球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亦是成就其霸权地位的根本原因。然而,英语在殖民地的主导地位直接导致了众多土著语言,奴隶语言的逐渐淡出甚至消亡。
随着殖民主义的扩张,对殖民地青少年进行殖民教育成为其中重要的内容,这不仅包括对宗主国历史,文化,政治的宣传,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对殖民地历史文化的压制。而这一过程中,语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关于语言,法侬认为,“一个人拥有了语言就拥有了这种语言所承载和表现的世界。语言同时表征着文化差异和力量的不均衡。控制语言将获得非凡的力量。尼古基指出,“子弹是征服肉体的武器,语言是征服精神的武器。语言携带着文化,尤其是文学语言,而文化则携带着我们赖以判断自己、判断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整个的价值体系。”
美洲黑人的民族语言的淡出有其历史根源。美洲早期的黑人从非洲贩运而来,他们的母文化是非洲文化,母语是非洲土语。他们远离故土,身处全新的异质文化环境,面对生存的压力,不得不接受异质文化的改变。在这个过程中异质(英语)文化必然经由语言的载体融入黑人文化之中。再者,根据当时殖民者制定的明文条款,奴隶之间只能用英语交流禁止用非洲土语,否则严惩不待。到殖民中期,为巩固帝国的殖民统治,英国政府在各个殖民地建设学校对奴隶后代进行英语语言历史文化教育。几代奴隶下来他们的非洲土语逐渐淡出消亡,取而代之的是文学当中常出现的黑人英语。加上英国殖民者对黑人奴役历史的蓄意掩盖,其结果是他们的非洲之根即黑人民族文化被斩断而处于无根状态。
三
克莱顿村男子学校的学生跟英国本土的孩子一样从英语字母学起。“a b ab catch a crab; g o go let it go” 是学前班所学的内容。高年级学生学会了唱圣歌, “噢,上帝是人千古保障,是人将来希望,是人居所、抵御风雨,是人永久家乡。”无论是岛屿上童年的生活,还是对上帝耶稣的歌颂,对大英帝国并无一害。帝国日庆祝会上,类似的“节目”年年上演。五月二十四日是伟大的维多利亚女王的诞辰。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教学督察员莅临检查,千余名学生在教师的指挥下排成整齐的九个方队,一一为女王真诚地祈祷,“上帝保佑女王,祝她万寿无疆,神佑女王…”。九个方队拥挤不堪,从操场上方的讲台上望去,好似一艘巨轮甲板上装箱的货物。当年非洲贩卖黑奴的历史场景在这里似乎又依稀重现。在这个盛大的日子里,校园四周都挂满了英国的三色国旗还有国王,王子的画像。低年级的孩子个个像刘姥姥进大观园,样样好奇;高年级的学生眼神里多了几分自豪,就像古罗马凯旋归来的战士,“红、白、蓝!多么耀眼的色彩啊!”这足以看出殖民地孩子在学校里被殖民异化的成长过程:从对宗主国文化的好奇探视到自豪接受的内化过程。检察员孜孜不倦的“教诲”,同样传达了忠君臣服的殖民意识形态,“亲爱的孩子们、老师们!我们再次相聚于此以追忆我们伟大的女王。她是你们的女王,也同样是我们的女王。我们都是大英帝国的臣民和缔造者。你们对帝国的忠诚可以从你们精彩的表演、严格的纪律和井然有序中看出来。你们必须牢记,大英帝国一直都致力于世界和平。切记,在这个世界的任何地方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或在这里,在巴巴多斯岛 ——帝国之骄子—— 身上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总站在和平这一边。你们和我们,我们和你们,站在一起,团结一致,必将走在上帝意愿的光环里”。如此振奋人心的演讲赢得了师生们雷鸣般的掌声。获此殊荣,最后督察员得出结论,“巴巴多斯是真正的小英格兰!”于是检阅在校长的命令下全校师生齐呼三声“万岁!万岁!万岁!”后圆满结束了。
在殖民过程中,语言是摧毁民族文化的强有力的武器,负载着殖民者文化价值观的语言通过渗透作用,可以从底部腐蚀并彻底摧毁被殖民者的文化。失去了民族文化载体的民族必然失语,从而导致这种文化在历史舞台上的隐没或淡出。尤其是书面语的运用,它通过不同的修辞、语法和文字,不仅从外观上改变一种文化,而且,当书面语被用于记载历史时,它所承载的内涵不可避免地蕴涵着这种语言本身所携带的价值观。遗憾的是,殖民地人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更不用说有意识地保护自己的民族语言和历史文化。庆祝会后,有个班在谈论国王的生活起居,谈论国王为何称之为陛下,谈论“影子国王”。有个班在唧唧喳喳谈论维多利亚女王。靠墙根的孩子无意中听到站在墙头上的老人说是维多利亚女王给了他们自由。一个小男孩重复着同样的话,“他们说是她给了我们自由,你,我,他,大家!他们就是这么说的。”“我也听到了!”另一个男孩附和道。“他们肯定曾被关在监牢里。是女王登基后大赦天下的。多好的女王啊。”老师说老人在胡说八道。殖民地新一代的教师接受的同样是殖民教育,他们对黑人奴役的历史或许一概不知或许作为帝国殖民统治的直接管理者,他们有意隐瞒黑人奴役的残酷历史。谈话继续进行下去,小男孩又听到一位老太太说他们曾经是奴隶。“奴隶?”,小男孩迷惑不解,而老师的解释毫无意义。“他还是不理解一个人怎能被另一个人买卖,牛马等牲口才被人买卖。老太太胡说八道。老师说,奴役是很久以前的事儿,跟老太太无关,跟巴巴多斯人无关,在小英格兰没有人曾是奴隶。小男孩决定放弃这个话题,却为老太太担心:她肯定不识字,谁告诉她说自己是奴隶的。他平生还是第一次听说‘奴隶’二字。简直是子虚乌有,无稽之谈!况且,没人跟他们讲过奴隶的历史,书上也没写;书上倒是讲了1066年英国伟大的黑斯廷斯战役还有征服者威廉的历史。那已是数百年前的事,奴隶制应该更加久远,久远到不值得作为历史教授传承”。最后孩子们的结论是:没有奴隶这回事。老太肯定是脑子进水了,要么就是做了个噩梦。作为非洲黑奴的后代不知自己民族的历史当然可悲,但他们却没有错。贩卖奴隶的历史不过两三百年,殖民者故意隐藏淡化“落后”民族的血腥历史,一是为了避免激起民愤和反抗,二是因为殖民者认为他们的文化有其不可比拟的优越性,而西方以外的“他者”的文化都是低劣、愚昧、落后的,理所当然应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同时将自己的语言、文化以各种形式灌输、渗透给“落后”民族和国家,并不失时机地将自己的文化意识强加于其他民族文化之上。
四
由此可见,英国殖民者的语言殖民教育是成功的。在殖民者建设的学校里,在督察员,校长及众多教师的“教育”下,奴隶的后代被成功地异化为大英帝国的“他者”。他们心甘情愿地认英格兰为“母亲”,并为有这样一位伟大的母亲而感到自豪。即使偶尔有类似于老太这样“宣扬黑人奴役史”的情况出现,也会被知识权威——教师这样的殖民走狗以各种方式或理由搪塞过去,最后不了了之。再者,奴隶一代/二代大多从非洲贩运至美洲。作为非洲原著民,他们没有书面语言,民族历史文化靠口述代代传承下去,在充满英语语境的世界里,只会说蹩脚的黑人英语,不会识文断字、书写历史,要将其民族历史文化传承下去只能是痴人说梦。如果没有新一代知识分子的觉醒,将民族记忆用英语书写出来,那么黑人奴役的历史必将石沉大海。
语言文化的殖民过程就是对被殖民者进行精神洗脑的过程,从而使其放弃自己的生存方式并否定族群的本质特征,最终导致“属下”对自身的否定,在扭曲的文化氛围中使黑人完成心理、精神和现实世界的被殖民过程。英国在殖民地的奴化教育过程中,语言文化功不可没。它们的殖民异化力量是规训惩罚等暴力手段所不能及的。特别是巴巴多斯等殖民地相继独立后进入后殖民阶段,英语语言文化的影响依然存在。独立后的巴巴多斯效仿美国由封建殖民社会进入了资本主义剥削社会,但殖民掠夺的本质却有过之而无不及:克莱顿村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家园,变成了一无所有的“自由人”。新的统治者由世袭克莱顿家族变成了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Mr. Slime一伙;主人公G昔日的玩伴成了新制度下的“国家机器”—— 警察。而以村里族老Pa为首的承载着民族文化记忆的祖辈被一一“请”进了养老院:一个收容“社会垃圾”且离死亡不远的地方。面对巴巴多斯发生的巨大改变,面对来自民族、语言、文化的压力,身为知识分子的主人公G终于下决心,冲破这一张张无形之网,到欧洲大陆去铸造出他的民族尚未被创造出来的良知,以沉默、流亡和机智为武器来保卫自己,寻求精神上的自由和解放。作者兰明就是在这种流放过程中用殖民语言 ——英语—— 书写了自己的成长过程、本民族的历史文化,解构了殖民的心灵。
参考文献:
[1] Gendzier, Irene L. Fanon: A Critical Study [M].London: Wildwood House, 1973:47.
[2] Ngugi Wa Thiong’O. Homecoming: Towards a National Culture [M].London: Heinemann, 1972:282-290.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社基金项目成果之一,项目编号:2010SJB750013
作者简介:王涛(1977—),女,重庆人,硕士,讲师,主要从事英语教学及英美文学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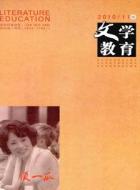
- 诚实的写作都是霸道的 / 姜广平
- 庄子内篇中的“则” / 赖明辉
- 《荆棘鸟》——爱与命运的传奇 / 张学梅
- 《长恨歌》主题解读 / 沈玉云
- 谁杀死了耶洗别 / 付春光
- “以诗证史”的蔡琰《悲愤诗》 / 王 月
- 中西方文化中的情与利 / 周 鑫
- 浅论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家园意识 / 张 歌 王朝辉
- 评析谢尔顿的惊险小说《你怕黑吗?》 / 张伟铭
- 弗吉尼亚.伍尔夫作品研究述评 / 陈 健
- 论贾宝玉形象的新时代特征 / 常洪妍
- 读罗纳德.德沃金的《认真对待权利》 / 彭 荔 尹殿元
- 第二课堂活动调查 / 韩 笑 邰运恒 华海文 石亚军
- 论夏洛蒂.卢卡斯婚姻选择的合理性 / 牛宝华
- 唐宋词文本解读三则 / 刘 威
- 高师院校大学生学习心理调查和分析 / 杨亚杰 王 瑾
- 《想北平》教案 / 涂盈盈 裔胜东
- 王维诗歌浅析 / 谭书琼
- 浅析丁玲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 况 军
- 从运河文化到淮安精神 / 黄银花 赵仕奇
- 浅谈《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道德冲突 / 谭艳萍
- 路遥小说创作中的乡土守望 / 石晓磊
- 对20世纪女性文学的审美流向分析 / 高 鹏
- 浅析复合图书馆的参考咨询服务 / 魏 亨
- 从《一间自己的房间》到《三个女人》 / 朱赛方
- 谈谈美国文化中的希伯来因素 / 邓 洁
- 犹太——基督教传统对美国和以色列关系的影响 / 唐 丽
- 赣州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调查研究 / 黄兴裕 秀华
- 对增强体育类考生成绩发挥的对策思考 / 李志华
- 古今“合同”知多少 / 张石砚
- 良好班集体的创建 / 李亚玲
- 五年一贯制班级管理初探 / 胡 梅
- 合作办学院校学生思想状况分析 / 王 伟
- 论新型教师的素质 / 彭 江
- 从人物关系论郝思嘉的传统意识 / 周亚明
- 基于学科建设的高校图书馆知识服务的研究 / 王宏洁
- 浅谈沟通技巧 / 王 平
- 上网对高职生学习成绩影响的调查 / 孙丽文 刘 乐
- 合同中长句的解读和翻译技巧初探 / 吴 娜 廖昌盛
- 信息的含义及其时代意义 / 李正海
- 探析档案人员应具备的素质 / 张素英
- 不可轻忽的关联词语 / 梁红春
- 建国以来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政策回顾与简评 / 李爱莲
- 用科学的人生观指引人生 / 刘 敏
- 网络时代的学生道德新问题 / 韩国栋
- 转化英语学困生的方法 / 蒋 丽
- 论思维差异与英语翻译 / 黄又竹
- 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与解决对策 / 姜 霞
- 如何帮助后进生坚持到底 / 李代勇
- 峨眉方言中“的”字考 / 杨里娟
- 论体悟的心理学研究方法 / 程威巍 景卫丽
- 《乌鸦》一诗的音韵之美 / 张雪峰
- 浅谈教学中网络资源的应用 / 金星晖
- 如何在阅读教学中激发学习动机 / 孟青兰 方 璐 钟永发
- 教学与实践结合的重要性 / 赫 瑾
- 摄影术发明以后绘画对摄影的反应 / 胡晓璇
- 篇章听写法在教学中的运用 / 付伶俐 宗燕
- 《乌鸦》一诗的音韵之美 / 张雪峰
- 学生口语焦虑感现状与对策 / 王壹清
- 《黄河大合唱》对《黄河钢琴协奏曲》的影响 / 魏 敏
- 摄影术发明以后绘画对摄影的反应 / 胡晓璇
- 高职商务日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之探讨 / 郑 佳
- 学生口语焦虑感现状与对策 / 王壹清
- 《黄河大合唱》对《黄河钢琴协奏曲》的影响 / 魏 敏
- 高职商务日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之探讨 / 郑 佳
- 浅析情感因素对“90后”大学生外语教学启示 / 于 艳
- 浅论丰子恺艺术作品中的文画互读 / 廖静爱
- 浅析情感因素对“90后”大学生外语教学启示 / 于 艳
- 音乐教育与素质教育 / 梅 芳
- 论图形创意的形式美 / 岳花娟
- 谈广告中的词汇运用 / 张素芳
- 论思维差异与英语翻译 / 黄又竹
- 浅析浪漫主义时期钢琴艺术的美学特征 / 刘 水
- 表演艺术的 “雅”与“俗” / 万建新
- 峨眉方言中“的”字考 / 杨里娟
- 谈谈朗读在中学阅读教学中的作用 / 何美秀
- 中西戏剧差异性原因探究 / 易 丹
- 让学生在复述中提升语文能力 / 宋碧波
- 阅读文学作品要学会让体验增值 / 袁 迎
- 中学语文阅读策略 / 周玉洁
- 《英文影视欣赏》在高职教学中的作用 / 李云辉 王 平
- 浅谈初中考场作文的几个亮点 / 温宏庆
- 从《维摩经变》看佛教对唐朝敦煌人物画的影响 / 顾月月
- 以新促趣 以趣促新 / 欧阳齐
- 皮格马利翁效应与语文教学 / 曾 亮
- 有效引领学生写作精彩结尾 / 单卿之
- 语文合作学习低效现象剖析及对策 / 丁勤枢
- 高校文学教学新模式的构建 / 曾静蓉
- 语文课堂教学有效预设与生成初探 / 金图标
- 语文阅读教学的朗读技巧 / 胡琍玲
- 从高职语文教学看学生人文素质的养成 / 吕 冬
- 布鲁纳结构课程观对语文学科课程建设的启示 / 付 云 王树志
- 中学作文教学的有效途径分析 / 邓 爱
- 古诗词教学中的审美教育 / 李宜兰
- 语文个性化阅读教学的实践研究 / 刘艺杰
- 语言文化与殖民教育 / 王 涛
- 人文素质教育和人文能力培养 / 陈 芳
- 提高作文教学质量初探 / 洪燕兰
- 关于深化高职院校人文素质教育的探讨 / 韩鸿雁
- 例谈语文教学中的阅读设计 / 陈 宾
- 德育教学应重视家庭德育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 / 董晓俐
- 浅谈作文创新策略 / 司振昊
- 大学双语课自主课堂探略 / 田志东
- 新形势下加强艺术类大学生创业教育的思考 / 史 璇 董桂刚
- 在语文教学中渗透闲暇教育 / 张 慧
- 农村教学的几点探究 / 郎法玉
- 新课改背景下的政治课教学探讨 / 徐 明
- 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有效途径研究 / 梁文颖
- “激励性教学法”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 / 陈好连
- 试论《英国文学》课程教学模式和实践改革的思考 / 李 静
- 职业学校新课改形势下教学的思考 / 林 冬
- 加强实验室建设 强化实验课教学 / 雷小军
- 阅读:学生成长的舞台 / 汪加林
- 谈谈课堂提问的艺术 / 秦 慧
- 如何激发学生参与教学活动的兴趣 / 陈 平
- 阅读课整体结构的建构视野 / 傅明流
- 北京胡同 / 柳丽莎
- 简析小学教育专业学生的职业规划教育现状与对策 / 朱晓娜
- 二程“教化”思想与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观 / 丁 静 赵 伟
- 当代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 / 王 薇
- 语言艺术在教学中的应用 / 孔 龙
- 应用型高校实践教学模式研究 / 李春玲
- 班主任工作中的几点体会 / 张俊艳
- 浅议高校篮球队训练的几点方法 / 李 斌
- 高职体育教育发展的探讨 / 晏仲谋 贺红兵
- 浅析初中思品课中创新型情景的导入 / 刘华伟
- 民办高校学困生学习困难原因及教育策略 / 徐慧茗 华玉坤
- 《唯一的听众》教学设计 / 邵振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