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文学教育·中旬版 2010年第11期
ID: 153868
文学教育·中旬版 2010年第11期
ID: 153868
《长恨歌》主题解读
◇ 沈玉云
[摘要]《长恨歌》主题一直争议颇多。本文就诗人的诗歌创作主张、政治倾向及所处环境,并诗歌内容本身进行阐述,提出《长恨歌》的主题应为“为君”诊病之作的观点。
[关键词]长恨歌;主题;“为君”诊病
白居易是步盛唐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后尘的中唐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那自称“感伤诗”的叙事诗《长恨歌》的主题一直有很多争议。大体上有这样的几个观点:“讽喻说”、“爱情说”、“讽喻爱情兼有说”。在笔者看来,《长恨歌》的主题当为“为君”诊病之作。
一、考察诗人的诗歌创作主张、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及政治倾向,并同时考察同时期的其他作品,有利于我们解读作品的主题
白居易(772-846)一生经历了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八个皇帝统治的七十四年时光。史家历来将白居易的生平思想与创作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以四十岁贬江州司马为界线。前期是“兼济天下”的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的时期。
宪宗元和元年,白居易35岁,为了准备参加“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的考试,写了《策林》七十五篇。他站在中下层地主阶级立场上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提出一系列进步的治理方案。主张节用爱民,轻赋敛,偃兵革,劝农桑,利万人。在第六十九《采诗》一篇里,诗人说“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形于歌诗矣。”意思是说诗歌的基础是“事”,是客观的社会现实,诗歌创作应该反映社会现实。说得具体一点,有两点值得注意,用诗人的著名语句来表达:一、“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二、“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这是指导诗人进行政治活动和诗歌创作的纲领。这年四月,白居易参加了考试,因为对策语直,被列入四等,授予周至县尉。在周至县,诗人创作了《长恨歌》。
那么,白居易写作《长恨歌》的特定历史时期最大的政治危机是什么呢?诗人通过对历史和现实的观察和思考,认为藩镇割据、拥兵自重,时刻觊觎着中央政权,随时都可能酿成天下大乱,乃是最大的忧患。而这最大的忧患又是由于政治腐败、宦官专权、朝纲废弛激变出来的。
“为君、为民、为物、为事而作”的诗人敏锐地抓到了这个总症结。我们可以通过考察诗人的同期作品《观刈麦》来领略诗人创作《长恨歌》的良苦用心。
《观刈麦》叙述了受横征暴敛之苦的人民的生活:农民在酷暑中劳作的艰辛:“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横征暴敛下的辛酸生活:“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及作者对自我的解剖:“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焦灼之心溢于言表深刻。同时期的还有“执政柄者扼腕”、“握军要者切齿”的《宿紫阁村》。
元和三年五月,做了左拾遗的诗人认真地履行谏官职责,“食不知味,寝不遑安”、“有阙必规,有违必谏”。有一次,诗人当面指责皇帝,皇帝脸色都变了,退朝后跟宰相李绛说:“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实难奈!”但诗人毫不畏惧,在《李都尉与剑》中写道:“愿快直士心,将断佞臣头。”
由此可见,《长恨歌》的主题绝不是什么“爱情论”、“兼有论”。
二、从诗歌内容及人物形象刻画上,分析《长恨歌》的主题
《长恨歌》中的“汉皇”形象是以历史上唐玄宗为原型的。诗人旨在“垂于将来者也”,因此,对唐玄宗前期的功绩作了彻底的舍弃。开卷的“汉皇重色思倾国”,既揭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又是全篇的纲领。“重色”二字,是艺术形象唐玄宗的性格特征,但“御宇多年求不得”。诗人在故事的开始,就巧妙地点了“恨”。“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则含蓄而又形象地刻画了杨玉环恃色而骄、待价而沽的性格特征,及李杨愿望的实现。“日高起”、“不早朝”、“夜专夜”、“看不足”,可以说,这是诗人满怀一腔义愤,用犀利而又沉重的语言揭露了唐玄宗纵欲行乐、终日沉湎于歌舞酒色是酿成“安史之乱”的重要根源。
诗的第二部分,诗人则一反第一部分的旨在揭示“长恨”的根本原因的讽刺笔调,转为深入挖掘因唐玄宗荒淫误国而造成的深层次苦难的冷静叙述。这一部分既可看作唐玄宗自述内心之“恨”,也可看作《长恨歌》的“长恨”发展之第一高潮。逃难奔蜀如丧家之犬,乱平回京被束之高阁,曾有的权势,曾经的荒淫,皆化为乌有。
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诗的结尾,诗人采用完全不同于一、二部分的忠于史实的艺术创造,而是别开生面,运用浪漫主义的手法创设了一个动人的仙境。从诗人着意刻画的这个死去的杨玉环对还活着的唐玄宗的“无限相思”而又永无会期的巧妙的艺术构思来看,这无疑是第二部分唐玄宗“长恨”的继续与深入。至此,“长恨”达到第二高潮,也是全篇的高潮。诗人以超然若逝的清丽女子形象呼应开头部分的以色邀宠的宠妃形象,则深刻地展示了“长恨”的结局,展示了李杨腐败与二者悲剧恶果的因果关系。
可见,“为君”诊病这根红线一直贯穿全诗。
三、“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
还在安史之乱发生时,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就写了《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首》一文,字字血、声声泪地斥责了在华清宫避寒,肆无忌惮地挥霍着老百姓的血汗,过着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腐败生活的唐玄宗。
白居易撰写《长恨歌》时,安史之乱早已过去了半个世纪,比之杜甫,诗人也许少了一点事关切身利害的沉痛感,但一定多了不少历史教训的清醒感。因此,尽管诗人把《长恨歌》定为“感伤诗”,我们也不应当把《长恨歌》与其他感伤诗相提并论。我们不能设想:诗人在疾风暴雨似地攻击统治阶级横征暴敛,攻击豪门贵族贪赃枉法、骄奢淫逸,攻击最高当局的穷兵黩武,满腔热情地为处在水深火热中的劳动人民呐喊,愤怒谴责封建皇帝的残酷与伪善的同时,会有一篇什么歌颂皇帝贵妃的长诗来否定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况且,白居易是杜甫的有意识的继承者,也是杜甫之后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继承并发展了《诗经》和汉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沿着杜甫所开辟的道路,进一步从文学理论上和创作上掀起了一个波澜壮阔的现实主义诗歌的高潮。
诗人也曾一再重申:“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可见,“风情“者,绝非风流多情,而是历代对《诗经》中“国风”风人之情、美刺之旨等作用的解释;“正声”则是以《诗经》中雅诗来类比,说《秦中吟》是王政兴废得失的镜子。
鲁迅曾经告诫人们:“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本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于说梦的。”
因此,《长恨歌》当为“为君”诊病之作。
参考文献:
[1]张忠宇.《长恨歌》主体研究综论.文学遗产,2005(3)
[2]萧涤非等.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
[3]鲁迅.《且介亭杂文集》上海,三闲书屋,1937.
作者简介:沈玉云(1968—),女,江苏淮安人,江苏省淮安市建筑工程学校教师,研究方向:语文教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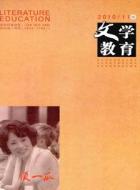
- 诚实的写作都是霸道的 / 姜广平
- 庄子内篇中的“则” / 赖明辉
- 《荆棘鸟》——爱与命运的传奇 / 张学梅
- 《长恨歌》主题解读 / 沈玉云
- 谁杀死了耶洗别 / 付春光
- “以诗证史”的蔡琰《悲愤诗》 / 王 月
- 中西方文化中的情与利 / 周 鑫
- 浅论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家园意识 / 张 歌 王朝辉
- 评析谢尔顿的惊险小说《你怕黑吗?》 / 张伟铭
- 弗吉尼亚.伍尔夫作品研究述评 / 陈 健
- 论贾宝玉形象的新时代特征 / 常洪妍
- 读罗纳德.德沃金的《认真对待权利》 / 彭 荔 尹殿元
- 第二课堂活动调查 / 韩 笑 邰运恒 华海文 石亚军
- 论夏洛蒂.卢卡斯婚姻选择的合理性 / 牛宝华
- 唐宋词文本解读三则 / 刘 威
- 高师院校大学生学习心理调查和分析 / 杨亚杰 王 瑾
- 《想北平》教案 / 涂盈盈 裔胜东
- 王维诗歌浅析 / 谭书琼
- 浅析丁玲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 况 军
- 从运河文化到淮安精神 / 黄银花 赵仕奇
- 浅谈《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道德冲突 / 谭艳萍
- 路遥小说创作中的乡土守望 / 石晓磊
- 对20世纪女性文学的审美流向分析 / 高 鹏
- 浅析复合图书馆的参考咨询服务 / 魏 亨
- 从《一间自己的房间》到《三个女人》 / 朱赛方
- 谈谈美国文化中的希伯来因素 / 邓 洁
- 犹太——基督教传统对美国和以色列关系的影响 / 唐 丽
- 赣州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调查研究 / 黄兴裕 秀华
- 对增强体育类考生成绩发挥的对策思考 / 李志华
- 古今“合同”知多少 / 张石砚
- 良好班集体的创建 / 李亚玲
- 五年一贯制班级管理初探 / 胡 梅
- 合作办学院校学生思想状况分析 / 王 伟
- 论新型教师的素质 / 彭 江
- 从人物关系论郝思嘉的传统意识 / 周亚明
- 基于学科建设的高校图书馆知识服务的研究 / 王宏洁
- 浅谈沟通技巧 / 王 平
- 上网对高职生学习成绩影响的调查 / 孙丽文 刘 乐
- 合同中长句的解读和翻译技巧初探 / 吴 娜 廖昌盛
- 信息的含义及其时代意义 / 李正海
- 探析档案人员应具备的素质 / 张素英
- 不可轻忽的关联词语 / 梁红春
- 建国以来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政策回顾与简评 / 李爱莲
- 用科学的人生观指引人生 / 刘 敏
- 网络时代的学生道德新问题 / 韩国栋
- 转化英语学困生的方法 / 蒋 丽
- 论思维差异与英语翻译 / 黄又竹
- 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与解决对策 / 姜 霞
- 如何帮助后进生坚持到底 / 李代勇
- 峨眉方言中“的”字考 / 杨里娟
- 论体悟的心理学研究方法 / 程威巍 景卫丽
- 《乌鸦》一诗的音韵之美 / 张雪峰
- 浅谈教学中网络资源的应用 / 金星晖
- 如何在阅读教学中激发学习动机 / 孟青兰 方 璐 钟永发
- 教学与实践结合的重要性 / 赫 瑾
- 摄影术发明以后绘画对摄影的反应 / 胡晓璇
- 篇章听写法在教学中的运用 / 付伶俐 宗燕
- 《乌鸦》一诗的音韵之美 / 张雪峰
- 学生口语焦虑感现状与对策 / 王壹清
- 《黄河大合唱》对《黄河钢琴协奏曲》的影响 / 魏 敏
- 摄影术发明以后绘画对摄影的反应 / 胡晓璇
- 高职商务日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之探讨 / 郑 佳
- 学生口语焦虑感现状与对策 / 王壹清
- 《黄河大合唱》对《黄河钢琴协奏曲》的影响 / 魏 敏
- 高职商务日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之探讨 / 郑 佳
- 浅析情感因素对“90后”大学生外语教学启示 / 于 艳
- 浅论丰子恺艺术作品中的文画互读 / 廖静爱
- 浅析情感因素对“90后”大学生外语教学启示 / 于 艳
- 音乐教育与素质教育 / 梅 芳
- 论图形创意的形式美 / 岳花娟
- 谈广告中的词汇运用 / 张素芳
- 论思维差异与英语翻译 / 黄又竹
- 浅析浪漫主义时期钢琴艺术的美学特征 / 刘 水
- 表演艺术的 “雅”与“俗” / 万建新
- 峨眉方言中“的”字考 / 杨里娟
- 谈谈朗读在中学阅读教学中的作用 / 何美秀
- 中西戏剧差异性原因探究 / 易 丹
- 让学生在复述中提升语文能力 / 宋碧波
- 阅读文学作品要学会让体验增值 / 袁 迎
- 中学语文阅读策略 / 周玉洁
- 《英文影视欣赏》在高职教学中的作用 / 李云辉 王 平
- 浅谈初中考场作文的几个亮点 / 温宏庆
- 从《维摩经变》看佛教对唐朝敦煌人物画的影响 / 顾月月
- 以新促趣 以趣促新 / 欧阳齐
- 皮格马利翁效应与语文教学 / 曾 亮
- 有效引领学生写作精彩结尾 / 单卿之
- 语文合作学习低效现象剖析及对策 / 丁勤枢
- 高校文学教学新模式的构建 / 曾静蓉
- 语文课堂教学有效预设与生成初探 / 金图标
- 语文阅读教学的朗读技巧 / 胡琍玲
- 从高职语文教学看学生人文素质的养成 / 吕 冬
- 布鲁纳结构课程观对语文学科课程建设的启示 / 付 云 王树志
- 中学作文教学的有效途径分析 / 邓 爱
- 古诗词教学中的审美教育 / 李宜兰
- 语文个性化阅读教学的实践研究 / 刘艺杰
- 语言文化与殖民教育 / 王 涛
- 人文素质教育和人文能力培养 / 陈 芳
- 提高作文教学质量初探 / 洪燕兰
- 关于深化高职院校人文素质教育的探讨 / 韩鸿雁
- 例谈语文教学中的阅读设计 / 陈 宾
- 德育教学应重视家庭德育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 / 董晓俐
- 浅谈作文创新策略 / 司振昊
- 大学双语课自主课堂探略 / 田志东
- 新形势下加强艺术类大学生创业教育的思考 / 史 璇 董桂刚
- 在语文教学中渗透闲暇教育 / 张 慧
- 农村教学的几点探究 / 郎法玉
- 新课改背景下的政治课教学探讨 / 徐 明
- 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有效途径研究 / 梁文颖
- “激励性教学法”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 / 陈好连
- 试论《英国文学》课程教学模式和实践改革的思考 / 李 静
- 职业学校新课改形势下教学的思考 / 林 冬
- 加强实验室建设 强化实验课教学 / 雷小军
- 阅读:学生成长的舞台 / 汪加林
- 谈谈课堂提问的艺术 / 秦 慧
- 如何激发学生参与教学活动的兴趣 / 陈 平
- 阅读课整体结构的建构视野 / 傅明流
- 北京胡同 / 柳丽莎
- 简析小学教育专业学生的职业规划教育现状与对策 / 朱晓娜
- 二程“教化”思想与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观 / 丁 静 赵 伟
- 当代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 / 王 薇
- 语言艺术在教学中的应用 / 孔 龙
- 应用型高校实践教学模式研究 / 李春玲
- 班主任工作中的几点体会 / 张俊艳
- 浅议高校篮球队训练的几点方法 / 李 斌
- 高职体育教育发展的探讨 / 晏仲谋 贺红兵
- 浅析初中思品课中创新型情景的导入 / 刘华伟
- 民办高校学困生学习困难原因及教育策略 / 徐慧茗 华玉坤
- 《唯一的听众》教学设计 / 邵振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