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11年第8期
ID: 156040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11年第8期
ID: 156040
诗歌《错误》的再审读
◇ 颜锟
《错误》是台湾诗人郑愁予的一首轻巧清隽的诗,被誉为“现代抒情诗的绝唱”。第一次朗读这首诗时,我就被其清新轻灵的语言所吸引住了。朗诵之后,我的头脑突然产生了两个疑问:本诗的第一句“我打江南走过”中的“打”字是不是动词?如果不是动词,那么该怎样理解“打”的含义?
于是,我带着这个疑问翻阅了《现代汉语字典》(第5版,商务印书馆2005年7月北京第338次印刷),了解到了“打”字的用法。“打”字除了作为动词和量词之外,还可以作介词,其词义是“从”,读音是“dǎ”,例如“打这儿往西,再走三里地就到了”。为了更详细地了解“打”作为介词时的用法,我又查阅《汉语大字典》(《汉语大字典》P767,湖北省新华印刷厂,1995年5月第2次印刷)有关“打”作为介词的用法。“打”:介词,相当于“自”“从”,用法①表示处所或方向。例如宝玉道:“才打学房里回来,吃了要往学房里去,先见老太太。”(《红楼梦》第九十一回)②表示时间。例如:打明天开始试车。
结合上面两本字典的解释,我们可以看出“打”在诗句中显然不是动词而是介词,“我打江南走过”就是“我从江南走过”。可是“打”字和“从”字都是介词,它们在用法上有什么差异呢?带着这个新的疑问,我再次翻阅了《现代汉语字典》去了解“从”字的用法。“从”字作为介词,读音是“cóng”,其词义有三种:①“起于”,“从-----”表示“拿----做起点”,例如“从上海到北京”;②表示“经过,用在表示处所的词语前面”,例如“从他们前面经过”;③表示“根据”,例如“从笔迹看,这字像孩子写的”。(《现代汉语字典》第5版,商务印书馆2005年7月北京第338次印刷)
在比较了“打”字和“从”字作为介词时的用法后,我还是不能解答心中的疑惑。在百思不解时,我上网查阅了《辞海》有关“打”字和“从”字的有关用法。“打”〈介〉①[口]∶从——带有北方方言色彩,普通话里一般用“从”,在单音方位词前只能用“从”。如:从南到北,从早到晚,从里到②表示处所、时间、范围的起点。如:打这儿往北去;打城里回来;打明儿开始③表示经过的路线、场所。如:打陆路走,三天可以到。“从”〈介〉①自,由——用作虚词,表示起点。“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贺知章《回乡偶书》②从自(自从);从马上猛跌下来。
从《辞海》上的解释,“打”作介词时和“从”用法的差异是它们使用的语境不同。此时,我们如果进一步分析作者的籍贯“河北”和出生地“山东”这两个地名,就可以找到问题的答案了。打”作为介词,用于口语且带有北方方言色彩,而河北省和山东省的方言都是属于北方方言中的华北官话。由于方言是特定地域的历史文化的符号,反映着本地域的自然景观与人文特色、民俗与风情,所以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自然而然地使用一些散发着泥土气息的方言词。从这点来看,祖籍河北而生于山东的诗人郑愁予在创作《错误》这首诗时,使用带有北方色彩的“打”字而没有使用“从”字是在情理之中的了。
最后综合《现代汉语字典》、《汉语大字典》和《辞海》对“打”字与“从”字的解释,我们可以理清它们作为介词时在用法上的差异:“打”字作为介词,可以表示经过的路线、场所,而“从”字则表示经过的起点。因此“我打江南走过”是说“江南”只是诗人漫漫旅途中的一个中点,而非起点或终点;“我从江南走过”则意味着“江南”是诗人漫漫旅途的起点,而非是中点或终点。从《错误》这首诗的结尾“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来分析,诗人用“打”字比用“从”字更容易表达诗歌的主题。所以美丽“错误”,非“打”不可。
从上面对“打”和“从”作介词时用法的差异,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美丽“错误”,非“打”不可。
颜锟,教师,现居湖北云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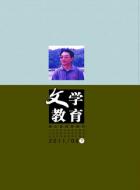
- 莺莺塔 / 马温
- 马一浮的“笑”和“哭” / 散木
- 论杜牧诗歌的怀古意识 / 盛莉
- 露西•斯诺 / 杨红霞
- 教学与行政双肩挑的殷杰教授 / 伍兵
- 《城邦暴力团》结构分析 / 孟令君
- 福柯理论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影响 / 景欣悦
- 论刘震云小说生命的异化状态 / 郭颖
- 语文课堂导语设计与运用 / 谢瑞芬
- 卡森•麦卡勒斯小说研究 / 曲晓晨
- 浅析高校英语教师的教学效能感 / 李媛媛
- 《呼啸山庄》和“三恋”的精神共通 / 何羚杰
- 《宗教与文学》中佛教与文学关系研究 / 李耀威
- 诗词中的双关举隅 / 丹慧敏
- 高职普通话课应加强听话训练 / 邓双荣
- 感悟古人的“闲”情 / 吴红
- 评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论》 / 石雯
- 如何进行英语语音教学 / 李颖
- 关于概念隐喻工作机制立体空间模型假设 / 陈玉梅
- 有效语言实践情境教学的特征与方法 / 周淑平
- 有对自动词与有对他动词可能态的用法差异 / 邱晓玫
- 略论设计的知识产权风险 / 邓俊
- 高中语文教学中长文短教的艺术处理 / 韦香琼
- 如何开发学生自主创新的潜能 / 张字洪 蔡由利
- 语文教学中如何预设有效问题 / 仲桂云
- 高校英语教师学科教学知识分析 / 李静
- 让语文课堂充满阳光 / 刘晓娟
- 高中英语阅读课文中的词汇教学方法 / 关颖
- 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词汇教学 / 俞静
- 怎样培养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 / 柴梦华
- “读者类型说”与语文教师的读者地位 / 罗雄
- 中学生逻辑思维训练实践探究 / 黄容春
- 课程资源与语文教学三维目标 / 姚红敏
- 学生语文自学能力的培养 / 骈玲玲
- 优化写作教学方法探析 / 卫雪利
- 商务英语翻译课程的学习要诀 / 李锦琴
- 唐代进士科在写作领域里的现代效应 / 杨扬
- 语文教学中的问题意识 / 朱易灵
- 中职旅游专业语文教学中的专业渗透 / 王菊珍
- 高中作文高效教学做法初探 / 孟庆焕
- 应把作文教学纳入普通语文课堂 / 吉伟
- 对潜能生的备考策略 / 黄红英
- 语言亮丽文章秀 / 赵红英
- 高职高专应用文写作类教材编写体例探析 / 李雯
- 考场作文写作技法探讨 / 褚福民
- 运用多媒体突破教学中的重难点 / 孟娜
- 课外阅读与写作的关联性 / 申翠英
- 高三后期作文复习的主题设想 / 李保国
- 新课改须落实学生学习习惯的转变 / 宋文娟
- 戏剧表演如何用于大学英语口语课 / 黄燕红
- 语文课怎样与写作进行有机结合 / 刘磊
- 走向作文教学的自由王国 / 颜更祥
- 《喧哗与骚动》里的人物分析 / 覃礼兰
- 《氓》中女主人公的婚姻观 / 周平平
- 新课改下的作文教学 / 程瑞莲
- 《淮上与友人别》赏析 / 严吉林
- 从叙述视角看《十九号房》的主题反讽 / 李逸云
- 如何巧拟题写好开头 / 王维侠
- 《伊豆的舞女》的虚无之美 / 王月琴
- 夏洛克对安东尼奥的恨之原因 / 贾冰
- 以生活为源积累作文素材 / 王新云
- 《蝇王》中的伦理困惑 / 于振飞
- 妙用修辞巧增色 / 池志波
- 《桃花扇》的语言艺术 / 田斌
- 名著推广阅读的有效方法 / 乔伟民
- 再议扬州方言数量短语后的助词“头” / 尹燕飞
- 民族院校《大学语文》教育的困境与对策 / 韩晓清
- 语文课堂教学中的虚假现象 / 薄春节
- 李白《将进酒》课堂教学实录 / 赵华
- 初中语文教学点滴谈 / 闫鸣
- 语文教学也应重视心理教育 / 胡杰
- 状位形容词的语义指向探析 / 陈伟
- 谈学前儿童的读经问题 / 刘洁
- 再析“谁之永号”的“之”“永” / 贺新梓
- 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几种途径 / 苏楠
- 对新时期班级管理工作的思考 / 黄苏锋
- 《虞美人》研读 / 李化
- 对学生自主课堂教学模式的思考 / 邓玉霞
- 中考半命题作文复习谈 / 李华明
- 让古典诗歌的意象鲜活起来 / 张丽
- 借鉴传统诵读法开展经典阅读 / 梁志斌
- 识字教学方法谈 / 苗冬梅
- 关于《故乡》的教学实践与尝试 / 周银玲
- 阅读教学中提高迁移能力的途径 / 曾仲权
- 诗歌《错误》的再审读 / 颜锟
- 浅谈班级凝聚力的形成 / 于勇
- 谈声乐有效教学 / 张萍
- 阅读教学中的情感交流 / 陈美嫦
- 对学生德育教育问题的思考 / 何瑞龙
- 高中阅读课语言积累途径研究 / 杨永辉
- 提高校长教学领导力的策略与方法 / 俞静
- 教学副校长领导力在实践中的提升 / 罗慧芳
- 高中语文课堂中的朗读教学 / 刘洪海
- 最是书香能致远 / 孙玉梅
- 如何提高学生现代文阅读的能力 / 程静
- 明明 / 王丽然
- 阅读 / 叶汉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