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11年第8期
ID: 156028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11年第8期
ID: 156028
谈学前儿童的读经问题
◇ 刘洁
内容摘要:当下儿童读经热潮席卷全国上下,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倡导儿童读经者普遍认为儿童读经利于民族文化的传承,益于儿童人格的养成,是一种能够开发儿童智力的较佳的早期教育。并且王财贵等人认为儿童阶段所读的经典将会自发的对其一生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对于儿童读经的文化传承及人格影响的意义笔者并不轻易否定,但对于经典的所谓自发影响笔者有所质疑,本文将对此从当下儿童所处的教育及语言文化的角度进行简要的阐述。
关键词:儿童 读经 问题 建议
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台湾文化界发起儿童读经倡议以来,儿童读经热潮真可谓是席卷全国上下。如今无论是在繁华的都市还是偏远的乡村,处处可见诵歌谣一般诵着“人之初,性本善”的小孩子。对于这一热潮文化界的争论也可谓是异常激烈,彼此针锋相对,据理力争。笔者基于学识所限,在此仅浅谈一下对学前儿童读经的一点认识。
对于极力倡导儿童读经的言论中,印象最为深刻的当数王财贵教授的演说。王财贵教授于北师大的演讲确实是激情澎湃,极富感染力,但其一部《论语》或《老子》便可拯救孩子的一生,甚至于一个民族的观点似乎未免过于极端。但总的来说,王财贵、郭齐家等为代表的倡导儿童读经者,基本理由便是儿童诵读经典对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儿童人格养成大有裨益,并以儿童智力发育的“黄金期”为理论依据。对于这种观点、理由笔者不敢妄加菲薄,但对于儿童“素读”经典,即“不求理解含义、只照着字面朗读汉籍(即中国的经史子集)”,然后用一生去理解、消化,从而“受用一生”的观念,笔者确实有所质疑。笔者认为在现下的语言文化环境下,儿童咿咿呀呀读得的“经典”到“受用一生”的过程中存在着太多的障碍,其中最基本的便是教育及语言上:
一.经典教育缺乏系统性,读经就只能滞留于学龄前
我国古代教育基本是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系统性的经典教育。这一点在古代蒙学教材《三字经》中便清晰可见:
为学者,必有初。小学终,至四书。
孝经通,四书熟,如六经,始可读。
经既明,方读子,撮其要,记其事。
经子通,读诸史,考世系,知终始。
从中可见传统教育的一贯而下:识字——《小学》——《孝经》——四书——五经——子史。并且发蒙阶段便已对后面所学有所了解,如对于“五经”,《三字经》云:“诗书易,礼春秋,号六经,当讲求。有连山,有归藏,有周易,三易详。有典谟,有训诰,有誓命,书之奥。我周公,作周礼,著六官,存治体。大小戴,注礼记,述圣言,礼乐备。曰国风,曰雅颂,号四诗,当讽咏。”所以说,我国古代教育经学学习无论在顺序上还是内容上都有其一定之规、一定之旨,可谓是一脉而下的。
而现代读经教育,经历五四及文革的两次断层再次掀起浪潮之时,其稳定性都还难以确定的情况下,教育的系统性更是无从谈起。于是,学前儿童热热闹闹地读着“经”,但进入小学、中学后,开始的却是“正规”教材的学习。而文言内容小学教材根本就未编排,到了初中阶段接触的多是选于《世说新语》一类文集中的浅易文言故事,《论语》、《孟子》、《庄子》等的内容则是浅尝辄止,所记诗文仅80余篇。高中阶段文言内容有所增加,但也不足50%。所以总的情况就是,学前读经与正规教育仍然处于脱节的状态。对此,有人倡议小学中学教材编辑及教育兼顾学期儿童的读经情况,建立系统性的经典教育。但关键问题就在于儿童读经目前仍还处于社会浪潮之中,对其稳定性及意义还很难确定,建立系统性经典教育的道路自然还很远。
二.文言语境不复存在,所读经典难以消化
王财贵教授认为,儿童背诵经典,有些内容虽然现在不一定理解、消化,但是随着年龄增长、知识和阅历的增加,会像牛的“反刍”一样,慢慢地会将这些内容理解、消化。一位小学教师也满怀信心地倡导这种“素读”经典的方式,相信“经典作品,有种子的能量!”对于经典“种子的能量”,笔者并不否认,但关键是经典这粒“种子”培植于什么样的土壤中。
经典是以文言形式记录的,在古代的文言语境之下,我们不会否认一部经典会对人一生自发地产生作用,即便这部经典是在发蒙阶段摇头晃脑如鹦鹉学舌般被机械记忆下来的。虽然唐宋时期书面语与口头语已经开始逐渐分离,但古白话仍然是根植于文言书面语的,并且文言书面语与古白话并行于世,在这样的语境之下,儿童机械识记的经典会随着理解力的发展、阅历的增加,自发的发挥其价值,“受用一生”。但是,自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彻底废除文言统治地位之后,文言时代离我们越来越远,文言阅读理解上的障碍越来越大,甚至于被当下的学生看成是第二门外语。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学前记诵了大量的经典,而没有后面系统学习、理解的教育条件下,这些经典怎能自发地“酝酿发酵”,怎能被慢慢的“反刍”呢?最终很可能成为堆积在记忆仓库中的符号。
徐梓教授曾在《传统蒙学与传统文化》一文中说道:“蒙学以及作为其核心内容的蒙学教材,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某个时代,为什么而教学、教或学些什么以及怎样教学,往往是这一时代性格和气质的典型体现。通过蒙学这扇窗口,我们就能了解这个时代的精神风貌,了解这一时代的文化特征。”尽管徐老师的话是针对古代的启蒙教育而言的,但同样适于反观当下的儿童读经浪潮。这股轰轰烈烈的读经热潮反映出国家经济的发展、民族自信心的增长以及文化意识的觉省,但无论我们的对继承民族文化传统以及塑造新一代继承人的愿望怎样迫切,我们都应面对现实的情况。对于儿童读经问题的争论确实方方面面,但都不可以忘却我们最终的目的地,然后再考虑读什么、怎么读等一系列的问题。
三.仰望星空,直面现实
对于经典教育缺乏系统性的问题,前文提及有人倡议建立读经教育的系统体系。但这种观点难免会有复古的嫌疑,引来质疑儿童读经者更为激烈的批驳,指责这是历史的倒退。但问题的关键是这种建立体系的经典教育的内容是什么,这自然涉及当下读经争议热潮中对“经”的争议。如果这一“经”单纯等同于古代教育的“经”——儒家经典,甚或扩充到子、史,都会给人复古之忧。我们民族文化发展至今,“经典”的外延亦在发展扩充,所以现代儿童经典的启蒙自然应是对民族文化发展中各类经典的发蒙,不单是经史子集还有诗词曲赋等等。但针对儿童年龄的特征,虽然0到13岁是所谓的记忆“黄金期”,他们的生活仍应是“游戏的、艺术的、好奇的、探究的、涂鸦的、歌唱的、蹦蹦跳跳的……”。儿童阶段的经典教育终归是启蒙教育,不能用经典的重负压制孩子的童年。
另外儿童经典的启蒙确实不可忽视后面教育的持续发展,否则就如前文所以所有记诵的所谓“经典”只能成为记忆仓库中无意义的语言符号。笔者认为学前儿童经典的启蒙应当与后面教育相接轨,所有的启蒙都为后续的学习做准备。儿童读经热潮中争论的焦点之一便是儿童的记忆能力,而现下小学、中学阶段教材中古诗文教育的一大问题便是学生记忆负担过重,以至于古诗文教育量小质劣。问题的根源就如王财贵先生所言的错过了最佳记忆期“没救了”。如果真如此,补救自然可以放置于儿童启蒙期。儿童阶段将后面教育需接触的经典诗文于游戏中记诵下来,进入小、中学,随理解能力的发展,循序渐进的将童年记诵的诗文去理解品味,这不仅仅是教育上的事半功倍之举,亦是符合教育规律的。我国古代的教育就是是先记诵,再串讲的。这样的教育程序,对于学生文言语言阅读能力的培养也将大有益处,改变现下文言教学起步晚、效率差的境况。
总而言之,十几年的儿童读经热潮虽然显现出一定的问题,也引发社会各界的诸多争议,但随着各方力量的努力,已经取得了许多成绩,如各类研讨会的召开,各种精美的国学启蒙教材、光盘的出现都将一步步推动儿童国学启蒙教育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胡立业.“读经教育”要有延续性[J].语文建设,2010(7)
[2]蔺燕.对学龄前儿童“读经”问题的思考[J].新学术,2008(2)
[3]廖军和.儿童“读经”问题引发的争论[J].中国教育学刊,2006(3)
[4]刘晓东.儿童读经就是“蒙以养正”与郭齐家先生商榷[J].南京师大学报,2006(6)
[5]徐梓.传统蒙学与传统文化[J].寻根,2001(2)
刘洁,女,山东人,曲阜师范大学文学硕士,山东省菏泽学院中文系教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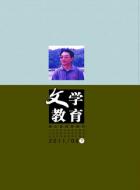
- 莺莺塔 / 马温
- 马一浮的“笑”和“哭” / 散木
- 论杜牧诗歌的怀古意识 / 盛莉
- 露西•斯诺 / 杨红霞
- 教学与行政双肩挑的殷杰教授 / 伍兵
- 《城邦暴力团》结构分析 / 孟令君
- 福柯理论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影响 / 景欣悦
- 论刘震云小说生命的异化状态 / 郭颖
- 语文课堂导语设计与运用 / 谢瑞芬
- 卡森•麦卡勒斯小说研究 / 曲晓晨
- 浅析高校英语教师的教学效能感 / 李媛媛
- 《呼啸山庄》和“三恋”的精神共通 / 何羚杰
- 《宗教与文学》中佛教与文学关系研究 / 李耀威
- 诗词中的双关举隅 / 丹慧敏
- 高职普通话课应加强听话训练 / 邓双荣
- 感悟古人的“闲”情 / 吴红
- 评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论》 / 石雯
- 如何进行英语语音教学 / 李颖
- 关于概念隐喻工作机制立体空间模型假设 / 陈玉梅
- 有效语言实践情境教学的特征与方法 / 周淑平
- 有对自动词与有对他动词可能态的用法差异 / 邱晓玫
- 略论设计的知识产权风险 / 邓俊
- 高中语文教学中长文短教的艺术处理 / 韦香琼
- 如何开发学生自主创新的潜能 / 张字洪 蔡由利
- 语文教学中如何预设有效问题 / 仲桂云
- 高校英语教师学科教学知识分析 / 李静
- 让语文课堂充满阳光 / 刘晓娟
- 高中英语阅读课文中的词汇教学方法 / 关颖
- 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词汇教学 / 俞静
- 怎样培养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 / 柴梦华
- “读者类型说”与语文教师的读者地位 / 罗雄
- 中学生逻辑思维训练实践探究 / 黄容春
- 课程资源与语文教学三维目标 / 姚红敏
- 学生语文自学能力的培养 / 骈玲玲
- 优化写作教学方法探析 / 卫雪利
- 商务英语翻译课程的学习要诀 / 李锦琴
- 唐代进士科在写作领域里的现代效应 / 杨扬
- 语文教学中的问题意识 / 朱易灵
- 中职旅游专业语文教学中的专业渗透 / 王菊珍
- 高中作文高效教学做法初探 / 孟庆焕
- 应把作文教学纳入普通语文课堂 / 吉伟
- 对潜能生的备考策略 / 黄红英
- 语言亮丽文章秀 / 赵红英
- 高职高专应用文写作类教材编写体例探析 / 李雯
- 考场作文写作技法探讨 / 褚福民
- 运用多媒体突破教学中的重难点 / 孟娜
- 课外阅读与写作的关联性 / 申翠英
- 高三后期作文复习的主题设想 / 李保国
- 新课改须落实学生学习习惯的转变 / 宋文娟
- 戏剧表演如何用于大学英语口语课 / 黄燕红
- 语文课怎样与写作进行有机结合 / 刘磊
- 走向作文教学的自由王国 / 颜更祥
- 《喧哗与骚动》里的人物分析 / 覃礼兰
- 《氓》中女主人公的婚姻观 / 周平平
- 新课改下的作文教学 / 程瑞莲
- 《淮上与友人别》赏析 / 严吉林
- 从叙述视角看《十九号房》的主题反讽 / 李逸云
- 如何巧拟题写好开头 / 王维侠
- 《伊豆的舞女》的虚无之美 / 王月琴
- 夏洛克对安东尼奥的恨之原因 / 贾冰
- 以生活为源积累作文素材 / 王新云
- 《蝇王》中的伦理困惑 / 于振飞
- 妙用修辞巧增色 / 池志波
- 《桃花扇》的语言艺术 / 田斌
- 名著推广阅读的有效方法 / 乔伟民
- 再议扬州方言数量短语后的助词“头” / 尹燕飞
- 民族院校《大学语文》教育的困境与对策 / 韩晓清
- 语文课堂教学中的虚假现象 / 薄春节
- 李白《将进酒》课堂教学实录 / 赵华
- 初中语文教学点滴谈 / 闫鸣
- 语文教学也应重视心理教育 / 胡杰
- 状位形容词的语义指向探析 / 陈伟
- 谈学前儿童的读经问题 / 刘洁
- 再析“谁之永号”的“之”“永” / 贺新梓
- 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几种途径 / 苏楠
- 对新时期班级管理工作的思考 / 黄苏锋
- 《虞美人》研读 / 李化
- 对学生自主课堂教学模式的思考 / 邓玉霞
- 中考半命题作文复习谈 / 李华明
- 让古典诗歌的意象鲜活起来 / 张丽
- 借鉴传统诵读法开展经典阅读 / 梁志斌
- 识字教学方法谈 / 苗冬梅
- 关于《故乡》的教学实践与尝试 / 周银玲
- 阅读教学中提高迁移能力的途径 / 曾仲权
- 诗歌《错误》的再审读 / 颜锟
- 浅谈班级凝聚力的形成 / 于勇
- 谈声乐有效教学 / 张萍
- 阅读教学中的情感交流 / 陈美嫦
- 对学生德育教育问题的思考 / 何瑞龙
- 高中阅读课语言积累途径研究 / 杨永辉
- 提高校长教学领导力的策略与方法 / 俞静
- 教学副校长领导力在实践中的提升 / 罗慧芳
- 高中语文课堂中的朗读教学 / 刘洪海
- 最是书香能致远 / 孙玉梅
- 如何提高学生现代文阅读的能力 / 程静
- 明明 / 王丽然
- 阅读 / 叶汉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