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文学教育 2011年第2期
ID: 151111
文学教育 2011年第2期
ID: 151111
当代回族文学创作与宗教
◇ 刘波
内容摘要:自古以来,文学便与宗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宗教在少数民族社会生活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并早已渗透到各少数民族社会生活之中。纵观当代回族文学创作历程,关于宗教题材与宗教人物的描写,经过了一个不同的演进变化过程。本文即论述了当代回族文学创作与宗教的关系。
关键词:当代 回族文学 宗教
自古以来,文学便与宗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以中国而言,《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其中的《周颂》既是宗教,又是文学;楚辞《九歌》也既是文学,又是宗教。因此,宗教与文学都是人类情感的表达方式,都是对世界的两种评说和把握方式,二者同属上层建筑,都是复杂的社会意识形态和广阔复杂的社会生活的复杂反映。它们同源而异流,如两股溪流,都发自于社会生活之源,而又各自沿着自己特有的渠道奔腾向前,以自己的波涛与喧闹,尽情地显示着自身的存在与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宗教与文学,犹如一对孪生兄弟,既有先天的血缘联系,也有后天的性格差异。
由于宗教在少数民族社会生活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并早已渗透到各少数民族社会生活之中。尤其是在政治、经济、哲学、伦理、文学艺术和生活习俗等方面,无不受到宗教的影响,留下了各种宗教印迹,而在全民信仰的民族,整个社会诸领域无一不受宗教的浸染。纵观当代回族文学创作历程,关于宗教题材与宗教人物的描写,经过了一个不同的演进变化过程。
从50年代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不久的近30年,回族文学是以歌颂为主调的歌颂型文学。宗教问题一直是回族文学创作中的一个禁区。这一时期的回族作家大多来自本民族地区,在党的关怀下,亲自参加了革命,亲自投身于火热的斗争,接受了新思想新文化的教育。当时初露头角的作家或后来才步入文坛的作家,在接受汉语言的同时,竭力学习和模仿汉族作家和外国作家(当时主要是苏俄作家)的写作(当然有相当一部分作家因熟悉本民族的本土文化,受到本民族民间文学的影响而成为作家,这也是事实)由此走上创作道路,所以他们的创作风格与中国当代文学作家中的汉族作家们有很大的相似之处。无论受本民族民间文学的影响还是受汉族作家的创作影响,他们均处于一个不断模仿的创作过程,属于一代具有一定成就的效仿型作家。
正是由于效仿别民族(主要是汉族)作家,加上大多数回族作家在接受外来文化的同时,只是单频道(纯粹实用性)地接受唯物论思想的教育,包括一些与宗教有关的民风民情,便在50-60年代中期的文学创作中,受到了无神论思想的冲击。作家们对待本民族传统文化,不假思索、不加研究地一概反传统,宗教理所当然第一个受到冷遇和致命的批判。几乎所有作家都在唱颂歌,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歌颂党的民族政策,歌颂社会主义新生活,歌颂民族团结、祖国统一,歌颂各民族的翻身解放等上面。当然,我们不反对这种颂扬,因为新中国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确立,这对中国少数民族来说,确是雨后晴天、翻天覆地的变化,确实值得大书而特书。但是,我们也认为,体现着每个民族历史文化深刻内涵民俗民情包括宗教信仰等,同样应该是不应被蔑视的文学创作的重要内容。
从50年代后期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不久,尽管回族作家的作品反映了本民族生活,带有一定的民族特色,如回族当代小说的开拓者哈宽贵的《金子》、《夏桂》,韩统良的《家》、《龙套》,郝苏民的《月光幽幽》等。但在“创作思想上,审美趣味上浓厚地带上中国当代政治变迁的历史风尘,甚至在这些作品的人物性格上因过多地涂上了政治色彩而失去了本民族的人文色彩。”宗教在他们看来是一个禁区,或不敢涉入,或有意无意地回避。当然,基于这一时期的客观现实,作家们不可能在创作上独辟蹊径,哲学上归属性思维必然导致归属于统一的政治模式而形成一种统一的创作模式。这个时期大部分回族作家的作品多数是寻找一种与汉族或与这一时期流行的看法相契合的生活表现,而缺乏从本民族生活、本民族历史文化以及本民族心理素质的角度去反映和描述生活。宗教,作为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自然要受到回避或扬弃。
到了三中全会后的新时期,随着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的落实,许多回族作家的笔触开始伸向这里,一般作品中常常出现的已演化为回民特用语的宗教术语和宗教活动自不必说,运用大部分篇章描写宗教人士和宗教活动以及宗教人物形象的作品也日益增多。有关这一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种是表现在新时期崛起的中青年作家的作品中,他们在寻找自己文学创作之“根”的同时,将笔端渗入本民族的宗教文化领域,正面描写宗教现象。他们既看到了宗教的消极因素,也发现了宗教文化在本民族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予以审美观照,如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查舜的《穆斯林的儿女》、白炼的《朋友》、马兰生的《索拉桥上的爱情》、石舒清的《修坟手记》、《沉重的季节》等等;另一种情况是完全肯定宗教文化的,如张承志。他是一位公开宣布皈依宗教的少数民族作家,他的现代宗教意识和肯定宗教文化在其小说《黄泥小屋》、《金牧场》和《心灵史》等作品中得到充分地表现。正如回族作家石舒清所说:“我族属使我的笔更容易游走在一个无限大的未知领域与精神空间。”他的文学创作之“根”就是在古老而纯朴的宁夏西海固,同样回族诗人马福宽,杨峰、师歌的“根”不也就在西北高原吗?
他们在中外文化的影响下寻觅着自己民族的“根”,并置于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文化和背景之中。因而以公正的态度去认识事物,描写生活,塑造形象。可见,当代回族作家有意识地向本民族历史文化土壤掘进是历史的必然。他们来自本民族,又回到本民族,立足于本民族。基于本民族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而生发的真诚感受,基于胸中流淌着民族血质而赋予的真诚意识是当代回族文学民族性的基本和首要的标志。回族作家们具有强烈的民族使命感而投入文学创作之中。他们把文化价值取向深入地指向了本民族传统文化所蕴含的美德,极力维护本民族文化属于美好的东西,以严峻的审视态度来描写本民族的风俗人情。其笔端有意无意地触及传统文化中的宗教现象,既揭示它在民族发展中的历史作用;又挖掘出陋俗中的劣根性,从而较深刻地展示出民族社会各个文化层次的特殊风貌。当然,由于宗教本身的复杂性,所以涉及宗教题材的作品,其主旨是复杂交错的;作家对宗教的感情,也是复杂奥妙的。
冯福宽的《割不断的思念》、《历史的影子》、《克尔白的新月》、《寻找丢失的骆驼》等作品典型地体现出作家对宗教的感情。在《寻找丢失的骆驼》一文中,作家通过荒原、苍茫的天色、孤零不靠的矮屋,深沉的黑夜沙漠和新月,构画了一幅完整的信仰之图,用以说明人类为追求一种目标时的那种坚不可摧的意志。即肯定了宗教的巨大凝聚力,又着力表现了虔诚固守的宗教信仰。而回族青年作家张承志是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中成绩卓著、影响很大的作家,也是一位公开宣布皈依宗教、系伊斯兰教最朴实的哲合忍耶教派的作家。他浓烈的现代人的现代宗教意识在其《黄泥小屋》、《金牧场》和《心灵史》等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心灵史》描述的是“世世代代举红旗”,用自己的生命义无反顾地殉教以捍卫自己的心灵自由的哲合忍耶教派在两百年间牺牲和流放、拼搏的历史,它即是一部艺术作品,也是一部回族人民的“宗教史”。
由此可见,宗教是人类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是人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元素。当代回族作家们以真诚、真实、慎重而严肃的态度来表现宗教题材与宗教人物,应当充分肯定这种极富现实意义的文学探索。但也应当看到,宗教与其陈旧的观念意识与各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现实生活以及心理素质等诸多方面有着紧密地联系。所以任何理论先行的简单化否定和肯定认识都不可能触及其本质,因而是不足取的。可以这样说,宗教现象可以和贫穷落后的民族紧密相联,也可以和繁荣富强的先进民族相并存;可以成为消极的力量,对各民族的发展和进步起着阻碍任用;也可以化为积极因素,成为各民族历史发展进程中某一阶段或时期的精神支柱。
马克思说:“一切宗教的内容是以人为本源,所以这些宗教在某一点上还有某些理由受到人的尊重,只有意识到,即使是最荒谬的迷信,其根基也是反映了人类本质的永恒性,尽管反映得很不完备,有些歪曲。”可见,宗教与各少数民族的现代生活关系十分密切。各少数民族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以及各种节日禁忌、风俗人情、婚丧嫁娶,乃至农牧业生产及收获等,都无不受到宗教的影响。这种影响已渗入到各少数民族社会诸领域,并积淀为稳定或超稳定的文化心理因素,隐含于各少数民族的精神文化之中,在不同时代和不同条件下,以各种形式展现出它颇具能量的作用。一个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学创作要历史地、真实地、生动地反映本民族生活的全部面貌、表现本民族固有的文化特质和揭示本民族的文化内核以及本民族的心理结构,不可能不对本民族文化现象作认真的考查和描述。宗教反映,渗透在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创作中,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
参考文献:
①阿城《文化制约着人类》(《文艺报》1985年7月6日)。
②《从文化的归属到文化的超越》,尹虎彬著,见《民族文学研究》第1987年第6期。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50-652页。
刘波,内蒙古包头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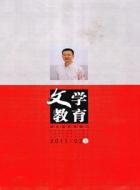
- 心安是吾乡——评周伟的《阳光故乡路》 / 叶立文
- 关于生命的哲学笔记 / 刘洁岷
- 《白雪乌鸦》:联缀性结构与现代性内涵的对接 / 周新民
- 实践教学在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中的建构 / 张芳
- 诗意文学课堂的重寻与呼唤 / 卢艳玲
- 英美文学自主学习探索 / 徐庆宏 常漪
- 新形式下大学语文教学浅论 / 刘红芹
- 提高大学语文课堂教学效果的思考 / 常亮
- 语文课堂教学中人文性的建构 / 高建云
- 我对当前文学的几点思考 / 汪政
- 情感教育在语文课堂减负中的作用 / 白家棚
- 语文教学中和谐课堂的营造 / 栾世堂
- 回家 / 薛荣
- 经验与超验——评薛荣的《回家》 / 李遇春
- 阳光故乡路 / 周伟
- 基于提问的语文教学重点难点突破策略 / 寿飞鸽
- 大学写作课教学法举隅 / 黄桂婵
- 当代回族文学创作与宗教 / 刘波
- 合作交流是提高课堂效率的捷径 / 林惠兰
- 大学写作课教学法举隅 / 黄桂婵
- 当代回族文学创作与宗教 / 刘波
- 学生学习文言文恐惧心理的克服 / 邓尚玲
- 情境创设与文学教育 / 陈灵彩
- 谈谈作文的细节描写 / 方锦娣
- 诗歌教学与诗词格律 / 李丽
- 新课标下现代诗歌教学探讨 / 马岽丽
- 作文材料漫谈 / 尹立新
- 高考作文探究 / 张金虎
- 高中语文新课程背景下的有效教学 / 李鹏
- 记叙文中字词的品析 / 王红霞
- 中学作文教学改革刍议 / 张旺雪
- 提高作文水平三部曲 / 张强
- 作文教学浅探 / 王红伟
- 提高作文讲评课实效性的策略 / 姚毅
- 记叙文写作中的走笔运巧 / 邵军花
- 《社戏》中“平桥村”解读 / 李林
- 《文心雕龙.神思》中的文学观刘 / 刘晶
- 从唐僧师徒的皈依路看《西游记》中的佛教思想 / 牟海超
- 浅谈文本开发的途径 / 黄美萍
- 杜甫《阁夜》中“人事音书漫寂寥”新解 / 曹天璞
- 《红楼梦》中晴雯的形象分析 / 赵明利
- 碾坊与渡船:《边城》不可忽视的两个意象 / 林忠港 朱晓林
- 浅析《背影》中的情感流程 / 余松涛
- 试论虹影博客身份形象的构建 / 陈瑜
- 孙犁小说中的联想艺术 / 邢宗和
- 试析三岛由纪夫《春雪》的叙事策略 / 王雪梅
- 《快乐王子》:诗意的唯美与现实的悲悯 / 吴涛
- 契诃夫《苦恼》以小见大的构思特点 / 张保明
- 浅谈王维山水诗的绘画美 / 胡富存
- 评佩里.安德森的《思想的谱系:西方思潮左与右》 / 陈桃霞
- 《浣纱记》叙事结构分析 / 吕维洪
- 《梦游天姥吟留别》的三美 / 曾菡召
- 评李遇春的《中国当代旧体诗词论稿》 / 郑祥琥
- 《所罗门之歌》中彼拉多.戴德的形象分析 / 李宝峰
- 中国古典山水田园诗浅探 / 洪季平
- 现代女性小说中的女性意识发展初探 / 姜辉
- 论惠特曼《草叶集》对郭沫若《女神》的影响 / 张浩
- 提高听课有效性的探究 / 袁湘英
- 谈古典词风的一主二变 / 刘福君 王幸
- 探析道家思想对心理咨询的启示 / 梅洪舟 范晓玲
- 浅说诗人与驴 / 刘翠华
- 新课程标准下的语文作业设计 / 董月萍
- 武汉地名的语言文化考察 / 何余华
- 以特色活动为载体优化新生代环保行为 / 叶季莉
- 从两大堕落主人公形象谈《失乐园》中的自由观 / 王雅雯
- 浅论《短歌行》的内容及其写作艺术 / 何平滚
- 论亦舒的写作姿态 / 王雷雷
- 论古希腊与先秦时代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 张晶
- 谈谈幼儿故事的趣味 / 徐虹
- 挖掘农村孝文化带来的和谐经 / 罗静荣
- 以《战地野餐》为例试析戏剧在教育中的作用 / 朱毅
- 对语文新课程改革的思考 / 韩晶晶
- 《月亮和六便士》与毛姆的哲学思想 / 刘 哲
- 从语言与文化关系的角度浅析外来词汇 / 常漪
- 语文教学中的情感教育策略 / 吴玉霞
- 从《芭蕉之旅》的英译看美国文化的本真吁求 / 熊莺
- 美国人屠杀印第安人背后的真相 / 张林艳
- 视译中存在的困难及应对策略 / 王宇珍
- 散文两章 / 龚玉林
- 割不断的情丝 / 刘协庭
- 信息18则 / 舒坦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