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文学教育 2011年第2期
ID: 151145
文学教育 2011年第2期
ID: 151145
《浣纱记》叙事结构分析
◇ 吕维洪
内容摘要:十部传奇九相思,通过运用叙事学方法对《浣纱记》进行不同的视角分析,我们看到:郎才女貌的外在形象,忠贞执着的爱情行为,反讽、对比的情节设置依然围绕着传统爱情主题而展开,叙事平衡的维护没有脱离对传统道德的宣扬。《浣纱记》对传统对立元素的解构扩大了爱情的内涵和悲剧意蕴,突破了传统剧目才子佳人以婚姻为目的的爱情模式。抨击假丑恶讴歌真善美,仍然是爱情叙事的本质内容。但由于发送者“行动元”的转移,丰富了情节发展的叙事张力,对塑造人物性格完善人物形象有着重要意义。把充满特色的矛盾冲突寓于普通的叙事结构中,使人物性格、心理的发展在合理的叙事中更加丰富而真实。
关键词:《浣纱记》平衡公式 结构主义置换法 结构语义学 形式主义组合法
元亡后,经过明初短暂的休养生息,社会由乱而治。明中叶以后,随着商业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的壮大,个性解放的要求变得更加强烈。个性解放常通过恋爱自由、婚姻自主来具体演绎,于是出现了“十部传奇九相思”的局面。梁辰鱼在借鉴《左传》、《国语》、《史记》、《吴越春秋》、《越绝书》、《吴地纪》等正史和野史的基础上,巧妙利用昆腔委婉典雅的“水磨调”[1],继承前人同类题材的艺术成就创作出的《浣纱记》,创新性地把范蠡和西施悲欢离合的爱情与吴越两国的兴衰更替结合起来。这种借生旦离合写国家兴亡的艺术构思,不仅扩大了传奇创作的题材范围,丰富了传奇的戏剧表现功能,同时也为改编创作传统故事题材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途径。沿着《浣纱记》“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足迹,出现了《秣陵春》、《长生殿》、《桃花扇》等大批名作。由此细考同类作品中有首创之功的《浣纱记》的叙事结构,从而探寻传奇的叙事规律,意义明显而重要。
一
在《浣纱记》中,范蠡西施的爱情过程及结局有别于以往中国戏曲的大众审美心理和情趣,不论是董《西厢》或王《西厢》还是代表南戏最高成就的荆、刘、拜等,演绎的都是才子克服重重困难和消除误会并与佳人结为美满婚姻的童话故事,歌颂了爱情的专贞和执着,鞭笞黑暗和假丑恶。《浣纱记》把范蠡西施的爱情置于国破家亡的大背景下,使个人的情感不得不服从于国家利益,他们的爱情成了爱国的献礼。爱情因与政治和国家利益息息相关,从而使其具有了更高的政治品位。这种崇高的爱情颠覆了传统意义上才子佳人以婚姻为目的的卿卿我我模式。在赞颂爱情崇高的同时,作者又着力表现了爱情的苦涩和沉重。因为爱情中渗透了太多的政治内容和社会负荷,使其变得苦涩。他们在如画的旖旎风光中匆匆相爱,又在沉重的政治风云中匆匆相别,为了国家的利益,无奈地选择了牺牲爱情,共同的作出了一个豪壮、痛苦和屈辱的决定:范蠡到吴国为奴三年,之后西施又献色三年,任吴王蹂躏。六年的相思虽换来了越国的胜利,可惜这对年轻的恋人,此时已是花残、心苦,本应美满的爱情,却已留下难以弥补的残缺。
梁辰鱼在《浣纱记》剧情的总体架构中,叙写了范蠡西施终归团圆并泛舟五湖的归宿,在情节上满足了观众对于“生旦团圆”的审美期待和欣赏习惯,同时也表现了自己对“女祸亡国”的传统观念的不同认识:西施不是间谍,不是祸水,不是惑主狐媚,不是美人计;西施入吴,如范蠡石室侍君一般,也是为国、为君、为民报效的一种方式。这就将西施与范蠡等量齐观,着力表现了这位深明大义、忍辱负重、爱国献身的巾帼英雄。西施这种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足以抑制从贞操角度可能提出的责难,又为“生旦团圆”奠定了可以引起悬念、激发同情和共鸣的心理基础。爱情抛却了华丽的面纱,还原传统价值观,更加重视心灵的美丽,这是明代张扬个性肯定人欲、追求自由的一种社会思想意识的体现。[2]
二
为便于分析,将《浣纱记》剧情简要叙述如下:范蠡西施在宁罗山下明澈的溪水边一见钟情并与一缕白纱定情——山雨欲来风满楼,吴国即将伐越——越国战败被围——越国买通伯嚭,吴王允降——越王范蠡君臣入吴为奴——君臣忍辱负重,得吴王信任并放归——卧薪尝胆,麻痹吴王,西施吴宫献色三年——范蠡西施离别,伍子胥死谏——同仇敌忾,越甲吞吴——吴王自杀,伯嚭被擒——范蠡西施历经磨难,泛舟五湖,归隐。
由上可见,《浣纱记》的情节采用顺叙的方式按照线性叙事模式进行,范蠡西施爱情力量的源泉可借用叙事学上的平衡公式和结构主义置换法表述如下。
法国叙事学家托多罗夫说,叙事是以某种形式平衡的状态开始,接着平衡被打破,最后重新恢复到平衡状态。图示为:平衡/完满状态→平衡打破/不平衡状态→寻求新平衡(正反力量势均力敌)→不平衡的状态→新的平衡。[3]通过对平衡叙事的研究,可以获得有关平衡背后的社会秩序问题的解决途径。按照此种研究方法,可以把《浣纱记》标示为:西施自由平静的生活→对立人物(吴王)破坏和同一阵营(越王、范蠡)破坏→范蠡君臣、西施与对立人物(吴王)斗争→获胜→重新过上平静闲适的生活。
在《浣纱记》中西施平衡的破坏者各不相同,分别是吴王、越王、范蠡。他们的目的各不相同,吴王的目的是获得美色,但他又是被动的受事者。越王、范蠡的目的是将西施当作获得国家独立和国家利益的手段,越王由于其位置的特殊性(国即家,家即国),因而一定程度上,他是将西施当作获取权利的手段。范蠡既是破坏者又是悲剧的承受者。越王、范蠡是平衡的破坏者又是新平衡的建立者。促使越王行动的动力是家国利益,促使范蠡行动的动力则源于国家利益和爱情。
上述分析表明,虽然破坏者的目的不一样,但情节脉络对故事架构的平衡模式是和谐的,其中越王、范蠡的行动力量是叙事的逻辑支点和平衡点,这个点使整部戏剧获得叙事的合理性。
施特劳斯认为,结构主义着眼于虚构的故事与其所对应的社会之间的关系,“虚构的故事对他而言,是社会为其成员所编制的代码信息,隐含在深层次的叙事结构当中”[4]。《浣纱记》表现了生旦团圆,但却是一种爱国献身、患难同志而不求荣华富贵的团圆,舟中花烛、湖上姻盟的格调,与传统戏剧中显扬个人或家族的俗套,如洞房花烛、金榜题名、一门族表等显然不同;《浣纱记》也表现了生旦归隐,却又是一种报仇雪耻、完姻团圆、功成身退的归隐,与传统戏剧中的渔樵高卧、友麋盟鸥也有所不同。《浣纱记》在总体上是一种团圆归隐的构架;表现为乐观地向往未来的儒家思想与深刻地审视现实的道家思想的合流,或者说是儒家思想中理想主义的进取精神和现实主义的人生思考的合流。[5]在倭寇屡次侵入东南沿海地区,国家形势岌岌可危的明中叶,《浣纱记》以大量的篇幅歌颂越国君臣上下一心和复国的坚强毅力,批判吴国君臣的骄奢腐化导致亡国,有深刻的现实意义。[6]在《浣纱记》中存在大量对立的元素,如“越王”和“吴王”、“节俭”和“奢侈”、“深谋远虑”和“短视”、“虚心”和“骄横”等等。这些二元对立的元素组,构成了戏剧激烈的矛盾冲突和叙事风貌。《浣纱记》善于运用对比的手法,把人物置于矛盾冲突之中来表现。剧中的人物几乎都是成对出现的;夫差与勾践,一个是骄傲自负、不谙事理、荒淫奢侈的昏君;一个是忍辱负垢,发愤图强,胸怀大志的英主。伍员和伯嚭,一个是刚肠直性、赤心报国的良臣,一个是“惯用倾险之智,全凭三寸斑斓舌”、“一味妒贤嫉能、以尸禄保位”的奸贼。范蠡和文种又是一对,文种善于治内,范蠡长于对外,同是忠臣,但两人的识见有许多不同。在这两对大臣的对比描写中,作者不是平分墨色,写伍员的刚直是为了反衬伯嚭的奸诈,写文种的见短是为了突出范蠡的谋士形象。[7]
该剧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与观众欣赏习惯或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结局相比既保留又相对立的安排,即经典才子佳人中:才子/佳人→英俊有才/貌美聪慧→家庭或其它个人原因→分离→斗争→实现目的→团圆或死亡(异化的团圆)。才子佳人卿卿我我的爱情模式始终是以婚姻作为追求的终极目标,因而始终摆脱不了个人的功利性,即使是悲剧也仅仅是个人的悲剧。《浣纱记》中:范蠡/西施→英俊干练/貌美忠义→国家危亡→分离→战争→实现目的(国家和个人)→团圆→隐退。范蠡西施的爱情模式把国家利益摆在个人的爱情幸福之上,以实现“大我”的共同理想,牺牲“小我”,升华了爱情的意义。其团圆是以付出国家的(战争)和个人的(青春、人格)昂贵代价来实现的,最终的隐退又多了几许惆怅和无奈,是一曲苦涩的叹歌,甜蜜的悲歌。
对形成戏剧冲突的二元对立素的解构,可以看出新对立的产生丰富了叙事的结构。突破了以往爱情团圆模式单一的叙事结构模式,增加了故事情节的跌宕性,改变以往故事结局的喜剧性,以喜中含悲,悲中有喜的结局诠释了世事沧桑人生无常的神秘多元性。颠覆了传统爱情戏的唯美梦幻风格,将爱情从以往才子佳人的二人世界的小天地中解放出来,还原其社会属性,充分体现了以共同理想为基础的爱情力量的伟大,淡化否定了传统的贞操观。
三
格雷姆斯的结构语义学既关注叙事语言,又赋予其结构功能的意义。他将“行动元”作为核心分析单位,通过主体/客体、发送者/接受者和帮助者/反对者三组对立元素,将逻辑结构同功能识别和经验主义分析结合在一起。根据“行动元”的基本特征划分出不同类型的叙事。在《浣纱记》中,以解救国家危亡为目标的行动里,发送者是吴王,范蠡是接受者。由于发送者起着最重要的作用,是整个叙事的最终动力,所以范蠡虽然是主体但作出的行为总体上是被动的,是出于救亡图存的策略作出的反映,是处于被动状态下的一种积极反应。在取得对吴战争的胜利后,由于所处地位发生变化,范蠡成为行动的发出者,积极主动地打消西施的顾虑,解救西施,范蠡成为命令发出者对叙事发展的推动以及其自我个体意识的增强主导着整部叙事的发生发展的结局。
在整个故事的发展中,作为主体的范蠡从最初的被动接受命令,即行动接受者,到最后的行动发送者,这一转变的过程成为整部戏剧叙事发展的驱动力。而接受者对于此类非常规人物的认同感也随着人物主观意识的成长与转变而逐渐加深,进而与剧中人物同欢喜共快乐。
我们运用形式主义组合法,通过对叙事角色的分析,获得一个关于《浣纱记》的经典叙事模型。剧中基本人物角色可分为:男主角、对立角色、、同盟者、女主角。叙事结构可以表述为:男主角平静的生活→对立角色进行战争→男主角和对立角色斗争→男主角被击败→失去女主角→男主角休养生息→男主角和对立角色再次斗争→对立角色被击败→救回女主角→男主角识破同盟者的陷阱→男主角和女主角归隐。虽然各出中的对立角色有差异:吴国和越国的根本关系是对立的,但在第七出《通嚭》中,伯嚭从个人利益出发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客观上成了越国的同盟者。吴国内部,伍员和伯嚭又构成了忠奸的对立等等。围绕吴越国家利益这一主要矛盾的冲突,以范蠡西施的爱情串演吴越争霸的历史,剧中组织了很好的戏剧冲突:吴国内部有伍员和伯嚭的忠奸冲突,有夫差与伍员的君臣冲突,有夫差与公子友的父子冲突;越国内部,有范蠡和文种认识上的矛盾,有范蠡西施的个人爱情幸福与君国利益的矛盾等等。梁辰鱼注意把握两国矛盾冲突的性质,吴国内部的冲突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越国内部的矛盾是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非对抗性的矛盾。在展示这些矛盾冲突时,作者不是单纯地、孤立地去描写,而是把这众多的矛盾冲突紧紧附着在吴越双方争霸这条基本矛盾冲突的主线上,将各种矛盾冲突巧妙地交织在一起,使得剧情一浪推一浪,逐渐趋于高潮,人物性格在矛盾冲突中逐步得到表现,渐次趋于鲜明,完整。[8]
四
通过运用上述四种叙事学方法对《浣纱记》进行不同视角分析的阐述,我们看到:首先,郎才女貌的外在形象,忠贞执着的爱情行为,反讽、对比的情节设置依然围绕着传统爱情主题的展开,叙事平衡的维护没有脱离对传统道德的宣扬。其次,对传统对立元素的解构扩大了爱情的内涵和悲剧意蕴,突破了传统剧目才子佳人以婚姻为目的的爱情模式,抨击假丑恶、讴歌真善美,仍然是爱情叙事的本质内容。再次,由于发送者“行动元”的转移,丰富了情节发展的叙事张力,对塑造人物性格完善人物形象有着重要意义。最后,把充满特色的矛盾冲突寓于普通的叙事结构中,使人物性格、心理的发展在合理的叙事中更加丰富而真实。由此可见,没有梁辰鱼付出一定代价的开拓,难以想象孔尚任毫无借鉴,单凭一己之力就能在戏剧史上凌空创作出《桃花扇》这样一部不朽之作。[9]
参考文献:
[1]【明】沈宠绥.度曲须知[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18.
[2][5][9]许建中.《浣纱记》结构论(下)一传奇结构研究之三[J].盐城师专学报,1994(2):23-25.
[3][4]安德斯·汉森等著.崔保国等译.大众传播研究方法.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169、177。
[6]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四).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68
[7][8]刘斌.借男女离合之情抒国家兴亡之感——浅谈梁辰鱼的浣纱记[J],文史知识,1988(12):97-100
吕维洪,曲靖师范学院人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古代文学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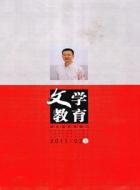
- 心安是吾乡——评周伟的《阳光故乡路》 / 叶立文
- 关于生命的哲学笔记 / 刘洁岷
- 《白雪乌鸦》:联缀性结构与现代性内涵的对接 / 周新民
- 实践教学在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中的建构 / 张芳
- 诗意文学课堂的重寻与呼唤 / 卢艳玲
- 英美文学自主学习探索 / 徐庆宏 常漪
- 新形式下大学语文教学浅论 / 刘红芹
- 提高大学语文课堂教学效果的思考 / 常亮
- 语文课堂教学中人文性的建构 / 高建云
- 我对当前文学的几点思考 / 汪政
- 情感教育在语文课堂减负中的作用 / 白家棚
- 语文教学中和谐课堂的营造 / 栾世堂
- 回家 / 薛荣
- 经验与超验——评薛荣的《回家》 / 李遇春
- 阳光故乡路 / 周伟
- 基于提问的语文教学重点难点突破策略 / 寿飞鸽
- 大学写作课教学法举隅 / 黄桂婵
- 当代回族文学创作与宗教 / 刘波
- 合作交流是提高课堂效率的捷径 / 林惠兰
- 大学写作课教学法举隅 / 黄桂婵
- 当代回族文学创作与宗教 / 刘波
- 学生学习文言文恐惧心理的克服 / 邓尚玲
- 情境创设与文学教育 / 陈灵彩
- 谈谈作文的细节描写 / 方锦娣
- 诗歌教学与诗词格律 / 李丽
- 新课标下现代诗歌教学探讨 / 马岽丽
- 作文材料漫谈 / 尹立新
- 高考作文探究 / 张金虎
- 高中语文新课程背景下的有效教学 / 李鹏
- 记叙文中字词的品析 / 王红霞
- 中学作文教学改革刍议 / 张旺雪
- 提高作文水平三部曲 / 张强
- 作文教学浅探 / 王红伟
- 提高作文讲评课实效性的策略 / 姚毅
- 记叙文写作中的走笔运巧 / 邵军花
- 《社戏》中“平桥村”解读 / 李林
- 《文心雕龙.神思》中的文学观刘 / 刘晶
- 从唐僧师徒的皈依路看《西游记》中的佛教思想 / 牟海超
- 浅谈文本开发的途径 / 黄美萍
- 杜甫《阁夜》中“人事音书漫寂寥”新解 / 曹天璞
- 《红楼梦》中晴雯的形象分析 / 赵明利
- 碾坊与渡船:《边城》不可忽视的两个意象 / 林忠港 朱晓林
- 浅析《背影》中的情感流程 / 余松涛
- 试论虹影博客身份形象的构建 / 陈瑜
- 孙犁小说中的联想艺术 / 邢宗和
- 试析三岛由纪夫《春雪》的叙事策略 / 王雪梅
- 《快乐王子》:诗意的唯美与现实的悲悯 / 吴涛
- 契诃夫《苦恼》以小见大的构思特点 / 张保明
- 浅谈王维山水诗的绘画美 / 胡富存
- 评佩里.安德森的《思想的谱系:西方思潮左与右》 / 陈桃霞
- 《浣纱记》叙事结构分析 / 吕维洪
- 《梦游天姥吟留别》的三美 / 曾菡召
- 评李遇春的《中国当代旧体诗词论稿》 / 郑祥琥
- 《所罗门之歌》中彼拉多.戴德的形象分析 / 李宝峰
- 中国古典山水田园诗浅探 / 洪季平
- 现代女性小说中的女性意识发展初探 / 姜辉
- 论惠特曼《草叶集》对郭沫若《女神》的影响 / 张浩
- 提高听课有效性的探究 / 袁湘英
- 谈古典词风的一主二变 / 刘福君 王幸
- 探析道家思想对心理咨询的启示 / 梅洪舟 范晓玲
- 浅说诗人与驴 / 刘翠华
- 新课程标准下的语文作业设计 / 董月萍
- 武汉地名的语言文化考察 / 何余华
- 以特色活动为载体优化新生代环保行为 / 叶季莉
- 从两大堕落主人公形象谈《失乐园》中的自由观 / 王雅雯
- 浅论《短歌行》的内容及其写作艺术 / 何平滚
- 论亦舒的写作姿态 / 王雷雷
- 论古希腊与先秦时代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 张晶
- 谈谈幼儿故事的趣味 / 徐虹
- 挖掘农村孝文化带来的和谐经 / 罗静荣
- 以《战地野餐》为例试析戏剧在教育中的作用 / 朱毅
- 对语文新课程改革的思考 / 韩晶晶
- 《月亮和六便士》与毛姆的哲学思想 / 刘 哲
- 从语言与文化关系的角度浅析外来词汇 / 常漪
- 语文教学中的情感教育策略 / 吴玉霞
- 从《芭蕉之旅》的英译看美国文化的本真吁求 / 熊莺
- 美国人屠杀印第安人背后的真相 / 张林艳
- 视译中存在的困难及应对策略 / 王宇珍
- 散文两章 / 龚玉林
- 割不断的情丝 / 刘协庭
- 信息18则 / 舒坦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