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文学教育 2011年第2期
ID: 151138
文学教育 2011年第2期
ID: 151138
孙犁小说中的联想艺术
◇ 邢宗和
内容摘要:联想是一种心理活动。孙犁非常善于运用各种联想方式,或扩大审美感知的范围,或揭示审美意象的丰富内涵,或体认审美对象的本质属性,或拓展审美对象的普遍意义。既使自己情有所依,又创造了生动感人的审美意象。
关键词:孙犁 小说 联想 艺术 意象
在孙犁的小说中,我们时时能够感受到作家那浓郁而热烈的情感:对于勇于牺牲的青年妇女的敬佩,对亲如一家的人民群众的热爱,对战斗过的冀中平原的怀恋。作家的情感似乎打通了空间的阻隔,飞越了时间的长河,突破了事物之间的关垒,自然而自由的流泻着。孙犁为什么能使情感抒发既尽情挥洒,又收放自如?应该说,联想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联想是一种审美心理活动。它来源于对生活的审美感知。孙犁在读书、求学、谋生中长期奔波,参加革命工作后,又一直从事文字工作,这为孙犁形成联想提供了生活基础和知识前提。孙犁非常善于运用联想,既使自己情有所依,又创造了一个个生动感人的审美意象。
一.接近联想扩大审美感知范围
接近联想是指在审美活动中,常常由某一对象的审美特征联想到在时间或空间上接近的另一对象的审美特征,从而扩大审美感知的范围。这种联想即为接近联想。孙犁为了营造审美意境,经常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将审美感受嫁接移植得以自由抒发。《琴和箫》的结尾,在黄昏“我”遥望着漫天芦苇,“远远看见一片深红的舞台幕布,飘卷在晚风里。人们集齐的时候,那上面第一会出现两个穿绿军装的女孩子,一个人拉南胡,一个人吹箫,演奏给人们听。”这“两个穿绿军装的女孩子”也许不是大菱二菱,但绝对也应该是大菱二菱的战友、伙伴。这些如花的生命在民族战争中过早地凋谢。但是她们演奏出的“力量”,正从“漫天芦苇”所织就的“大帐幕”中“升起”。孙犁抓住舞台空间和黄昏的时间展开联想,将沉痛和悲愤的情感蕴含在色彩鲜明、画面灵动的审美意境中,既寄托了对逝去的生命的哀思,又表现了革命脉搏永不停止跳动的深刻内涵。
二.相似联想揭示审美的丰富内涵
抓住事物之间的形状或性质的相似点,由此事物想到彼事物就是相似联想。这种联想方式常用比喻、象征、比拟修辞手法,联想特征非常明显,所以在审美活动中经常运用。孙犁非常善于抓住人物的瞬间特征,运用相似联想,展示形象的美好心灵,揭示审美境象的丰富内涵。作家似乎特别喜欢以红喻火,给在冰天雪地战斗着的人们以些许暖意。比如《红棉袄》:“灶堂里的火旺了,火光照得她的脸发红,那件深红的棉袄,便象蔓延着火焰一样。”再如《吴召儿》“她登在乱石尖上跳跃着前进。那翻在里面的红棉袄,还不断被风吹卷,像从她的身上撒出的一朵朵的火花,落在她的身后。”作家喻“红棉袄”为火焰、火花,把单纯的物象转化为含蕴着深厚情感和丰富内涵的意象,既昭示了两位小姑娘对人民子弟兵的炽热的情感,也揭示了她们性格的细微差异。前者热情里透着腼腆,后者热情中带着活泼。
三.对比联想体认审美对象的本质属性
对比联想是指在对某一事物的审美活动时,引起和该事物具有相反特征的另一事物的审美感受,使两种事物在性质或形态上产生对比,从而加深对该事物的本质属性的认识。孙犁常用色彩的对比,凸现审美意象的形态美。如用黑、白、红三种最鲜明的色彩组合成一个热情、勇敢、矫健的吴召儿爬山的形象。作家还常用人物和事件的对比,表现审美对象的心灵美。如身材干瘦、眼神干涩、说话气喘的邢兰,干起活来,却是一个“拼命三郎”(《邢兰》)尽管环境艰难,老胡还是“从山沟里摘回几朵还在开放着的花,插在一个破手榴弹的铁筒里,摆在桌上”,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审美情趣的热爱生活的美好心灵(《老胡的事》)。
四.关系联想拓展审美对象的普遍意义
审美主体根据事物之间的某种关系,由个体到整体或由原因到结果,扩展审美对象的外延或拓展审美对象的内涵,使得审美对象更具有普遍意义。如《浇园》,伤员李丹看到香菊为多打粮食而挥汗如雨浇园时想“要吸收多少水,才能止住这庄稼的饥渴?要流多少汗,才能换来几斗粗粮,供给我们吃用?他深深地感到自己战斗流血的意义,对香菊的辛苦劳动,无比地尊敬起来。”在这里李丹和香菊不仅是一个个审美对象,同时又是军民两个审美群体的代表。
邢宗和,河南偃师市国瑾中学教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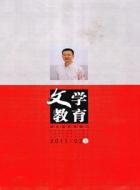
- 心安是吾乡——评周伟的《阳光故乡路》 / 叶立文
- 关于生命的哲学笔记 / 刘洁岷
- 《白雪乌鸦》:联缀性结构与现代性内涵的对接 / 周新民
- 实践教学在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中的建构 / 张芳
- 诗意文学课堂的重寻与呼唤 / 卢艳玲
- 英美文学自主学习探索 / 徐庆宏 常漪
- 新形式下大学语文教学浅论 / 刘红芹
- 提高大学语文课堂教学效果的思考 / 常亮
- 语文课堂教学中人文性的建构 / 高建云
- 我对当前文学的几点思考 / 汪政
- 情感教育在语文课堂减负中的作用 / 白家棚
- 语文教学中和谐课堂的营造 / 栾世堂
- 回家 / 薛荣
- 经验与超验——评薛荣的《回家》 / 李遇春
- 阳光故乡路 / 周伟
- 基于提问的语文教学重点难点突破策略 / 寿飞鸽
- 大学写作课教学法举隅 / 黄桂婵
- 当代回族文学创作与宗教 / 刘波
- 合作交流是提高课堂效率的捷径 / 林惠兰
- 大学写作课教学法举隅 / 黄桂婵
- 当代回族文学创作与宗教 / 刘波
- 学生学习文言文恐惧心理的克服 / 邓尚玲
- 情境创设与文学教育 / 陈灵彩
- 谈谈作文的细节描写 / 方锦娣
- 诗歌教学与诗词格律 / 李丽
- 新课标下现代诗歌教学探讨 / 马岽丽
- 作文材料漫谈 / 尹立新
- 高考作文探究 / 张金虎
- 高中语文新课程背景下的有效教学 / 李鹏
- 记叙文中字词的品析 / 王红霞
- 中学作文教学改革刍议 / 张旺雪
- 提高作文水平三部曲 / 张强
- 作文教学浅探 / 王红伟
- 提高作文讲评课实效性的策略 / 姚毅
- 记叙文写作中的走笔运巧 / 邵军花
- 《社戏》中“平桥村”解读 / 李林
- 《文心雕龙.神思》中的文学观刘 / 刘晶
- 从唐僧师徒的皈依路看《西游记》中的佛教思想 / 牟海超
- 浅谈文本开发的途径 / 黄美萍
- 杜甫《阁夜》中“人事音书漫寂寥”新解 / 曹天璞
- 《红楼梦》中晴雯的形象分析 / 赵明利
- 碾坊与渡船:《边城》不可忽视的两个意象 / 林忠港 朱晓林
- 浅析《背影》中的情感流程 / 余松涛
- 试论虹影博客身份形象的构建 / 陈瑜
- 孙犁小说中的联想艺术 / 邢宗和
- 试析三岛由纪夫《春雪》的叙事策略 / 王雪梅
- 《快乐王子》:诗意的唯美与现实的悲悯 / 吴涛
- 契诃夫《苦恼》以小见大的构思特点 / 张保明
- 浅谈王维山水诗的绘画美 / 胡富存
- 评佩里.安德森的《思想的谱系:西方思潮左与右》 / 陈桃霞
- 《浣纱记》叙事结构分析 / 吕维洪
- 《梦游天姥吟留别》的三美 / 曾菡召
- 评李遇春的《中国当代旧体诗词论稿》 / 郑祥琥
- 《所罗门之歌》中彼拉多.戴德的形象分析 / 李宝峰
- 中国古典山水田园诗浅探 / 洪季平
- 现代女性小说中的女性意识发展初探 / 姜辉
- 论惠特曼《草叶集》对郭沫若《女神》的影响 / 张浩
- 提高听课有效性的探究 / 袁湘英
- 谈古典词风的一主二变 / 刘福君 王幸
- 探析道家思想对心理咨询的启示 / 梅洪舟 范晓玲
- 浅说诗人与驴 / 刘翠华
- 新课程标准下的语文作业设计 / 董月萍
- 武汉地名的语言文化考察 / 何余华
- 以特色活动为载体优化新生代环保行为 / 叶季莉
- 从两大堕落主人公形象谈《失乐园》中的自由观 / 王雅雯
- 浅论《短歌行》的内容及其写作艺术 / 何平滚
- 论亦舒的写作姿态 / 王雷雷
- 论古希腊与先秦时代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 张晶
- 谈谈幼儿故事的趣味 / 徐虹
- 挖掘农村孝文化带来的和谐经 / 罗静荣
- 以《战地野餐》为例试析戏剧在教育中的作用 / 朱毅
- 对语文新课程改革的思考 / 韩晶晶
- 《月亮和六便士》与毛姆的哲学思想 / 刘 哲
- 从语言与文化关系的角度浅析外来词汇 / 常漪
- 语文教学中的情感教育策略 / 吴玉霞
- 从《芭蕉之旅》的英译看美国文化的本真吁求 / 熊莺
- 美国人屠杀印第安人背后的真相 / 张林艳
- 视译中存在的困难及应对策略 / 王宇珍
- 散文两章 / 龚玉林
- 割不断的情丝 / 刘协庭
- 信息18则 / 舒坦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