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文学教育 2011年第2期
ID: 151151
文学教育 2011年第2期
ID: 151151
现代女性小说中的女性意识发展初探
◇ 姜辉
内容摘要:从“五四”前后开始,现代女性作家作品中的女性意识逐渐发展开来,从起初的隐晦而不违封建礼教,到大胆追求女性意识的独立,最终在建国之前开始消解。这种女性意识在女性文学作品中的显现与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来的女性文学走向。
关键词:现代 女性小说 女性意识
自1918年,第一篇由现代女性作家创作的小说公开发表以来,女性作家们就当仁不让地活跃于文坛之上了[1]。她们在男权社会的腐浊气氛里,怀着满腔的哀怨,以柔弱之手拈起纤纤细笔,开始尝试在作品中与男性对话。
女作家们最先敢于着墨运笔的对象是作为社会最小单位的家庭,但在与家庭中男性的对话过程中,她们面临着一个不可逾越又无法回避的高壁坚垒──夫权。她们在这壁垒前拜倒,轻声慢语地向作品中那个若隐若现的夫君表述浓浓的爱意。苏雪林(绿漪)正是这类女作家的典型。她的小说大多囿于封建礼教,“礼教所不许的爱,她是不肯写的,她只敢在礼教的范围之内,竭力发挥她的天才,书写她心中的爱。”[2]但是,在看似温柔顺从的笔调中,却道出了夫权制度下的女性不敢言明的欲求──男女平等之爱。在《鸽儿的通信》中,苏雪林将这份爱化作妻子盼夫早归的书信,虽然字字句句不脱礼教束缚,但字里行间又分明流露着为礼教所不敢说出的夫妻之间的真实情感。在她的长篇小说《棘心》中,苏雪林试验性地塑造了胆敢突破道德约束、与已婚男子热恋的知识女性杜醒秋。但值得注意的是,苏雪林并未敢将这段在一定程度上抨击了传统道德的恋情安排在国内,它的场景被安置在以浪漫著称的法国,而其结局亦滑入了两人分手,分别过上“正常”生活的局面。
苏雪林的意义在于,她在顺从与哀怨中,寻找到女性对抗男权社会的突破口,即男女双方平等之爱。而与其同时的凌叔华亦以爱为目标,且走得更远。在小说《绣枕》中,凌叔华让主人公大小姐在闷热的大暑天里,不辞辛苦,用“三四十样丝线”绣成一对靠枕,送给白少爷,这是男权社会中,深闺小姐对爱情憧憬的象征,以靠枕为信物,寄托深宅大院内年轻女子的怀春之情,仿佛暗合了封建时代的美丽爱情故事,但《绣枕》的结局却是讽刺和滑稽的:在那对靠枕被送往白家的当晚,正逢白家请客,客人们酒后不能自抑的呕吐和踩踏将这对靠枕糟蹋得面目全非。在这篇小说中,绣枕“成为中国传统女性‘闺房情怀’的最为确切的隐喻。”[3]《绣枕》的意向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女性已经意识到,在男权体制之下,女性对平等爱情的要求是无法被占有统治地位的男性接受和尊重的,女性对平等爱情的乞求也显得非常可笑。在此背后,似乎能够若隐若现地看到,女性作家们正在渐渐确定自己作为女性的独立身份,一场与男权对抗的革命即将爆发。
真正将独立的女性意识呈显出来的是丁玲。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前后,政治气氛趋紧,文学队伍进入低潮,“仅就女作家队伍来说,第一代女作家群体进入了低沉期,中国文坛出现了暂时的女性轮空状态”[4]。丁玲就在这时凭借《梦珂》及《莎菲女士的日记》等作品豁然登场,让当时的文坛倍感震动。莎菲女士的形象在建立独立的女性意识的问题上是具有突破意义的。首先,莎菲是一个脱离了家庭困囿的新潮女子,她既没有成为一个男人的妻子,也没有在男人的追求下迷失自我,自始至终都是一个独立的女性。这一点与冯沅君塑造的人物不同。冯沅君笔下的女性人物大多大胆奔放,可以为爱情不理父母之命,甚至可以为爱情付出生命,但冯沅君总是将小说中的男性确定为人格上毫无瑕疵的理想恋人,这样的人物出现在女性角色面前,她就被剥夺了思考、分析、选择的机会,最终男女主人公均为爱情而自我燃烧(参看冯沅君小说《旅行》、《隔绝》、《隔绝之后》等),这显然只是对封建父权的反叛和对家长制度的逃脱,而非真正建立独立的女性意识。莎菲与之不同之处在于,她在寂寞和苦闷中还不放弃选择的权利,在她对两个看似还算优秀的男人进行了比较和分析之后,毅然决定继续固守寂寞。在她绝叫声中,我们看到一个新式的女性形象正从由男性意识构筑的硬茧中探出触角,即将振翅起舞。其次,莎菲这一角色不再像以往的形象一样仅仅代表了“女性”,她更代表了“人”。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形象,莎菲不再坚持“坐怀不乱”的清高,当她看到英俊的凌吉士时,立刻被迷住了。在莎菲的情怀之中,充满了感性,这种感性使她具有了强大的生命活力,更使她给人们带来的震撼,远比那些仿佛不食人间烟火的纯洁女性形象大得多。最后,莎菲是灵肉统一的。莎菲并非一个完全被情感支配、没有头脑的女子,在她的感性背后,有着成熟且强大的理性后盾,她与封建礼教统治下含蓄、贞节而禁欲的“优秀”女子形象相去甚远,又与艳情小说中开放而无知的女性不同,真正实现了灵与肉的统一。可以说,只有在丁玲笔下,现代女性才真正成为了成熟而且完整的女人。
但丁玲并未就此停住在作品中构建女性性别意识的笔。《莎菲女士的日记》发表十三年后,丁玲在《我在霞村的日子》中,以模糊多义的贞贞形象指向了深受社会痼疾所累,但又常常扮演封建礼教卫道者角色的普通民众,在怀疑中质问了男权沉疴下普通民众对待性别问题的价值观。诚然,《我在霞村的日子》的人物塑造略显粗糙,对人性的刻画亦未深入,但决不能因此否定了该作品对女性性别意识的构建作用。贞贞具有多重意义:既被动地失去了贞操,又主动利用身体获得情报支持抗日;既作为村民的亲人和恩人受到多数人内心的同情,又受到他们溢于言表的鄙视;既在肉体上饱受凌辱,又在心灵上保持纯洁;既对封建贞节观念不以为然,又未对持有这种观念的村民做任何反抗,而是最终选择了离开霞村治病,这看似重新开始,实际上更是一种逃避。与莎菲这种上流社会中的反叛小姐形象不同,贞贞是借以质问下层民众的武器。在他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封建礼教观念遮蔽了他们的心灵,让他们迷失在对丧失贞操的女子的蔑视和对亲人的同情之间,难于权衡,这正是当时中国女性面临的实际问题。若不能注意到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思想中的封建观念,仅仅宣扬城市里上流小众的新女性形象,是不足以从根本上以解决这样的问题的。因此,可以说《我在霞村的日子》是“五四”之后文学作品中女性意识最全面的彰显,是在文学作品中建立了独立的女性性别价值取向的标志,也是现代女性文学发展的至高点。
从“五四”运动开始到40年代初,一些女性作家在文学作品中构筑了较为独立的女性性别意识,但这一意识由于抗日战争和随后的解放战争对社会的影响,并未得到充分的深化,也未能蔓延扩散开来,恰恰相反,女性意识开始在文学作品中消解了。扛起消解女性意识这面大旗的旗手又是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丁玲创作生涯的又一高峰,也是她引导中国女性文学走向女性意识消解的转折。在《莎菲女士的日记》和《我在霞村的日子》之后,丁玲又最先根据政治的需要,于其作品中隐去了在当时不合时宜的女性意识。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女性人物黑妮、董桂花等,已不再充满妇女特有的感性,她们的性格、行动为革命理性操控着,偶然出现的感性成分也已经不再像莎菲一样狂妄,不再像贞贞一样有着质感。那些感情成分的出现不过是在革命理性之上撒下的一丁点调味料而已。在对女性角色的刻画上,丁玲的转变是显而易见的:从表现感性理性参半的人物形象转化为表现理性占压倒力量的人物;从情感话语的表述转化为革命话语的表述。诚如有论者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可以看做是作者正式放弃女权立场的标志性作品。”[5]
从“五四”前后到建国之前的三十年间,现代女性文学逐渐从萌芽到成熟。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女性文学一直被隐于其间的女性意识支配着走向,而女性意识从“隐”到“显”再到“被消解”,并不是偶然的,它是与社会和政治的发展相契合的。这种趋势并没有就此结束,建国后到改革开放之前,女性意识在文学作品中进一步消解,直至完全被遮蔽。八十、九十年代,以张洁、王安忆、林白、陈染为代表的当代女性作家在作品中将被遮蔽的女性意识爆炸式地彰显出来,无疑是对现代女性文学中女性意识的继承和对其长期被消解、遮蔽的全面反抗。
参考文献:
[1]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M]香港:昭明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168–169.
[2]毅真.几位当代中国女小说家[A] 黄人影.当代中国女作家论[C].上海:上海书店,1985.13.
[3][4][5]李有亮.给男人命名[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11、17、109.
姜辉,陕西中医学院人文科学系教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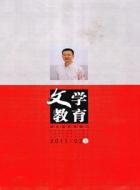
- 心安是吾乡——评周伟的《阳光故乡路》 / 叶立文
- 关于生命的哲学笔记 / 刘洁岷
- 《白雪乌鸦》:联缀性结构与现代性内涵的对接 / 周新民
- 实践教学在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中的建构 / 张芳
- 诗意文学课堂的重寻与呼唤 / 卢艳玲
- 英美文学自主学习探索 / 徐庆宏 常漪
- 新形式下大学语文教学浅论 / 刘红芹
- 提高大学语文课堂教学效果的思考 / 常亮
- 语文课堂教学中人文性的建构 / 高建云
- 我对当前文学的几点思考 / 汪政
- 情感教育在语文课堂减负中的作用 / 白家棚
- 语文教学中和谐课堂的营造 / 栾世堂
- 回家 / 薛荣
- 经验与超验——评薛荣的《回家》 / 李遇春
- 阳光故乡路 / 周伟
- 基于提问的语文教学重点难点突破策略 / 寿飞鸽
- 大学写作课教学法举隅 / 黄桂婵
- 当代回族文学创作与宗教 / 刘波
- 合作交流是提高课堂效率的捷径 / 林惠兰
- 大学写作课教学法举隅 / 黄桂婵
- 当代回族文学创作与宗教 / 刘波
- 学生学习文言文恐惧心理的克服 / 邓尚玲
- 情境创设与文学教育 / 陈灵彩
- 谈谈作文的细节描写 / 方锦娣
- 诗歌教学与诗词格律 / 李丽
- 新课标下现代诗歌教学探讨 / 马岽丽
- 作文材料漫谈 / 尹立新
- 高考作文探究 / 张金虎
- 高中语文新课程背景下的有效教学 / 李鹏
- 记叙文中字词的品析 / 王红霞
- 中学作文教学改革刍议 / 张旺雪
- 提高作文水平三部曲 / 张强
- 作文教学浅探 / 王红伟
- 提高作文讲评课实效性的策略 / 姚毅
- 记叙文写作中的走笔运巧 / 邵军花
- 《社戏》中“平桥村”解读 / 李林
- 《文心雕龙.神思》中的文学观刘 / 刘晶
- 从唐僧师徒的皈依路看《西游记》中的佛教思想 / 牟海超
- 浅谈文本开发的途径 / 黄美萍
- 杜甫《阁夜》中“人事音书漫寂寥”新解 / 曹天璞
- 《红楼梦》中晴雯的形象分析 / 赵明利
- 碾坊与渡船:《边城》不可忽视的两个意象 / 林忠港 朱晓林
- 浅析《背影》中的情感流程 / 余松涛
- 试论虹影博客身份形象的构建 / 陈瑜
- 孙犁小说中的联想艺术 / 邢宗和
- 试析三岛由纪夫《春雪》的叙事策略 / 王雪梅
- 《快乐王子》:诗意的唯美与现实的悲悯 / 吴涛
- 契诃夫《苦恼》以小见大的构思特点 / 张保明
- 浅谈王维山水诗的绘画美 / 胡富存
- 评佩里.安德森的《思想的谱系:西方思潮左与右》 / 陈桃霞
- 《浣纱记》叙事结构分析 / 吕维洪
- 《梦游天姥吟留别》的三美 / 曾菡召
- 评李遇春的《中国当代旧体诗词论稿》 / 郑祥琥
- 《所罗门之歌》中彼拉多.戴德的形象分析 / 李宝峰
- 中国古典山水田园诗浅探 / 洪季平
- 现代女性小说中的女性意识发展初探 / 姜辉
- 论惠特曼《草叶集》对郭沫若《女神》的影响 / 张浩
- 提高听课有效性的探究 / 袁湘英
- 谈古典词风的一主二变 / 刘福君 王幸
- 探析道家思想对心理咨询的启示 / 梅洪舟 范晓玲
- 浅说诗人与驴 / 刘翠华
- 新课程标准下的语文作业设计 / 董月萍
- 武汉地名的语言文化考察 / 何余华
- 以特色活动为载体优化新生代环保行为 / 叶季莉
- 从两大堕落主人公形象谈《失乐园》中的自由观 / 王雅雯
- 浅论《短歌行》的内容及其写作艺术 / 何平滚
- 论亦舒的写作姿态 / 王雷雷
- 论古希腊与先秦时代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 / 张晶
- 谈谈幼儿故事的趣味 / 徐虹
- 挖掘农村孝文化带来的和谐经 / 罗静荣
- 以《战地野餐》为例试析戏剧在教育中的作用 / 朱毅
- 对语文新课程改革的思考 / 韩晶晶
- 《月亮和六便士》与毛姆的哲学思想 / 刘 哲
- 从语言与文化关系的角度浅析外来词汇 / 常漪
- 语文教学中的情感教育策略 / 吴玉霞
- 从《芭蕉之旅》的英译看美国文化的本真吁求 / 熊莺
- 美国人屠杀印第安人背后的真相 / 张林艳
- 视译中存在的困难及应对策略 / 王宇珍
- 散文两章 / 龚玉林
- 割不断的情丝 / 刘协庭
- 信息18则 / 舒坦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