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11年第12期
ID: 156404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11年第12期
ID: 156404
语文教师应重视自身人文素养
◇ 孙亦涛
内容摘要:《语文新课程标准》指出人文素养包涵以下内容:“在语文学习过程中,培养爱国主义情感、社会主义道德品质,逐步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正确的价值观,提高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作为一名语文教师要用自身的人文素养去滋养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语文教师自觉地将文学作品融入自己的生命体验中,以自己对生命的感悟扩展学生的疆界,充实学生的内涵,丰富学生的认识。当教师深情投入、真情流露的时候,学生才能受到文化感染,文化熏陶。
关键词:精神 人文素养 感染
《语文新课程标准》指出人文素养包涵以下内容:“在语文学习过程中,培养爱国主义情感、社会主义道德品质,逐步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正确的价值观,提高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认识中华文化的丰厚博大,吸收民族文化智慧。关心当代文化生活,尊重多样文化,吸取人类优秀文化的营养。”显然,这段话指出了注重利用传统文化培育学生人文素养是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
古语云:经师易得,人师难求。在中国古代,特重“教化”二字,根据近代思想家魏源的解释:“教以言相感,化以神相感。”“教”与“化”相互为用、相得益彰,“有教而无化,无以格顽;有化而无教,无以格愚。”可见,无言之教、人格感化的力量是难以估量的。
作为一名语文教师,我们不能仅仅着眼于知识技能的提高。因为学生素养获得不是通过说教和灌输获得的,而是让学生置身于文学情境中自我体验、相互影响,以素质培养素质、以灵魂塑造灵魂,从而使人文素养丰盈起来。正如苏霍姆林斯基说的那样,“人只能由人来建树”,所以在教学中,教师要先用自身的人文素养去滋养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
语文作为一门人文性极强的学科,需要心灵的自由参与,需要思想的大胆碰撞,需要智慧的平等交流,更需要情感的积极投入。而“教师不仅是传播者,而且还是模范。看不到语文妙处及其威力的教师,就不见得会促使别人感到这门学科的内在刺激力。”
成功的语文教育应是教师用对生命的热爱唤起学生对生命的热爱,激发他们生命的活力。“要散布阳光到别人心里,先得自己心里有阳光。”所以说,语文老师应当自觉地将文学作品融入自己的生命体验中,以自己对生命的感悟扩展学生的疆界,充实学生的内涵,丰富学生的认识。语文老师如果照本宣科,人云亦云的分析和练习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把好端端的文章“碎尸万段”,要学生用“死记”答案来代替“记诵”活生生的文章本身。“读书人”成了“习题人”。被统一到一个“标准”答案中的学生就不可能有激情和个性。
另外,文本教学中如果把语言文字从文学精神中抽离出来,如同对剥离了皮肉去欣赏文本,那么文本还有何美丽、润泽可言?文学精神是贯穿语文教育的灵魂,是最精致、最精微、最有生气、最直指人心的。所以语文教师只有先提升自己的文化品位,自觉地将文学作品融入自己的生命体验中,用心体验个中滋味:踏着雪莱拜伦的足迹,咀嚼他们的忧伤和欣喜;神游但丁奇妙的《神曲》世界;陶醉于庄子“天人合一”的和谐自然的境界;才能使自身的人文素养去滋养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
例如苏教版必修五的《逍遥游》,这是高中课本种较难理解的一篇文章,学生的阅历限制他们的接受能力和理解力。庄子提出的道家的理想人格——至人、神人、圣人,如宋荣子“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逍遥游》);列子“御风而行,冷然善也”(《逍遥游》);老子“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养生主》);他们分别代表着“圣人”、“神人”和“至人”。通读《庄子》方能理解庄子为什么“游心”于道德,轻视功名利禄。这种人生态度,即使在今天也是十分可取的。与其说它是自欺欺人的自我安慰,毋宁说是对独立人格的追求;与其说它是一曲没落阶级的挽歌,毋宁说是一曲乱世中的知识分子的气节歌。
“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在道家的观念中,人的生命本性原如赤子,道德醇厚,仅仅因为后天世俗的各种欲望、人为机巧,才使得生命本性被搅乱。所以老庄力图使人们的心灵回到一种淳朴自然的“赤子之心”。于是道家反理性、反功利、讲养生、“齐物”、“逍遥”。当然,这其中有消极的一面。但是在那个人人自危的社会中,就连孔子都谆谆告诫他的学生“危邦不入,乱邦不居”,“邦有道则现,无道则隐”(《论语》)。庄子对现实世界感到心灰意冷、悲观绝望,对矛盾采取回避和顺应的态度,甚至在这种回避与顺应中获得逍遥自适。庄子的这种无为混世是迫不得已的,在他的内心深处应该始终保持着人格的独立,“彼且为婴儿,亦与之为婴儿,彼且为无町畦,亦与之为无町畦,彼且为无崖,亦与之为无崖。”因此,庄子认为“死生、存亡、穷达、富贵、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徳充符》)命运的安排任何人都无法抗拒,“不知其所以然而然,命也。”(《达生》)“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秋水》)既然人不能改变命运,那就应该安之若素,不为所动,保持内心的宁静和愉悦,进而在对命运的消极顺从中获得一种消极的达观人生,在真实的人生中超越世俗,在现实惨淡的生活中追求超越的人生境界,“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只求自我内心精神的逍遥自由,诚然是一种避世主义的自我精神安慰,但也是庄子无法超越的时代局限。
可是,庄子对“逍遥游”的大胆热烈、执着飘逸的追求,在物欲横流、人为物役的现实世界之外为人们寻找到一个宁静的心灵港湾,为个体生命诗意的生存提供了契机,抚慰了一代又一代失意文人的心灵,使他们在痛苦困惑中还能以表面的逍遥自适,表现出一丝乐观和委婉的反抗:“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
由此观之,庄子恢宏的气势,恣纵的精神,又岂是用“宿命”二字就能扫入“历史垃圾堆”的?试想,如果语文教师自己不具备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如何能传递文化。
所以只有当教师深情投入、真情流露的时候,学生才能受到文化感染,文化熏陶。点点滴滴地积累,潜移默化地渗透,学生的精神得到贯注,思想随之净化,行为获得矫正,文化得以熏陶,人文素养才能提高。
孙亦涛,教师,现居江苏徐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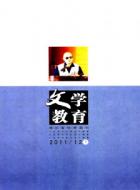
- 古道热肠的陈竹教授 / 马元龙
- 记忆光线 / 李汉荣
- 夏腊初散文创作述评 / 汤天勇
- 伟大的风格隐藏在看不见的地方 / 和歌
- 从《美狄亚》看欧里庇得斯的道德关怀 / 唐廷碧
- 夏衍话剧创作的艺术风格 / 陈玉焕
- 教育素养的提升在于转换自身角色 / 孙德建
- 小议胡风的现实主义文艺观 / 曾小忙
- 语文教学中如何拓展人文内涵 / 王丽华
- 萧红小说散文化倾向刍议 / 黄启祥
- 中西传统文化中关于言意问题的主要观念 / 熊安黎
- 课堂导入艺术初探 / 赵旭
- 文学作品中的“肥”与“瘦” / 彭锐
- 语文教学中的语言艺术 / 张志强
- 接受美学观照下的初中散文教学 / 虞志江
- 语文教学中的情感态度及其培养 / 施贤芬
- 将现代教育技术运用于语文教学 / 高二静
- 高中语文探究教学例说 / 吴书兰
- 语文课堂教学内容确定的基本原则 / 崔沛泉
- 教学中怎样培养语感 / 郭银云
- 职校艺术类学生的美学素质培养 / 沈强
- 隐性教材对语文教学的促进作用 / 高德利
- 赏识教育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 / 单朝阳
- 学生概括能力培养的实施途径 / 王安顺
- 语文教学中的审美教育 / 胡华青
- 把语文选修课上得更有语文味 / 胡丽丽
- 高中文言文教学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 李奕
- 课堂提问艺术浅析 / 戈志国
- 小组合作学习活动方式研究 / 章志辉
- 中职语文课堂教学有效设问策略 / 赵华
- 美术文化校本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实施 / 张映红
- 在课堂教学中应加强情感教育 / 陈静雯
- 网络背景下的大学英语听力教学研究 / 贺岚
- 语文作业的最优化设计 / 王尉华
- 创设学习情境提高教学效率 / 陆华奎
- 《白鹿原》中背离的两兄弟命运分析 / 张静
- 让初中生走好学语文的第一步 / 时秀丽
- 语文自主学习漫谈 / 刘保
- 提高文言文课堂教学有效性刍议 / 颜东仕
- 《史记》中项羽结局的描写艺术 / 魏佳
- 《给李风叔叔帮忙》的讽刺性 / 易麟
- 教出文学作品的语文味 / 丁维华
- 语文课堂中的生命化教学 / 顾素燕
- 品读郁达夫的《江南的冬景》 / 朱利超
- 语文教师如何变主讲为主持 / 舒红梅
- 祥林嫂死因探析 / 王成才
- 怎样把记叙文写得充满人文情怀 / 李涛
- 文言文教学要四看 / 孙彩云
- 中学生写作情感缺失及其引导措施 / 陈建昌
- 给学生插上想象的翅膀 / 杨东
- 多媒体资源在教学中的利用 / 赵烨
- 高中作文思维创新能力的培养 / 邵志芳
- 作文教学中如何渗透心理健康教育 / 覃婉露
- 《河岸》的另一种解读 / 韩爱强
- 中学作文教学之浅见 / 彭晨光
- 作文批改的尝试与体会 / 杨明
- 从细微主义看《巴黎瞬间》的写作特色 / 张丹
- 作文因“我”而精彩 / 戴兆坤
- 《哈姆莱特》中的女性形象 / 王安湉 颜清
- 论粤山区中职语文教学中的朗读 / 李万红
- 让学生乐于写作文 / 焦大磊 刘月梅
- 如何提高阅读教学质量 / 王成霞
- 体验阅读教学的引导策略 / 胡小林
- 语文教学中的“滑过现象” / 卢跃武
- 媒介文化的审美视域反思 / 宋园园 王亮
- 关于L2阅读推理框架的认知研究 / 王金玉
- 做一个反思型的教师 / 曹辉
- 语文课堂教学有效性的几点思考 / 张春英
- 论大学语文课程性质思考中的两个维度 / 冯文丽
- 文章类读中点与文的选择 / 任敏
- 漫话阅读教学的新理念 / 隆溢清
- 也谈字母词的使用和规范问题 / 宋美凤
- 活动单导学课堂案例分析 / 钱萍
- 《沁园春.长沙》课堂设计 / 夏福英
- 高职英语教学现状之反思 / 杨席珍
- 古诗鉴赏例谈 / 李红兵
- 多媒体技术与语文教学 / 闫冬丽
- 语文教师应重视自身人文素养 / 孙亦涛
- 用心温暖每个学生 / 许桂花
- 诗歌鉴赏答题技巧 / 李其明
- 高校招生制度国际横向比较研究 / 王樱南
- 让学生不再谈“语”色变 / 张相龙 李中发
- 教师与学校文化建设 / 蔡昌洋
- 反思当下的中学语文教学 / 胡登峰
- 释《海国图志》中的“泥封告绝” / 张惠民
- 论文学与音乐之相同点 / 王渊
- 现行高中语文教学的得与失 / 黄桥生
- 说说“不”和“没” / 李鸿燕
- 语文之路在脚下 / 王宗群
- 提高语文课堂吸引力的思考 / 陈玉兰
- 如何解决农村小学生的唱读问题 / 金玉芳
- 批评的艺术 / 张旺生
- 深切怀念我的母亲 / 蒋从明 李利青
- 红楼中的悲情女子 / 刘莉
- 图书文化对教育的强力推助 / 李发兵
- 课程改革与校长的角色 / 张发生
- 小细节见大精神 / 李冬霞
- 可爱的清江 / 蔡宝万
- 音乐教学中的审美教育 / 马素萍
- 散文二题 / 杜晨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