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11年第12期
ID: 156326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11年第12期
ID: 156326
古道热肠的陈竹教授
◇ 马元龙
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甚至到硕士博士,在漫长的学习生涯中,想必每个人都会至少遇到一位深刻影响他、令他终生难忘的老师。对于我来说,陈竹先生就是这样一位令我深怀感念的老师。
陈竹先生是一个古道热肠的人,我能在他指导下读硕士研究生,纯粹因为一种机缘。1993年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石棉县中学任高一年级语文教师。学生不多,一个年级只有两个班。学生都非常可爱,十分聪明,而且好学。可我当时正年轻,一心向往着外面的世界,恨不得立刻插上翅膀飞出去。但是我没有翅膀,飞不出去;通向外面世界的路只有一条,一条在群山之间、峡谷之中蜿蜒盘旋的简陋而漫长的公路;而要真正踏上这条道路,考研在当时似乎是最为可行的选择。
报考研究生并不自由,必须获得我所在学校校长的书面认可。我工作不满一年就想考研逃跑,校长当然不会同意。我最终还是偷偷报考了华中师范大学文艺学的研究生,并且上线了。然而事情并未完结,因为没有得到校长的同意,教育局无法把我的档案投递到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处,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处也就无法为我发录取通知。更加糟糕的是,如果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处不能在七月底之前收到我的档案,我将自动失去录取资格。心急如焚之下,我不知怎么竟然要到了此前素昧平生的陈竹老师的电话。在我带着焦虑、急切的心情向素昧平生的陈老师陈述完我当时面临的困境后,陈老师给予了我热情的安慰,并指点我妥善协调,尽快把档案邮寄过去。后来我得知,为了保证我能到华中师范大学读研,陈竹老师亲自到研究生处陈述了我的情况,并请求研究生处把我的投档期限延长到八月底。因为陈老师的鼎力相助,我终于如愿以偿地来到了华中师范大学攻读研究生。
华中师范大学是一所美丽的学校,校园建设虽不精致,部分地方甚至还是荒坡野地,但别有一种朴素和宁静的韵致。学校里颇有许多高大的梧桐树和香樟树,还有一个小小的梅园,每逢岁末年初,一场飘飘洒洒的雪下来,红梅白梅便纷纷绽放,散发出沁人心脾的芬芳。但桂子山上最富盛名的是桂树,尤其是在校园中心区域,所有道路两旁全是挨挨挤挤的高大桂树。金秋时节,三五之夜,明月在天,清风徐来。此时在盛开的桂树下缓步幽行,真能领略到“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的诗意。
华中师范大学的美不仅限于校园风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对大学来说是一个相对祥和的时期。高校尚未产业化,量化刻板的管理模式也尚未盛行,老师不必为申报课题而绞尽脑汁、费尽心力,除了致力学术研究,可以把大部分精力放到学生的学习上。至于学生,因为就业压力不大,故不必为工作操心劳神,学习听课全凭兴趣,学术的魅力得到了保留。虽然大家读研的动机不一定都是为了学术,但听课、读书还是非常认真。当时高校也未扩张,博士研究生尚且稀有,硕士研究生也为数不多,我们文艺学一届的同学总共也只有四个。故而师生之间不仅交往比较充分,而且彼此还有一种亲切融洽的感情。
因为入学的曲折和困难,因为这份困难和曲折造就的机缘,我顺理成章地成为了陈竹老师的学生,在他的指导下攻读文艺学硕士,彼此之间的联系自然就很密切了。陈竹老师是一个极有个性的人,对学术心存敬畏,对自己严格要求,但对学生,他展示的不是严峻的一面,相反是和蔼的一面。我从未见他严厉批评过哪一个学生,即使愚钝顽劣如我之辈,偶有批评,也非常含蓄委婉,疾言厉色从未有过。研究生二年级时,陈老师给我们开了一门古代文论的课,有一次,无知无畏的我在课堂上毫无理据地对他的某一观点表示异议,令他颇为不悦。然而即便如此,他也只是一时有些气恼而已,过后丝毫芥蒂不存于心。陈老师授课比较随性,颇有魏晋风度。暮春三月,草长莺飞,天气和暖之时,他有时会把大家从教室里带到草坪上,师生席地而坐,谈笑风生。
陈老师对学生永远是关爱,有时你甚至会觉得他关爱得有些糊涂。我常常看见有些学生为考研直接向他求助,他一律认真指点,仿佛每个来拜访他的学生都是有志于学术的笃学之士,其实许多人考研就像我当初一样,只是为了改变一下自己的处境而已,哪里谈得上有志于学术。如果只是想改变自己的处境而求教于他,也可以理解,但其中更多人的目的其实更加简单:希望陈老师能向他们暗示考题。一旦这种直接目的不能得到满足,这些人大多就不再登门了,但陈老师似乎对此还毫不知情。陈老师就是这样,在他看来,仿佛学生都是单纯可爱的。不过,这种糊涂倒反衬出了他的单纯和可爱。
陈老师的生活非常简单,读书、研究是他生活的绝对主题,除了偶尔外出访友,他一直把自己禁闭在那间小小的书斋中。我从未见过他打牌下棋,惟一的嗜好可能就是一口小酒。据师母说,他似乎每餐必饮,但仅限一两而已,绝不过量。由此可见,他其实也是一个极为理性的人。
除了每周上课相见,我每月大概会去他家一次。陈老师住在华中师范大学北区一栋比较古旧的楼里,楼下墙角处有腊梅一树。每年岁末,梅花未开时,腊梅已经争先吐蕊。陈老师家在五楼,居室不大,或者应该说比较局促。我1994年到华中师范大学读书时他已经在那里居住有年,如今17年光阴悠悠而去,华中师范大学的教师员工,即使是那些非常年轻的教工都已经乔迁进了宽敞明亮的华居,而垂垂老矣的他仍然蛰居陋室,日日与青灯古籍为伴,思之能不令人浩叹!
我和陈老师聊天,除了汇报自己的读书心得或者困惑,偶尔也拉些家常闲话。有时谈兴上来,师母必留饭,我也就却之不恭了。硕士研究生最后一年,我草草完成论文初稿之后,为求职而外出实习,陈老师家便去得少了。师从陈老师学习的三年转瞬就告结束,但我与陈师的缘分并未结束,因为毕业后我竟然在华师出版社做了编辑。因为工作之故,2003年当陈师把他和曾祖荫教授合著的《中国古代艺术范畴体系》交到出版社时,社长指命我担任这部大作的责任编辑,我自然欣然领命。
陈老师一生致力于中国古代文论思想研究,退休之后依然笔耕不辍。五十年来有著述多种,最为重要的可能是《中国古代剧作学史》(武汉出版社,1999年)和《中国古代艺术范畴体系》(2003年,与曾祖荫合著)。然而在这样一篇随笔性的文字中是不适宜深入评论其学术成就的,而且我也不是评论陈老师学术的合适人选。我虽然是陈老师的学生,但硕士毕业之后忙于工作,加之心思浮躁,无暇于学术;后来虽重新立志读书,但兴趣已经转移到西方哲学、美学和文学理论,对陈老师精研的问题反到越发陌生了。所幸我的学兄黄念然教授既是古代文论领域的专家,而且恰好在其大作《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文论卷》中对陈竹老师的学术成就做出了精当的评论,在此我只能掠人之美聊以塞责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陈老师曾出版过一本篇幅不大的《中国古代气论文学观》。陈师认为,中国古代元气论哲学中内涵三个基本观念:一、以气为造化之本的气本观;二、强调气之运动变化和化育生命的气化观;三、强调一气贯通、顺应自然、天地共感的气感观。陈师认为,以此三大基本观念为内涵的气本论对中国古代诗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直接表现就是围绕着“气”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气论诗学体系,其理论形态又有多种表现。例如,就创作主体而言,有“养气说”,“主敬”说,有“虚静说”,“应感说”;就艺术风格而言,有“阴阳刚柔”说等等。总之,陈师在该著中不仅全面清理了“气”的哲学、美学内涵,还将之上升为诗学理论的元范畴,试图以此建构出一个气论文学观体系。
陈老师的《中国古代艺术范畴体系》(和曾祖荫教授合著)可以视为《中国古代气论文学观》的进一步发展。如果说《气论文学观》还只是尝试围绕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气这一种范畴建构一种理论体系,而《中国古代艺术范畴体系》则表现出了为整个中国古代艺术理论建构一个完整的宏大体系的雄心壮志。此书试图打破中国古代美学“无体系”的传统观念,以道为本,用系统论、心理学等方法来发掘、描述中国古代艺术范畴的潜体系,使其以逻辑的形式得以敞现。
陈老师认为,“道”不仅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元范畴,而且也是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元范畴。大道无形,周流不滞,诗人依于道而游于艺,兴于诗而成于乐。道之显现,于物则为气、为艺、为文,于人则为志、为情、为欲。由此陈师确立了道转化为艺并进而渗透到艺术主体性的层层递进的研究理路,以极强的通观整合能力对中国古代艺术范畴的基本构架和逻辑发展进行了精密的建构,并特别指出,中国古代艺术范畴之转化具有宏观性与微观性高度统一的特点(即不仅表现为大的历史时段之间勾连衔接的宏观性,也表现为同一历史时段内不同发展阶段及不同艺术部类间名同质异的微观性,是宏观与微观之间的高度统一)。
念然兄认为,该著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一、首次提出了中国古代艺术范畴具有层次性、序列性的观点,并对元范畴“道”的确立、深化、哲学意义之嬗变以及“道”向“艺”的渗透之大势作了清晰的描述,从一开始就避免了以往文艺范畴研究中缺乏逻辑出发点、不分主次的毛病。二、著者于古代美学内在理性脉络中去神会古人、推阐义蕴,首次将从先秦至明清的中国艺术范畴的整体运动状况进行了极具理性整合能力的提摄,并藉中国艺术范畴的运动态势首次完整地揭示了中国古代艺术理论形态的基本发展脉络:先秦的文理论→秦汉的文性论→魏晋的文气论→唐代的文意论→宋元的文韵论→明清的文情论。三、除首次对每一具体时代的艺术范畴之发展和演变作了共时性和历时性两个维度上的勾勒,还首次按范畴分级和历史分期两个向度对中国古代艺术范畴的体系作了总体描述,完成了对中国古代艺术范畴内在体系的敞现。四、著者植根于历史理性之中又跳出历史之外,首次对中国艺术范畴体系内的矛盾性、向审美现代性转化的可能性以及与当代学术思维实现对接的潜质等问题作了深入的探究。
陈老师的另一部大作是《中国古代剧作学史》(武汉出版社,1999年)。这本书也可以说是他先前出版的《明清言情剧作学史稿》(华中师大出版社,1993年)的发展。《明清言情剧作学史稿》以情感论为线索剖析了明清两代戏剧编剧理论的发生发展历程,而《中国古代剧作学史》尝试对古代编剧理论进行完整、全面、深入的探讨。陈老师从古代戏剧形态和古代剧作形态的演进等戏剧文化背景入手,探讨了中国古代戏剧观念的进化过程,提出了古代编剧理论是以写意性为基石、由“曲学”、“词学”、“剧作”三大体系为构架的全新观点。陈老师对三大体系中每一体系的首倡者及其演进关系都作了清晰的爬梳,第一次系统地对古代编剧理论作了历史分期上的探讨,并从自己对编剧理论萌芽、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的深入考察出发,向“中国戏剧晚出”这一命题提出了质疑。陈师指出,数千年的剧作学史对剧作的现实发展的启示就在于:“要有牢固的戏剧文化市场观念”;应该“发挥主体性在编剧中的主导地位”。可以说,这些观点从剧论历史的发展中自然贯串而出,不仅令人信服,同时也值得戏曲理论界深刻反思。
陈老师对学术的虔诚和勤勉是毋庸置疑的,他所取得的学术成就仍然有待学术界予以必要的关注。作为陈老师的不肖学生,我固然不是评论其学术成就之得失的合适人选,但我也并不想一味为陈老师唱赞歌。事实上,我一直认为陈师的学术研究在两个方面存在值得商榷的问题:其一是过于强烈的唯理论倾向,其二是过于偏爱宏大叙事,而这两个方面在陈师那里又是纠结在一起的。强烈的唯理论倾向使得陈师的著作演绎多于考证,逻辑胜于历史;偏爱宏大叙事使得陈师的路径过于本质主义和中心主义,有亏于文学和文学理论的历史性。文学不是生活的彼岸,它与政治、经济、宗教、阶级、种族、性别等因素密切相关。写作既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实践,又是对意识形态的破坏。写作一方面生产了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也是一种身体的享乐过程。中国古代诗学对此并非全然无知,但缺乏深入细致的思考。陈老师的学术研究如果能在这些方面做更多的挖掘、分析和阐释,就更加完满了。虽然在我看来,陈师的研究不无值得商榷之处,但相比今天那些几乎把全部精力都耗费在跑课题搞经费的学术明星来说,陈老师的风骨、他对学术的虔诚是十分令人钦佩的。
2005年8月,我整月都在为到中国人民大学做博士后研究而办理各种繁琐而令人痛苦的手续。一天,在华中师范大学校医院门口遇见陈老师和师母,问及近况,我简短叙述了自己的打算。陈老师听后,知道我这一去就算是离开武汉了,立时面色有些凄然。见我当时正忙碌,无暇长谈,说改天请我吃饭为我饯行。第三天果然打来电话,约定下午到学校餐厅小饮一杯。那一次是我们师生第一次在餐馆吃饭,彼此都有些伤感,但叙谈还算从容。北来之后,见面的机会更少了,除了两次到武汉开会,我去他家拜访之外,平时只能打打电话。上次在武汉见他,精神尚好,只是肥胖了一些。
陈老师性格耿介,嫉恶如仇,他在日常生活中也许有些糊涂,但在大是大非上毫不苟且,具有一个真正知识分子的良知。然而终不免偏执,不易与人沟通。退休后,他的生活更加封闭,又不能忘怀世事,所以每多愤激之辞。作为学生,我甚至希望他现在少读一些书,少关注一些世事,多出去与人交流一下,散散步,打打牌。忧国忧民之事,肉食者尚不能谋之,已入桑榆晚景的他,又何必介怀,徒增烦恼而已。
陈老师家楼下有一条小路,路旁两边满是桂树。有一次,秋天,桂花盛开的季节,从陈老师家出来,已是夜晚。当时夜宇澄澈,明月皎洁;月华如水,清香沁人。独自走在那条小路上,走在桂花的芬芳里。看看天上的月,看看地上的影,一个人,心境一如月夜空明。不知何时能够再在那样的月与夜,那样的花与影中独自走过。
马元龙,中国人民大学教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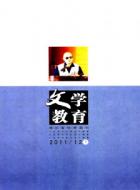
- 古道热肠的陈竹教授 / 马元龙
- 记忆光线 / 李汉荣
- 夏腊初散文创作述评 / 汤天勇
- 伟大的风格隐藏在看不见的地方 / 和歌
- 从《美狄亚》看欧里庇得斯的道德关怀 / 唐廷碧
- 夏衍话剧创作的艺术风格 / 陈玉焕
- 教育素养的提升在于转换自身角色 / 孙德建
- 小议胡风的现实主义文艺观 / 曾小忙
- 语文教学中如何拓展人文内涵 / 王丽华
- 萧红小说散文化倾向刍议 / 黄启祥
- 中西传统文化中关于言意问题的主要观念 / 熊安黎
- 课堂导入艺术初探 / 赵旭
- 文学作品中的“肥”与“瘦” / 彭锐
- 语文教学中的语言艺术 / 张志强
- 接受美学观照下的初中散文教学 / 虞志江
- 语文教学中的情感态度及其培养 / 施贤芬
- 将现代教育技术运用于语文教学 / 高二静
- 高中语文探究教学例说 / 吴书兰
- 语文课堂教学内容确定的基本原则 / 崔沛泉
- 教学中怎样培养语感 / 郭银云
- 职校艺术类学生的美学素质培养 / 沈强
- 隐性教材对语文教学的促进作用 / 高德利
- 赏识教育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 / 单朝阳
- 学生概括能力培养的实施途径 / 王安顺
- 语文教学中的审美教育 / 胡华青
- 把语文选修课上得更有语文味 / 胡丽丽
- 高中文言文教学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 李奕
- 课堂提问艺术浅析 / 戈志国
- 小组合作学习活动方式研究 / 章志辉
- 中职语文课堂教学有效设问策略 / 赵华
- 美术文化校本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实施 / 张映红
- 在课堂教学中应加强情感教育 / 陈静雯
- 网络背景下的大学英语听力教学研究 / 贺岚
- 语文作业的最优化设计 / 王尉华
- 创设学习情境提高教学效率 / 陆华奎
- 《白鹿原》中背离的两兄弟命运分析 / 张静
- 让初中生走好学语文的第一步 / 时秀丽
- 语文自主学习漫谈 / 刘保
- 提高文言文课堂教学有效性刍议 / 颜东仕
- 《史记》中项羽结局的描写艺术 / 魏佳
- 《给李风叔叔帮忙》的讽刺性 / 易麟
- 教出文学作品的语文味 / 丁维华
- 语文课堂中的生命化教学 / 顾素燕
- 品读郁达夫的《江南的冬景》 / 朱利超
- 语文教师如何变主讲为主持 / 舒红梅
- 祥林嫂死因探析 / 王成才
- 怎样把记叙文写得充满人文情怀 / 李涛
- 文言文教学要四看 / 孙彩云
- 中学生写作情感缺失及其引导措施 / 陈建昌
- 给学生插上想象的翅膀 / 杨东
- 多媒体资源在教学中的利用 / 赵烨
- 高中作文思维创新能力的培养 / 邵志芳
- 作文教学中如何渗透心理健康教育 / 覃婉露
- 《河岸》的另一种解读 / 韩爱强
- 中学作文教学之浅见 / 彭晨光
- 作文批改的尝试与体会 / 杨明
- 从细微主义看《巴黎瞬间》的写作特色 / 张丹
- 作文因“我”而精彩 / 戴兆坤
- 《哈姆莱特》中的女性形象 / 王安湉 颜清
- 论粤山区中职语文教学中的朗读 / 李万红
- 让学生乐于写作文 / 焦大磊 刘月梅
- 如何提高阅读教学质量 / 王成霞
- 体验阅读教学的引导策略 / 胡小林
- 语文教学中的“滑过现象” / 卢跃武
- 媒介文化的审美视域反思 / 宋园园 王亮
- 关于L2阅读推理框架的认知研究 / 王金玉
- 做一个反思型的教师 / 曹辉
- 语文课堂教学有效性的几点思考 / 张春英
- 论大学语文课程性质思考中的两个维度 / 冯文丽
- 文章类读中点与文的选择 / 任敏
- 漫话阅读教学的新理念 / 隆溢清
- 也谈字母词的使用和规范问题 / 宋美凤
- 活动单导学课堂案例分析 / 钱萍
- 《沁园春.长沙》课堂设计 / 夏福英
- 高职英语教学现状之反思 / 杨席珍
- 古诗鉴赏例谈 / 李红兵
- 多媒体技术与语文教学 / 闫冬丽
- 语文教师应重视自身人文素养 / 孙亦涛
- 用心温暖每个学生 / 许桂花
- 诗歌鉴赏答题技巧 / 李其明
- 高校招生制度国际横向比较研究 / 王樱南
- 让学生不再谈“语”色变 / 张相龙 李中发
- 教师与学校文化建设 / 蔡昌洋
- 反思当下的中学语文教学 / 胡登峰
- 释《海国图志》中的“泥封告绝” / 张惠民
- 论文学与音乐之相同点 / 王渊
- 现行高中语文教学的得与失 / 黄桥生
- 说说“不”和“没” / 李鸿燕
- 语文之路在脚下 / 王宗群
- 提高语文课堂吸引力的思考 / 陈玉兰
- 如何解决农村小学生的唱读问题 / 金玉芳
- 批评的艺术 / 张旺生
- 深切怀念我的母亲 / 蒋从明 李利青
- 红楼中的悲情女子 / 刘莉
- 图书文化对教育的强力推助 / 李发兵
- 课程改革与校长的角色 / 张发生
- 小细节见大精神 / 李冬霞
- 可爱的清江 / 蔡宝万
- 音乐教学中的审美教育 / 马素萍
- 散文二题 / 杜晨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