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11年第12期
ID: 156337
文学教育下半月 2011年第12期
ID: 156337
中西传统文化中关于言意问题的主要观念
◇ 熊安黎
内容摘要: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强调妙悟体认、不甚依赖言词的传统和言意观。中国人都善于从宏观整体角度把握问题的实质,一旦这种实质被个人所感受到,通常就不会纠缠于文字的表述。相比起其它文字系统,尤其是力求用精确明晰的“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s)语言表述思想的字母文字系统,中国人在言与意、能指与所指、表达与思想之间必然出现模糊、不确定、不可言说的特点,与西方文化中传统的言意观形成了差异。
关键词:中西传统文化 言意 主要观念
“大音希声”、“言不尽意”、“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得意忘言”,这些表达方式历来为国人熟知,其中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种强调妙悟体认、不甚依赖言词的传统和言意观。无论是生活的实践还是文艺的创作,无论是理论的提出还是处世的哲学,中国人都善于从宏观整体角度把握问题的实质,一旦这种实质被个人所感受到,通常就不会纠缠于文字的表述。这样一来,相比起其它文字系统,尤其是力求用精确明晰的“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s)语言表述思想的字母文字系统,中国人在言与意、能指与所指、表达与思想之间必然出现模糊、不确定、不可言说的特点,这与西方文化中传统的言意观形成了极大的差异。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言意观
中国人历来认为语言只是表意的工具。如果说从老子“美言不信”、“大音希声”开始形成了中国人对语言持怀疑态度的传统,并在庄子的“言不尽意”、“得意忘言”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那么魏晋玄学创始人王弼则更为中国人“得意忘言”作出了经典的解释。王弼以《庄子·外物》所说的“得意忘言”和“得意忘象”去解说《易·系辞》所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这里有两层意思,其一是以“忘象”、“忘言”要人解《易》不滞于名言,而体会其中所蕴之义。其二是王弼将言、象说成得意的工具,“得意忘言”如同“得兔忘蹄”、“得鱼志筌”,蹄(套索)筌(竹篓)为工具,而得到兔鱼之后,则可弃置不用;而言、象为得意工具,得到意,言、象亦可弃置不用。王弼谓言、象为工具,只用以得意,而非意本身。故不能以工具为目的,若执着于言、象,则反失本意。(汤一介,1993:76)这段引述清楚地说明了古人对意、象及言的关系的理解,正因为明确了言是作为得意的工具使用,所以一旦得意,则言也就可以弃之忘之了。
中国人认为涉及本体论、宇宙观的概念通常是“能言而不言”的。孔子《论语·阳货》曾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冯友兰先生就“天何言哉”曾有过评说,他说:“以天不言为一命题,即含有天能言而不言之意,否则此命题为无意。如吾人不说石头不言,桌子不言,因石头桌子,本非能言之物也。”他主张孔子所言之天为“有意志”的“主宰之天”,既有意志,则必能言,只是它不言而已。老子的无形“大道”无疑也是“能言而不言”者,因为老子说“道可道”,表明了“道”是一种可以言说的,但是一旦言说出来,也就是“非常道”,所以“道”也是“能言而不言”的。禅宗的“第一义不可说”,但是佛又是随处可见,“郁郁黄花莫非般若,青青翠竹皆是法身”,也都是所谓“能言而不言者”。可见在中国文化中所表现的大智、真知、要义等抽象的直觉的理性观念,莫不属于“能言而不言者”的范畴。
二.西方传统文化中的言意观
古希腊哲学作为西方文化的源头之一,产生了西方诗学话语体系的基本范畴。柏拉图在《斐德罗》篇中转引苏格拉底的话说:“我们会认为那些拥有正义、荣耀、善良一类知识的人……不会看重那些用墨水写下来的东西,也不会认真用笔去写那些既不能为自己辩护,又不能恰当地体现真理的话语。”语言无法传达真理,原因就在于一切诗人都只是摹仿者,无论是摹仿德行,或是摹仿他们所写的一切题材,都只是得到影像,并不曾抓住真理。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看来,个体的语言不能完全传达绝对理念。而稍后的亚里斯多德却认为史诗、悲剧和喜剧“都凭借节奏、话语和音调进行摹仿”,不仅如此,他还认为在这种摹仿艺术中“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诗人的职责不在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在这个意义上说,亚里斯多德认为语言是可以达到对具有普遍性的绝对理念的认知的。其实,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最终又殊途同归,因为在他们的诗学观念中都意识到语言的存在是为最高理念的传达服务的,柏拉图也意识到诗人一旦有神灵凭附在身,就能传达那最高的真理。自古希腊以来西方诗学都力图在强化语言明晰化的基础上实现对意义的客观性的追求,而这一点发展到后来的古典主义诗学、启蒙主义诗学那里,语言对意义的理性架构都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其深层的文化根源就在于西方世界对客观实在的逻各斯中心的执着和肯定。
到了二十世纪上半叶,密布在西方文论话语体系中的核心观念就是语言中心论的转向。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为语言学界而且为文学批评界引来了一场被称作是“哥白尼式的革命”。他认为文本的意义是由语言本身在一个纵横交错的结构关系网中建构的,在语言中,任何一个符号的意义都取决于它与前后上下各符号构成的差异和对立。很快这一观点引发了西方艺术界的结构主义革命,“结构主义宣布:说话的主体并非控制着语言,语言是一个独立的体系,‘我’只是语言体系的一部分,是语言说我,而不是我说语言。”(杰姆逊,1985:28)结构主义试图确立语言的中心地位,进而认为语言规定着人的思想,语言书写着历史,语言创造着意义。然而这种仅仅由语言建构起来的意义系统到底是对文学价值的衍生还是对文学的再次囿困,的确值得我们深思。正如伊格尔顿在评价结构主义时说到:“结构主义在括起真实客体的同时也括起了人类主体。正是这样一个双重倾向限定了结构主义研究的课题。作品既不涉及一个作家,也不是个别主体的表现,二者都被挡开了,剩下的悬空在二者中的东西只是一个规则系统。”(伊格尔顿,1986:40)从这段评述中我们看到结构主义的缺憾就在于把文本的意义挤入了语言的牢笼,忽视了文本外更广阔的意义空间,在片面推崇语言的理性建构的基础上,因为忽视文学的感悟式体验最后只剩下一堆抽象的认知模式。
由此看来,与中国传统思想相同的是,西方学者也认识到言意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有时也会产生言不及意的情况,然而,与中国传统思想不同,西方学者认为语言的价值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工具和中介作用,而是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价值中心地位,从语言对绝对理念的再现到二十世纪语言转向,没有语言,意义的存在是模糊不清的,他们认为语言之外没有意义的存在,他们需要在语言中使意义明晰化,他们执着于语言对意义的形塑和创造。中国文化指向的是意义的圆融通达,不为有形的语言所束缚,推崇“言不尽意”,力图实现“言外之意”的审美追求;西方文化的“逻各斯中心”,指归在客观的理念世界,它是从语言的本体生发而来,所以语言在西方的文化观念中是第一性的,因此,为了更好的通过语言再现客观的意义世界,西方推崇语言的明晰性和逻辑性。
参考文献:
[1]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M]. 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3]汤一介.国故新知——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诠释(纪念汤用彤先生诞辰百周年论文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4]柏拉图.柏拉图全集[M].王晓朝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5]亚理斯多德.诗学[M].陈中梅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6]康德.判断力批判[M].邓晓芒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7]张隆溪.道与逻各斯[M].冯川译.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8]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M].唐小兵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9]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熊安黎,女,四川外语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2009级研究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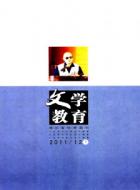
- 古道热肠的陈竹教授 / 马元龙
- 记忆光线 / 李汉荣
- 夏腊初散文创作述评 / 汤天勇
- 伟大的风格隐藏在看不见的地方 / 和歌
- 从《美狄亚》看欧里庇得斯的道德关怀 / 唐廷碧
- 夏衍话剧创作的艺术风格 / 陈玉焕
- 教育素养的提升在于转换自身角色 / 孙德建
- 小议胡风的现实主义文艺观 / 曾小忙
- 语文教学中如何拓展人文内涵 / 王丽华
- 萧红小说散文化倾向刍议 / 黄启祥
- 中西传统文化中关于言意问题的主要观念 / 熊安黎
- 课堂导入艺术初探 / 赵旭
- 文学作品中的“肥”与“瘦” / 彭锐
- 语文教学中的语言艺术 / 张志强
- 接受美学观照下的初中散文教学 / 虞志江
- 语文教学中的情感态度及其培养 / 施贤芬
- 将现代教育技术运用于语文教学 / 高二静
- 高中语文探究教学例说 / 吴书兰
- 语文课堂教学内容确定的基本原则 / 崔沛泉
- 教学中怎样培养语感 / 郭银云
- 职校艺术类学生的美学素质培养 / 沈强
- 隐性教材对语文教学的促进作用 / 高德利
- 赏识教育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 / 单朝阳
- 学生概括能力培养的实施途径 / 王安顺
- 语文教学中的审美教育 / 胡华青
- 把语文选修课上得更有语文味 / 胡丽丽
- 高中文言文教学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 李奕
- 课堂提问艺术浅析 / 戈志国
- 小组合作学习活动方式研究 / 章志辉
- 中职语文课堂教学有效设问策略 / 赵华
- 美术文化校本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实施 / 张映红
- 在课堂教学中应加强情感教育 / 陈静雯
- 网络背景下的大学英语听力教学研究 / 贺岚
- 语文作业的最优化设计 / 王尉华
- 创设学习情境提高教学效率 / 陆华奎
- 《白鹿原》中背离的两兄弟命运分析 / 张静
- 让初中生走好学语文的第一步 / 时秀丽
- 语文自主学习漫谈 / 刘保
- 提高文言文课堂教学有效性刍议 / 颜东仕
- 《史记》中项羽结局的描写艺术 / 魏佳
- 《给李风叔叔帮忙》的讽刺性 / 易麟
- 教出文学作品的语文味 / 丁维华
- 语文课堂中的生命化教学 / 顾素燕
- 品读郁达夫的《江南的冬景》 / 朱利超
- 语文教师如何变主讲为主持 / 舒红梅
- 祥林嫂死因探析 / 王成才
- 怎样把记叙文写得充满人文情怀 / 李涛
- 文言文教学要四看 / 孙彩云
- 中学生写作情感缺失及其引导措施 / 陈建昌
- 给学生插上想象的翅膀 / 杨东
- 多媒体资源在教学中的利用 / 赵烨
- 高中作文思维创新能力的培养 / 邵志芳
- 作文教学中如何渗透心理健康教育 / 覃婉露
- 《河岸》的另一种解读 / 韩爱强
- 中学作文教学之浅见 / 彭晨光
- 作文批改的尝试与体会 / 杨明
- 从细微主义看《巴黎瞬间》的写作特色 / 张丹
- 作文因“我”而精彩 / 戴兆坤
- 《哈姆莱特》中的女性形象 / 王安湉 颜清
- 论粤山区中职语文教学中的朗读 / 李万红
- 让学生乐于写作文 / 焦大磊 刘月梅
- 如何提高阅读教学质量 / 王成霞
- 体验阅读教学的引导策略 / 胡小林
- 语文教学中的“滑过现象” / 卢跃武
- 媒介文化的审美视域反思 / 宋园园 王亮
- 关于L2阅读推理框架的认知研究 / 王金玉
- 做一个反思型的教师 / 曹辉
- 语文课堂教学有效性的几点思考 / 张春英
- 论大学语文课程性质思考中的两个维度 / 冯文丽
- 文章类读中点与文的选择 / 任敏
- 漫话阅读教学的新理念 / 隆溢清
- 也谈字母词的使用和规范问题 / 宋美凤
- 活动单导学课堂案例分析 / 钱萍
- 《沁园春.长沙》课堂设计 / 夏福英
- 高职英语教学现状之反思 / 杨席珍
- 古诗鉴赏例谈 / 李红兵
- 多媒体技术与语文教学 / 闫冬丽
- 语文教师应重视自身人文素养 / 孙亦涛
- 用心温暖每个学生 / 许桂花
- 诗歌鉴赏答题技巧 / 李其明
- 高校招生制度国际横向比较研究 / 王樱南
- 让学生不再谈“语”色变 / 张相龙 李中发
- 教师与学校文化建设 / 蔡昌洋
- 反思当下的中学语文教学 / 胡登峰
- 释《海国图志》中的“泥封告绝” / 张惠民
- 论文学与音乐之相同点 / 王渊
- 现行高中语文教学的得与失 / 黄桥生
- 说说“不”和“没” / 李鸿燕
- 语文之路在脚下 / 王宗群
- 提高语文课堂吸引力的思考 / 陈玉兰
- 如何解决农村小学生的唱读问题 / 金玉芳
- 批评的艺术 / 张旺生
- 深切怀念我的母亲 / 蒋从明 李利青
- 红楼中的悲情女子 / 刘莉
- 图书文化对教育的强力推助 / 李发兵
- 课程改革与校长的角色 / 张发生
- 小细节见大精神 / 李冬霞
- 可爱的清江 / 蔡宝万
- 音乐教学中的审美教育 / 马素萍
- 散文二题 / 杜晨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