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语文教学与研究·综合天地 2012年第2期
ID: 139533
语文教学与研究·综合天地 2012年第2期
ID: 139533
《天狗》的时代艺术性
◇ 尹基殿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天狗》在郭沫若诗集《女神》,乃至新文学中占据着不可忽略的地位。从思想内容和艺术上,都是新诗歌尤其是革新诗歌的典范。
《女神》诗集突破了旧格套的束缚,创造出了雄浑奔放的自由诗体,在艺术、思想等层面上都为“五四”以后自由诗的发展开拓了新的天地,而这种意识在《天狗》一诗中体现得尤为淋漓尽致。
选材上,作者以“天狗”自喻,精心极致。据《山海经·西山经》载:“又西三百里,曰阴山。……有兽焉,其状如狸而白首,名曰天狗,其音如榴榴,可以御凶。”同时,天狗是古代人们对二郎神杨戬的哮天犬的称呼,它不仅能帮助二郎神降妖除魔,还能吞下整个月亮。这里天狗的“御凶”和“吞月”的形象被作者巧妙的运用并升华了意义,为作者“诗言志”的目的很好地作了服务。
1919年,五四运动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崭新的气象、勃勃的生机。旧传统受到猛烈抨击和批判,新事物得到热烈的崇尚与赞扬。倡导科学与民主,追求个性解放,建设新社会,成为时代的强音。当时诗人正在日本留学,五四运动的消息,给诗人精神上以极大的鼓舞,诗人内心那积蓄已久的爱国热情,如火山爆发般迅速沸腾、燃烧起来。
因而,作者巧妙运用典故和象征手法,借助诗歌的独特形式,大胆而张扬地重造新的艺术形式,把心中的激情自由而有序的爆发出来。“御凶”是为了“破旧”,而“吞月”是为了吸取能量而“立新”。
无破不立。首节中,作者以超乎想象的气魄,把自己比喻成一只“天狗”,将一切旧事物吞噬。把“月”“日”“星球”“全宇宙”吞噬,大胆的力量,叛逆中带着理性。新事物的建立,必须是在废除旧事物的基础上,作者力图将旧事物废除,毁灭,才能致力于在废墟上重建。“破”作为首节,可见作者的激情中带有清醒的革命意识。
力量是基础。第二节中,作者把天狗“吞月”的形象,大胆阐明出来。“立”须有力量。要重建,必须有重建的力量。天狗吞噬一切“光”,就是将能量集中的体现,这种想象超乎了如李白“黄河之水天上来”和“飞流直下三千尺”等众多古典诗歌的意象构取,把全宇宙的力量集于一身,在张扬个性,显示自我的同时,又准确把握时代青年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唯“立”是途。第三节为全文的主体部分,文中的天狗形象一方面“飞奔”“狂叫”“燃烧”;另一方面自我“剥皮”“食肉”“吸血”。飞奔是为革命,四处奔走,不辞辛苦;狂叫是为宣传,救国救民;燃烧是何等激情,革命救国。要革命,要“立”是需要极大的行动,更需极大的牺牲。就像“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一样,作者在认识到“寻找光明”的基础上,也认识到本身来至黑夜。革命,既然来自黑夜,那么自身也当破除,只有毁坏,才有重建。“剥皮”“食肉”“吸血”等破除的行为,是为在灰烬中重生,是作者“凤凰涅槃”的行动,只有觉醒的新人,才能配得上新的世界。
此后,作者的情感已经不由得自己的意志而“爆了”,这种爆炸是爱国热情的喷薄和升华。
从“我便是我了”到“我的我要爆了”,《天狗》中个性形象获得充分张扬而充满的力量是诗人在五四精神激励下对个性解放的赞歌的体现,也正因有了冲决一切束缚的个性发展的勇气后,个性才得以充分发扬,才有作者撼天地的勇气和从心所欲的能量收聚,并使之成为了五四时代的最强音。
作为自由诗的初级阶段的产物,《天狗》以其恰如其分的艺术手法,纵横捭阖的宣泄力量,及清晰可感的革命精神,使其时代、艺术价值异常显著。
尹基殿,教师,现居湖北黄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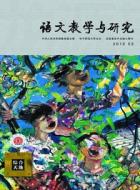
- 卖豆腐的女人 / 晓 苏
- 铁锤敲醒的白日梦 / 王海燕
- 解决教学对话操作层面问题的策略 / 翟红霞
- 提高学生作文能力的实践与思考 / 谢伟民
- 试论面批作文 / 杜运杰 万美莉
- 试论探究式教学 / 李腾军
- 试谈作文教学与思想教育的有机结合 / 魏永林
- 浅谈我的作文教学法 / 杨 晓
- 新材料作文审题立意探微 / 陈新宇
- 初中作文教学的反思 / 赵梅香
- 学学名著中的心理描写法 / 黄秀武
- 人物细节描写阶段性训练例谈 / 孙德建
- 作文教学个性化的内涵特征 / 李 刚
- 写作应关注社会生活 / 陈宏宽
- 作文《粗俗》评点 / 毛伟东
- 个性化作文教学的举三反一 / 武 宪
- 培养学生写作能力的实践策略 / 顾丽莉
- 让学生的写作回归真实 / 万珍娟
- 写景生动亮人眼 / 康吉松
- 搞好日记训练 提高写作水平 / 王德英
- 绿色作文 写亮生命 / 胡金凤
- 在作文教学中调动学生的主动性 / 董伟良
- 作文有效教学策略 / 王海玉
- 话说写话 / 王 梅
- 读写结合 以写促读 / 吴天学
- 我的高职语文教学探析 / 刘丽萍
- 例谈教学思想的有效取舍 / 魏晓斌
- 情境教学在高中语文教学中的实践 / 李宇佳
- 诱思探究策略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 / 赵广霞
- 信息技术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 / 孔国瑞
- 高中文言文教学浅论 / 张沭淮
- 谈谈中学语文教学中的表演艺术 / 谢静贝
- 浅谈如何实施语文综合性学习 / 车玲燕
- 陌生化在语文教学中的作用 / 罗湛英
- 探究性学习在语文教学中的作用 / 陈如天
- 指导学生积累的几点看法 / 兰 娟
- 实现课文教学与作文教学的双赢 / 罗 俊
- 试论多媒体技术在语文教学中的运用 / 杜爱玲
- 中学文言文教学方法探讨 / 袁 珊 罗秋红
- 构建大语文教育实践活动 / 郭西花 陈 鸿
- 语文教学要重视情感因素 / 靳江萍
- 经典阅读学习活动实施情况报告 / 庞仁甫
- 避开缺失 进行有效引导 / 夏明玉
- 也谈对话在语文阅读教学中的实施 / 朱亚萍
- 信息技术在识字教学中的应用 / 陈雪芳
- 小学语文个性化阅读教学的探究 / 石 晶
- 语文课堂因点拨而精彩 / 陈 芳
- 阅读古代文学作品意义漫谈 / 吕夫俭
- 变味的公开课 / 孙勤香
- 语文教学应注重课堂提问设计 / 洪孝添
- 语文教学中如何营造高效课堂 / 王 静
- 语文课堂导入的误区及改善对策 / 单淑英
- 优化多媒体教学 打造高效课堂 / 蒋 健
- 巧用电子书架 优化语文课堂教学 / 林文英
- 新课程改革下的课堂教学监控艺术 / 金玉红
- 细品《香菱学诗》中香菱的笑 / 任端巧
- 实现语文课堂教学有效性的途径 / 陈约芬
- 海洋文化资源语文价值的开发与利用 / 徐正辉
- 如何构建动态生成课堂 / 刘文娟
- 利用校园文化拓展语文学习新空间 / 何 翠
- 打造小学语文绿色课堂 / 王海侠
- 对外汉语语块教学实际效果调查研究 / 刘莺倩
- 也谈《风筝》的主旨 / 刘 洋
- 《林黛玉进贾府》二题 / 刘 明
- 三板块四环节教学模式反思 / 宋俊姿
- 三板块四环节之预习板块反思 / 王爱明
- “火眼金睛”辨歧义 / 李 莹
- 重建时代所急需的职业学校语文教学 / 谢增伟
- 高中语文教学的几点尝试 / 王亚丽
- 语文教改中的误区反思 / 杨文琴 王 岩
- 炼字炼出语文味 / 王凡娣
- 趣话语言得体 / 陈芬芳
- 巧用双关趣话 / 刘 菲
- 高考字形题解题技巧 / 杨丽华
- 品读:阅读的根本 / 崔春燕
- 例谈略读课文的切入式教法 / 盛 洪
- 《罗密欧与朱丽叶》教学设计 / 周 荔
- 《江南的冬景》说课稿 / 王立新 梁秀英
- 《一碗清汤荞麦面》教学方案 / 孙学勇
- 《天狗》的时代艺术性 / 尹基殿
- 《醉花阴》《声声慢》“愁”之比较阅读 / 张 弘
- 浅谈顾城诗歌的写作特点 / 冉建平 盛家林
- 《项羽之死》导学设计 / 王 敏
- 读王国维《人间词话》 / 孙付平
- 谈诗歌教学中的怡情养性 / 余旭辉
- 笑对一切 / 谢乐予
- 《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教学札记 / 余艳荣
- 岳飞印象 / 叶 烨
- 在语文教学中传承中华传统美德 / 熊 惠
- 务实校本教研 构建有效课堂 / 杜传家
- 语文教学是关于人的学问 / 孔凡鹏
- 让笑容重返人间 / 李成华
- 可爱的爸爸 / 王路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