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语文教学与研究·综合天地 2012年第2期
ID: 139456
语文教学与研究·综合天地 2012年第2期
ID: 139456
解决教学对话操作层面问题的策略
◇ 翟红霞
对话(Dialongue)作为语文教学中的一种重要的活动形式,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对话”和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无论是哪一种对话,都是学者之间进行学术研讨、思想交流和感情沟通的主要方式。最早正式提出对话理论的是俄国文艺理论家巴赫金,“自从巴赫金探讨对话性之后,对话,这个具有多元价值的理论开始逐渐被人们所重视并开始活跃于人本主义者的视野之中。”[1]巴赫金说,对话“是同意和反对的关系,肯定和补充的关系,问和答的关系。”他认为,“存在就意味着进行对话的交往。对话结束之时,也就是一切结束之日。因此,对话实际上不可能,也不应该结束。”“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单一的声音什么也结束不了,什么也解决不了。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2]巴赫金看来,对话与存在同生共存,生存离不开对话,对话是生存的前提和必要条件。存在意味着对话,对话是生命间互为存在必不可少的决定性要素。所以,有人类就有对话。人类教育活动起源于对话,从一定意义上说,教育是人类一种特殊的对话活动。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即使在原始社会中,人与人的对话也离不开教育者、受教育者、媒体及教学内容四大要素,是与当时的物质生产方式和整个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的。其目的是让人们在对话中传递社会信息,“将人类的精神内涵转化为当下生气勃勃的精神,并通过这一精神引导个体掌握知识和技术。”[3]所以,教育是个体通过对话从知识的学习和精神养育过程中共同去探究生命和世界的本质。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到了哈贝马斯那里,在他的“交往理论”中,他把对话更多地视为一种方法论,认为对话是达成现代交往最为合理、最为有效的一条重要途径。这种途径,形成了一种以传播知识、促进个体精神陶冶与养育、发展、完善及社会关系为直接目标的活动,今天的语文教学奠定了基础,并促使语文教学方式、程序和价值发生变革。
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订九年义务教育,在《语文课程标准(实验)》解读中指出:“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文本之间对话的过程。”[4]《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指出:“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教科书编者、文本之间的多重对话,是思想碰撞和心灵交流的动态过程。阅读中的对话和交流,应指向每一个学生的个体阅读”。[5]这些崭新的语文教育理念都源自于对话理论。对话理论的具体说明是:“要重视学生在阅读过程中的主体地位”,“要重视学生的独特感受和体验”,“教师绝不能取代学生在阅读中的主体地位”。这在语文教学操作层面上,是一种维权行为,即维护学生独立思考权、独立发言权,“维护学生‘倾听’和‘言说’权,是十分要紧的举措”。[6]只要我们落实这种举措,真正转变教育思想,从传统的语文教学“满堂灌”“话语霸权”中走出来,对话理论操作起来并不困难。对话理论操作的基本条件是:教师对学生要尊重、信任、平等。从对话的方式上说,读者与文本对话、与文本相关者对话,包括读者通过文本与作者对话、读者通过文本与文本所反映时代背景对话,与教师对话,与学生对话。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教学对话是最需要重视与解决的基本问题。
教学对话是师生之间问与答的语言行为,是师生之间凭借文本所达成的语言性沟通与交融,也是师生之间的语言性交往。通过教师的提问,激励与引导,学生自由思考,自由表达自己的疑问见解而获得知识技能、发展能力、与人格的教学方法,明确了阅读对话教学的概念,为教学对话实施奠定了基础。
阅读教学的目的是培养优秀的对话者,阅读教学依然是阅读教学,它具有一定程度的目标预设和行为控制,对话只是发生在某些教学手段,某些教学层面,某些教学内容上。在阅读教学对话过程中经常有对话的光芒闪现,教师始终对学生、对“教”抱有对话情怀,即使是教诲或是传授,也总是出于对学生爱和成长的责任。教学对话具有以下特征:(1)教学对话的共同性。对话必须双方都具有共同的利益追求。对话展开的前提是对话双方不能完全对立。(2)教学对话的平等性。对话作为一种人际交往行为只存在于两个或更多具有独立人格的主体之间。它是以一种人际“互动”为特征、以人生意义的获得为目的的交互主体间性。对话的这种主体间性决定了对话必须在两个平等的主体之间展开。(3)教学对话的创新性。对话是一种开放、自由探究的理性精神,同他人或他人创造的文本一道,共同创造知识、追求真理的智慧活动,重新建构,生成意义,因此教学对话具有创新性。(4)教学对话的动态开放性。对话双方可以探讨所有跟主题有关的内容,可以和其它任何一个主体或客体发生对话,不会刻意追求答案的唯一性和标准性,并且,对话还可以延伸到课前课后等时间,对话双方在对话中解决了一个问题,得到了一种新的认识,接着又会出现新的问题,对话是可持续的,没有终点的。因此,整个过程是开放的、动态的。
运用对话理论实施阅读对话教学,教师的担子不是轻了,而是重了许多,要力所能及地在课堂上与学生对话提供话题资料,有如准备自助餐一般,要提高自己的对话水平,不但要备教材与文本对话,还要备学生与学生对话,了解他们已经知道了哪些,还需要补充哪些,不但要预设对话,还要到课堂上处理生成性对话,既要组织好讨论,更要指导好生生对话,同时教师还得参与到对文本的理解之中,不但将自己对文本的理解交给学生,更重要的是教学生如何与文本对话。因此说,教师既是阅读对话的指导者,又是教学对话的促进者。在对话理论操作层面中,教学对话有效策略如下:
一.通过填补文本“空白”激话对话
文本“空白”即作者有意无意在作品中留下的可供读者去充分发挥的空间。正是这种空间使读者自觉不自觉的参与到文本的创作中来。成为文本的补充对话者。文学作品自身之内容包含着许多“不确定点”和“空白”,作品由于这些“不确定点”和“空白”的存在而产生一种活力性。这种活力吸引着读者介入到作品所叙述的事件中去,为他们提供阐述与想象和自由。以这种想象填充文本空白的形式可以激活学生与作品进行交流与对话。教师由文本“空白”入手。充分为学生提供、创造对话的条件,让学生深入到作品中去体验作者的生命意识,发挥想象力、思维力、创造力、参与到作品中的平等的对话中,与文本形成心灵的碰撞与精神共鸣。波兰现象学家美学家罗曼·英家登(Roman lngarden,1893—1970)从艺术作品严密层次中发现了“空白点”。这种“空白点”是一种图式化或是被表现的客体。图式化方面和被表现的客体则由意义群决定,指虚构的纯粹意向性客体世界。它充满“空白点”,模糊不清,迷离恍惚,是不确定的,依赖于读者的参与才能确定下来,有待于读者去“填充”对话。[7]例如《祝福》中的鲁四老爷听到祥林嫂被她婆婆家绑架回去后,他说道:“可恶!然而……”这句话省略了大量的信息,如果教学中只是一带而过,就会留下很多疑点。我在这里是这样激活学生对话的,提出为什么说“可恶”?“然而”之后省略了鲁四老爷的什么思想?这时学生只要联系文本中介绍的人物关系和身份,并调动期待视野中封建礼教的相关知识,就不难填补这个“空间”。有的学生说,“可恶”是因为鲁四老爷认为祥林嫂的婆婆家暗中绑架了自己的佣人,失掉了鲁家的身份,损害了他的尊严,因此骂出了“可恶”;“然而”,他又认为婆婆劫走媳妇,于封建礼教而言却是应该的,合情合理的。可见,学生在阅读文本时并不是直接简单地“登记”文本的表面形式,而是激活脑海中相关的信息参与文本的理解,填补了“可恶!然而……”的空白点。而这种“填补”于原文本要表达的意思是一致的。
二.通过教师的“见解”隐蔽呼唤对话
在对话理论操作层面中,根据教师的见解隐蔽呼唤对话,不失为一种好的教学对话策略。
教师见解隐蔽,就是教师在阅读教学中有意识地将自己的思考、理解、体验不直接说出来,呈现给学生视野“空白”,通过填补“空白”而呼唤学生进行深层次对话。给学生创造一个经由与文本对话而产生的自我对话,也是新旧知识的视野融合,这种融合还能呼唤学生与学生之间对话,在对话中他们有不同的见解和冲突,碰撞出智慧的火花,涌动出情感的激流,充分地感受到在教师见解隐蔽状态下,作为阅读文本的学生与文本对话、与文本相关者对话所具有的创造力量。
阅读《我与地坛》文本时,教师先不把自己的见解作为结论告诉给学生,而是隐蔽起来呼唤学生与文本对话得出结论。我提出问题:“为什么‘自从那个下午我无意中进来这个圈子,就再也没长久地离开过它’?‘我’在地坛里究竟得到了什么?”要求学生以对话的形式表达出自己的阅读感受。于是出现了个性化阅读对话:有的同学说给“我”以启示,因为地坛经历四百年风雨沧桑而生命更为精彩更为炽热,正告诉作者虽然残疾但还是要坚强活下去;有的同学说,给“我”以超脱,因为地坛四百年,宇宙几万年,个人的生命只是沧海一粟,所以个体苦难在整个历史面前失去重量;还有的同学说,给‘我’以安慰,这里宁静的气氛容使“我”心灵在此栖息,是不用逃避一个世界的另一个世界。这种见解隐蔽,引发学生联系文本自己来“说”,使学生能够在“感受性阅读”中进入想象空间,而这种空间所带来的文本自身的呼唤力,与教师隐蔽见解呼唤学生与文本对话是相一致的,可见,呈现教师的见解隐蔽可以呼唤学生对话这种方式,无论是就文本自身内容与形式来说,还是就教学对话方式来论,都在向学生最大程度的展示着自己与文本对话,而这种对话所带来的恰恰是对教师见解隐蔽的补充,完成了对作品的阅读。
三.通过纠正学生“误读”引导对话
“误读”是指学生在阅读时使用了不正确的读法因而出现了不合适的理解。这种理解是学习过程中的常态。也就是说,尽管最终的理解未必与文本契合,尽管对同一文本可能产生几种不同的理解(阐释),但他们都是可接受的。在接受过程中用对话的形式给学生纠正。纠正,当然不是给出正确的答案,而是纠正学生不正确的理解和读法。
例如,对《窦娥冤》三桩誓愿怎样解释“冤”的含义时,学生进行了一场争论:
学生1:三桩誓愿是窦娥对黑暗社会的抗争,她的冤屈和抗争感天动地,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窦娥是善良的,她的悲惨命运是值得我们同情的,所以说她很“冤”。
学生2:但我认为窦娥的三桩誓愿是一种变态的复仇行为。她的反抗是一种祸及百姓的反抗,谈不上什么“冤”和善良。
学生3:我也同意这种说法。因为窦娥因一己之冤,而让百姓蒙受抗旱三年之灾,老百姓吃什么?喝什么?怎么活?她“冤”什么?
学生4:我认为刚才两位同学的发言不对,他们俩看问题比较偏激,我们看问题应该以一种积极的心态去看,也许这其中存在着复仇行为,但我认为更主要是颂扬窦娥的善良品质和她含冤被斩时强烈的反抗精神。
学生已经争论了8分钟,这已经超越了锻字炼句、咬文嚼字的范畴。而与学生人生观、道德观联系来看,我认为,单从学生对问题片面的理解来说服学生,学生很难服气。于是,我引导学生探讨“思考的角度”——以积极正面的态度或者消极反面的态度来看待窦娥的冤屈,哪个角度更好?指导学生纠正对话。
学生5:我认为应以积极的态度去面对窦娥,如果大家都用消极的态度来看待事物,那么这个世界就没有可爱的东西了。
学生6:我认为应该是前者。我在课外读物中看到,《窦娥冤》本身就是为了弘扬窦娥受刑的强烈愤怒和反抗精神。作者本身就是为了歌颂窦娥的这种精神而创作的。
很显然,同学们以他们自己的智慧和能力作出了判断,进行了纠正对话。他们的智慧和判断再一次证明了——相信学生,会创造出美好的未来!
四.通过学生“倾听”进行“言说”对话
在新课程改革中,我们经常见到和听到的一个新词汇——“倾听”,这个重要的语文教学理念,给教师赋予了新的使命——教学生能够学会倾听,实际是在强调,在教学对话中赋予学生“倾听”“言说”作品的权利。新课程标准总目标中说的“具有独立阅读能力”,“教学建议”说的“不应以教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有一层含义就是在阅读教学中倡导让学生自己去“倾听”,自己去“言说”。这样体现了对话理论操作层面中的阅读对话和教学对话的理论精神。对“听者”的确认,是我们不再停留于说者个人的精神世界,而是深入言语交际的内部,体会思想与思想的碰撞,感情与感情的交流与对话。对“言说”的理解,我们也不能简单的理解为让学生听后把他的思想简单的复制与他人的头脑中,而是要求“听者在接受和理解言语的意义(语言意义)时,他同时就要对这一言语采取积极的应对立场:同意或是不同意(全部还是部分同意),补充它,应用它,准备实现它等。”[8]说者不仅力求使自己的言语为人理解,更要求获得来自听者的回应。这样看来,对话是“言说”与“倾听”共生共促的,言者与听者角色不断转换,教学对话继续,就是对话双方“倾听”与“言说”的结果
从“听者”与“言说”的角度来分析文本,剖析人物语言,能够更加深入理解人物内心世界,看到更多的隐藏着的思想和情感。在《宝玉挨打》的细节中,我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贾宝玉是挨打的人,他可以哭而且可以嚎啕大哭,但课文没有写他哭。这是为什么呢?同学们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又读了一遍这个细节,读罢,我接着问:同学们说宝玉是哭好还是不哭好?
学生“倾听”后进行了“言说”对话:
学生1:写宝玉不哭好,因为这样可以体现宝玉的封建叛逆者的形象,面对贾政毒打,他一声不吭,表现了他反抗和倔强。
学生2:我认为写他哭好,因为宝玉不是什么英雄好汉,被打疼了就哭,乱哭乱嚷让人感到真实。
学生3与学生1对话:我觉得写宝玉哭比较真实可信。因为他怕贾政,忠顺王府的人来追查蒋玉菡时便哭了,他被人打之前也托人通风报信,只是没有找到人。贾宝玉不敢有意对抗贾政。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学生的每一句对话都是针对宝玉挨打哭与不哭的性格来言说的。对话中决定了它总是要针对一定的“听者”来表达思想、交流感情的。“听者”把握“言说”来构建自己表达的言语。没有这个“听者”,就不会有“言说”,也就没有这段对话。如果听者没有这样的反应,言说者构建出来的话也许会是另一番面貌。这都是“倾听”后的“言说”,是自己与文本对话后的“意义建构”。在这里学生“倾听”后“言说”对话的作用是何等的重要!
上述问题,我们不难看出,对话是语文教学的基本特征。教师在教学对话中,绝不能话语霸权,要创设平等、民主、和谐的课堂教学对话环境,要互动交往、动态开放、合作发展、创造生成、倾听关爱、以人为本地进行课堂教学。与学生对话、与文本对话、与文本相关者对话,在多层次对话中达到思想碰撞和心灵交流,将阅读对话和教学对话有机结合,并且讲究教学对话的有效策略,抓住对话时机,教会学生有节制地“说”(解读),使学生学会在对话中如何合适的“倾听”,合适的“言说”,即学会“对话”——与文本“对话”。唯有如此,教学对话理论操作层面问题才能迎刃而解,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教学对话步入理想的境界。
参考文献:
[1]郑国民、黄显涵《对话理论与语文教育》[J] 语文教学通讯·高中刊2003年5期。
[2]张开焱《开放人格——巴赫金》[M]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3]唐勇《论教学交往的有教性》[J] 中国教育学刊,2003年6期。
[4]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语文课程标准研制组九年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试验稿)解读》[M]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5]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订《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试验)》[J] 语文建社,2003年9期。
[6]王荣生《语文科课程论基础》(第二版)[M] 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7]王一川《从意义的瞬间生成——西方体验美学的超越性结构》[M] 山东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8]巴赫金《文本对话与人文》 [M] 白春仁等译,石家庄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翟红霞,吉林松原职业技术学院讲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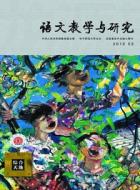
- 卖豆腐的女人 / 晓 苏
- 铁锤敲醒的白日梦 / 王海燕
- 解决教学对话操作层面问题的策略 / 翟红霞
- 提高学生作文能力的实践与思考 / 谢伟民
- 试论面批作文 / 杜运杰 万美莉
- 试论探究式教学 / 李腾军
- 试谈作文教学与思想教育的有机结合 / 魏永林
- 浅谈我的作文教学法 / 杨 晓
- 新材料作文审题立意探微 / 陈新宇
- 初中作文教学的反思 / 赵梅香
- 学学名著中的心理描写法 / 黄秀武
- 人物细节描写阶段性训练例谈 / 孙德建
- 作文教学个性化的内涵特征 / 李 刚
- 写作应关注社会生活 / 陈宏宽
- 作文《粗俗》评点 / 毛伟东
- 个性化作文教学的举三反一 / 武 宪
- 培养学生写作能力的实践策略 / 顾丽莉
- 让学生的写作回归真实 / 万珍娟
- 写景生动亮人眼 / 康吉松
- 搞好日记训练 提高写作水平 / 王德英
- 绿色作文 写亮生命 / 胡金凤
- 在作文教学中调动学生的主动性 / 董伟良
- 作文有效教学策略 / 王海玉
- 话说写话 / 王 梅
- 读写结合 以写促读 / 吴天学
- 我的高职语文教学探析 / 刘丽萍
- 例谈教学思想的有效取舍 / 魏晓斌
- 情境教学在高中语文教学中的实践 / 李宇佳
- 诱思探究策略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 / 赵广霞
- 信息技术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 / 孔国瑞
- 高中文言文教学浅论 / 张沭淮
- 谈谈中学语文教学中的表演艺术 / 谢静贝
- 浅谈如何实施语文综合性学习 / 车玲燕
- 陌生化在语文教学中的作用 / 罗湛英
- 探究性学习在语文教学中的作用 / 陈如天
- 指导学生积累的几点看法 / 兰 娟
- 实现课文教学与作文教学的双赢 / 罗 俊
- 试论多媒体技术在语文教学中的运用 / 杜爱玲
- 中学文言文教学方法探讨 / 袁 珊 罗秋红
- 构建大语文教育实践活动 / 郭西花 陈 鸿
- 语文教学要重视情感因素 / 靳江萍
- 经典阅读学习活动实施情况报告 / 庞仁甫
- 避开缺失 进行有效引导 / 夏明玉
- 也谈对话在语文阅读教学中的实施 / 朱亚萍
- 信息技术在识字教学中的应用 / 陈雪芳
- 小学语文个性化阅读教学的探究 / 石 晶
- 语文课堂因点拨而精彩 / 陈 芳
- 阅读古代文学作品意义漫谈 / 吕夫俭
- 变味的公开课 / 孙勤香
- 语文教学应注重课堂提问设计 / 洪孝添
- 语文教学中如何营造高效课堂 / 王 静
- 语文课堂导入的误区及改善对策 / 单淑英
- 优化多媒体教学 打造高效课堂 / 蒋 健
- 巧用电子书架 优化语文课堂教学 / 林文英
- 新课程改革下的课堂教学监控艺术 / 金玉红
- 细品《香菱学诗》中香菱的笑 / 任端巧
- 实现语文课堂教学有效性的途径 / 陈约芬
- 海洋文化资源语文价值的开发与利用 / 徐正辉
- 如何构建动态生成课堂 / 刘文娟
- 利用校园文化拓展语文学习新空间 / 何 翠
- 打造小学语文绿色课堂 / 王海侠
- 对外汉语语块教学实际效果调查研究 / 刘莺倩
- 也谈《风筝》的主旨 / 刘 洋
- 《林黛玉进贾府》二题 / 刘 明
- 三板块四环节教学模式反思 / 宋俊姿
- 三板块四环节之预习板块反思 / 王爱明
- “火眼金睛”辨歧义 / 李 莹
- 重建时代所急需的职业学校语文教学 / 谢增伟
- 高中语文教学的几点尝试 / 王亚丽
- 语文教改中的误区反思 / 杨文琴 王 岩
- 炼字炼出语文味 / 王凡娣
- 趣话语言得体 / 陈芬芳
- 巧用双关趣话 / 刘 菲
- 高考字形题解题技巧 / 杨丽华
- 品读:阅读的根本 / 崔春燕
- 例谈略读课文的切入式教法 / 盛 洪
- 《罗密欧与朱丽叶》教学设计 / 周 荔
- 《江南的冬景》说课稿 / 王立新 梁秀英
- 《一碗清汤荞麦面》教学方案 / 孙学勇
- 《天狗》的时代艺术性 / 尹基殿
- 《醉花阴》《声声慢》“愁”之比较阅读 / 张 弘
- 浅谈顾城诗歌的写作特点 / 冉建平 盛家林
- 《项羽之死》导学设计 / 王 敏
- 读王国维《人间词话》 / 孙付平
- 谈诗歌教学中的怡情养性 / 余旭辉
- 笑对一切 / 谢乐予
- 《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教学札记 / 余艳荣
- 岳飞印象 / 叶 烨
- 在语文教学中传承中华传统美德 / 熊 惠
- 务实校本教研 构建有效课堂 / 杜传家
- 语文教学是关于人的学问 / 孔凡鹏
- 让笑容重返人间 / 李成华
- 可爱的爸爸 / 王路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