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文学教育·中旬版 2010年第2期
ID: 152988
文学教育·中旬版 2010年第2期
ID: 152988
于反复中见真意
◇ 羊乃书
[摘要]重复叙事是余华写作中运用的一种重要手段,《许三观卖血记》中大量的主次重复叙事不仅搭建起小说全文的总体框架,同时也在细处勾勒文本肌理,构成了简练明净却寓意深邃的叙述风格。
[关键词]许三观卖血记:重复叙事
先锋派作家余华自1987年发表《十八岁出门远行》开始,其作品的先锋性和实验性就尤为引人注目。而叙述,在余华看来,在作品中具有本体的地位,他在涉及阅读和创作的随笔和访谈中曾多次谈及他对于叙述的认识,他说“叙述,在确立之前就是一堆杂乱无章的困难,写作的过程就是不断地和它们相遇的过程,不断地去克服它们的过程,最后你会发现一个完整的叙述成立了。”而余华对重复叙事的运用在此部小说中达到了一个高峰,它不仅搭建起小说全文的总体框架,同时也在细处勾勒文本肌理,构成了简练明净却寓意深遴的叙述风格。
一、何为“重复”
重复是一种古老的艺术力量,最早是修辞学术语,指依靠重复某一词或词组来达到特定效果的修辞手法。在诗歌中,重复是最基本的修辞原则,体现于对押韵、格律、对仗等的要求。按照传统的阅读经验,重复在诗歌中主要通过句式的循环往复,营造艺术气氛,产生一唱三叹的效果。重复也是小说叙事的重要手段,在小说中,“重复”的运用可分为两类:叙述重复和主题重复。关于重复,美国当代批评家J·希利斯·米勒认为:“从细小处着眼,我们可以看到言语成分的重复:词、修辞格、外在形式或内在情态的描绘;以隐喻方式出现的重复则显的更为精妙:”从大处看则“有事件或场景”的复制或“由一个情节或人物衍生的主题”在“同一文本中的复制”。
二、文本中的主重复叙事
“卖血”无疑是全文中最大的叙事重复。小说中写到许三观在七个不同的时期、为了七个不同的目的而进行的十二次卖血。
第一次出现在第一章,许三观无意中卖了一次血,他用这次卖血的钱结了个婚。此后大约过去了十年。第二次因为儿子一乐打架闯祸而被方铁匠抄了家,为了赎回这个家,他去卖了血。第三次是为了另一个女人林芬芳,他卖了一次血。第四次是在大饥荒的日子里。在全家喝了一个月的玉米稀粥之后,他决定去卖一次血,以便全家能吃上一顿面条。第五次是在上山下乡的运动中,两个儿子一乐和二乐都被发往乡下,为了儿子他接连两次卖。第六次是为了一乐的病他沿途一路卖血去上海,一路连续卖了五次,差点儿搭上了自己的一条命。此后又是十一年过去了,年老了的许三观为了吃炒猪肝喝黄酒而去卖血,与前面那么多次不同的是,这一次,他的血被拒收。
全文情节发展以“血”为底色,开篇以许三观与爷爷牵涉“卖血”的谈话起势。‘前部又以阿方与根龙的“卖血启蒙课”为过渡,再到后部许三观由被引领到成为另一些人(来喜来顺)卖血之路上的领路人,最后到文末许三观再也卖不了血的悲剧结局为落幕。第一次到第五次卖血时序上分布循序渐进,不拖沓,不急迫,缓缓将读者引入由“卖血”串连起的许三观的生命历程,在全文的展开部分将故事节节推进。而第六次到第十一次卖血则骤然密度加强、节奏加快,氛围明显凄厉、惨烈,卖血这件事的悲剧本质赤裸地显露,将全文带向高潮点。最后一次失败的卖血为许三观一生的卖血历程画上了句点。整个进程充满音乐性,前段平实舒缓,中段高昂激越,后段复归平静。这一曲属于许三多的优美而悲怆的受难曲,使读者不得不紧紧跟着作者的叙述,一口气将小说从头看到尾,
纵观许三观的卖血经历可以发现,除了第一次是偶然性的,第三次是偷情后为林芬芳买补品作补偿,其余的都是为了生活的方方面面,迫于生活的艰难、人生的困苦不得不以卖血维持生活的常态与生命的进程。几乎每一次卖血,就暗示着许三观一家面临的一次难关,而卖血,这一愚昧与无知的求生手段,也成了这个家庭战胜难关的唯一选择,看似自愿的次次卖血掩盖的是生活的无奈与辛酸。生活一次又一次挤压出许三观的血液,卖血换来的金钱反过来艰难的推动陷在泥泞中的生活车轮,生活——血——生活,这个悲剧循环是无数下层人苦涩的生存智慧和生活准则。
“血”这个意象背后,是旺盛的生命力,是美好的人性,更是民间永恒的苦难象征。
三、文本中的大量重复序列
围绕主题的重复事件一卖血,小说中还存在着不少次主题重复的序列。小到许三观儿子的名字:许一乐,许二乐,许三乐,以及医院里李血头死后的“年轻血头”;大到超出(或包含)许三观卖血事件范围的序列:阿方和根龙的卖血。许三观的卖血,来喜、来顺兄弟的卖血。此外,小说中局部的叙事技巧也沿用主题重复的方法。第五章中关于一乐不是许三观儿子的流言的描述,直接使同一内容的段落一字不差地重复(这倒符合流言的特征),一些人物对话段落采取车转辘式的重复办法,譬如“许三观对许玉兰说:……”,接着没有任何停顿,又是“许三观对许玉兰说:……”,如此反复,甚至独立构成一章,如第十八章。在大大小小的次主题重复序列中。许三观卖血的主题重复显得不是那么突出了。至少在叙述节奏上。次主题重复序列分流和转移了主题重复积累的紧张感。在一个钟表店里,听清一只钟的走动声显然是非常费力的。次主题重复序列中还有两个直接对许三观卖血的主题重复产生影响的部分,它们是卖血前的大量喝水和卖血后在胜利饭店来“一盘炒猪肝,二两黄酒,黄酒要温一温”。这两个次主题重复具有较强的戏剧化效果,它们使无奈、悲凉的卖血事件带来某些诙谐意味。例如,第二次卖血后,许三观为事前束喝水而懊丧不已:第三次卖血后在胜利饭店因为大夏天叫人把“黄酒温一温”而落下笑柄。戏剧化效果冲淡了卖血事件的正剧色彩,主题重复的悲剧浓度有所降低,整部小说的最后一句意味深长。新来的年轻血头不让年迈的许三观卖血,于是他愤愤不平地对许玉兰说:“这就叫席毛出得比眉毛晚,长得倒比眉毛长”。在主题重复的完整序列中,只有那茂盛地生长在隐蔽角落里的徽不足道的东西,没有重复“重复”的覆辙:“出得比眉毛晚,长得倒比眉毛长”。在这个卑微的唯一突破“重复”秩序的存在物前,小说中所有的主题重复序列都蒙上了窘迫的似是而非的表情。
四、重复叙事的价值
重复成为这篇小说耐人寻味的亮点,使小说在叙述方式上有一种反补归真的单纯和明净。而这种单纯和明净中,却又蕴含着深厚的情感和思想内涵。
1、重复叙事有助于深化主题
这主要体现在主重复叙事“卖血”这一主题中,小说在重复叙述的舒缓优美而不乏苍凉的旋律中传递出作者对许三观卖血的怜悯和敬慕,对人类苦难承受能力和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之情。
2、重复叙事有助于塑造人物性格
当许三观得知妻子许玉兰与她原来的对象何小勇有过性关系后,重复的对白构成叙述语言,充分表现了许三观受了委曲伤害之后的神
情、动作及其简单的内心活动。
许三观躺在藤榻里,两只脚架在凳子上,许玉兰走过来说:
“许三观,家里没有米了……,去粮店把米买回来。”
许三观说:“我不能去买米,现在什么事都不能做了,我一回家就要享受……你知道我为什么要享受吗?就是为了罚你,你犯了生活错误……”
许玉兰说:“许三观,我正在洗床单,这床单太大了,你帮我揪一把水。”
许三观说:“不行,我躺在藤榻里,我的身体才刚刚舒服起来,我要是一动就不舒服啦。”
许玉兰说:“许三观,你帮我搬一下这只箱子,这一个人搬不动它。”
许三观说:“不行,我躺在藤榻里享受呢……”
许玉兰说:“许三观,吃饭啦。”
许三观说:“你把饭给我端过来,我就坐在藤榻里吃。”
许玉兰说:“许三观,你什么时候才享受完呢?”
许三观说:“我也不知道。”。
许三观对待妻子不忠一事,分别予以了惩罚;对男方何小勇他告诉二乐三乐长大后去强奸何的两个女儿,让当时还很小的二乐三乐都乐了;为惩罚许玉兰,采取了“罢工”行动,用“躺在藤榻里,两只脚架在凳子上”的“享受”、“舒服”来弥补精神上所受的伤害,最后以偷情来企图摆脱压在心里的屈辱。他曾有一点儿古人的血气方刚,也曾有一点儿现代西方的洒脱通达,但最终就是用最简单的重复语言、最简单的重复行动来表达他的痛苦和不满,用自己能有的肉体享受来弥补,得到简单的补偿。这就是许三观无奈的生存境遇。重复的叙述,勾勒出了许三观对生活没有奢望,也没有远大目标,只是被一种简单的生存欲望支配着的性格特征,即使是对于现代人视为最痛苦的事情,他也仅仅是幼稚肤浅的发泄一通后置之脑后,一个当代版的“阿Q”似的人物呼之欲出。
3、重复叙事有助于形成文本引力
“过生日的许三观用嘴给家中每个人炒一道菜,让他们用耳朵听着吃”这一片断,巧妙却让人心酸流涕。这次“精神会餐”吃红烧肉,一般看来描述一遍就可以了,但余华却让许三观重复了四遍。这一而再,再而三的“烧红烧肉”,看似漫不经心,但叉合情合理的重复,慢慢将吃红烧肉这一事件本身带入“后台”,一个家庭苦难中的温馨走向“前场”,文本的抒情旋律和情感节奏逐渐凸显,形成了独特的艺术效果。也正因为如此,许三观嘴皮的每一次嗫动,说者精心、听者专心的叙述,才让人每每读来都倍觉心酸。陈思和曾说:“许三观过日子这一段,是用想象中的美味佳肴来满足饥渴的折磨,这是著名的民间说书艺术中的发噱段子,进行移用后,恰当地表现了民间化解苦难的特点。”
4、重复叙事有助于简化叙述,强化节奏感,直击现实
小说的第四章仅由徐玉兰生孩子的三段喊叫构成。作者而在许玉兰产子的部分,运用跳跃式重复处理的方式,不但加快了小说的叙述速度,还为文本注入了明快、激情的旋律。每一次生子,许玉兰都声嘶力竭、大喊大骂,场面反复、话语单一,而医生适时的出现,中断喊叫,使之成为一部完整的三重奏。这种疏空式重复叙述,在密集叙述中间断出现,使作品的密度和谐,形成了很清晰的作品节奏,同时使我们进入到没有被语言掩盖的赤裸的现实。
5、重复叙事有助于营造回旋复沓的美感和童话韵味
余华大胆采用了富有童趣的、简单循环的叙述方式。叙述语句一次次简单重复,回环复沓产生出令人惊叹的童话韵味。如“他们去告诉许三观说:‘许三观,休家的一乐呜呜哭着往西走:许三观,你家的一乐不认你这个爹了:许三观,你家的一乐见人就张嘴要面条吃;许三观,……”;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前面已引用的:在饥荒年里,许三观过生日,他用嘴给三个儿子“炒”菜吃,让儿子们“用耳朵听着吃了”,这一回精彩的口头烹饪表演,一次一次重复产生的一种令人震惊也回味无穷的艺术效果,在重复中实现了深度推进。这也令人想到《诗经》里回环往复的那特有的审美韵味。
五、结 语
其实重复叙事在余华的多部作品中既是结构的主要手段,也是构成细节的主要手法之一。从他的第一篇实验性作品《十八岁出门远行》写“我”漫无目的地在路上漂泊,“像一条船”、“像一匹马”,始终在游荡,沿途的风景是丰富而单调的不断重复。《河边的错误》就因运用事件的重复凸现主题而引人注目。《偶然事件》叙写的是不同的人物都沿着命定的路线,在重复着相同的命运悲剧。转型后的长篇小说《活着》,重复仍是主要手法,以连续不断的死亡事件而进行着不断的重复叙述,而且较之从前更为精致。其“叙事视角和叙事方式,是借用了民间叙事歌谣的传统,有意偏离知识分子为民请命式的‘为人生’的传统,独创性地发展起民间视角的现实主义传统。《活着》是叙事者下乡采风引出的一首人生谱写的民间歌谣。”在这无疑都是余华为实现深度推进而有意制造出来的叙事策略。通过上述分析,在《许三观卖血记》中,余华对于重复叙事的运用无疑最为纯熟自如。重复的手法以如此多的形式成功地出现在一篇篇幅并不是很长的长篇小说里,无疑是极大地丰富了它的内涵,拓展了它的应用空间,仅从这一点来看《许三观卖血记》也是功莫大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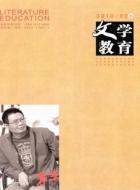
- 写作的清醒叙事的智慧 / 姜广平
- 浅析《小团圆》的人称视角 / 陈禹来 周益龙
- 同调秋色各抒心曲 / 李培荣
- 一曲奉献给为国捐躯者的颂歌 / 李 蓉
-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心中的自然人格美 / 轩袁祺
- 《墙上的斑点》赏析 / 卓 芹
- 情归何处:从历史情境到当代网络 / 陆艳清
- 儒家传统与鲁迅的精神至上观 / 刘 倩
- 萧红与国民精神 / 吕 娜
- 《歧路灯》中“再”的一种特殊用法 / 李继刚
- 在颠覆中重建现实主义精神 / 孟庆敏
- 冯尼格特小说《猫的摇篮》的生态主义解读 / 张云帆
- 一段精彩的“电影语言” / 谢妙婉
- 玫瑰的悲剧 / 刘 俊
- 新解中国之道德 / 德 庶
- 培养人文素养提升文化品位 / 曾建聪
- 玫瑰的悲剧 / 刘 俊
- 由社会考试与学校考试脱节现象反观学校教育 / 陈 玥 胡园园
- 欠发达地区民办高中面临的师资问题及对策 / 王志华
- 刍议街头篮球在我国兴起的原因及意义 / 吴水华 宋 辉
- 试论白先勇的《永远的尹雪艳》 / 姚 雨
- 用科学发展观创新高职学生管理理念 / 谭煜颖
- 论《文苑外史》中作家的异化 / 穆文超 李权芳
- 浅析《女勇士》中华裔女性成长的艰辛 / 马 荟
- 从法律视角看如何促进教师幸福感 / 刘 媛
- 文学之“轻”与生命之“重” / 李婉莉
- 于反复中见真意 / 羊乃书
- 例说自主学习中教师角色的定位 / 孙静华
- 李商隐《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一诗解读 / 陈阳阳
- 中年知识分子心理健康的现状分析 / 王 磊 周艳杰
- 卢仝:险怪诗人 / 范爱菊
- 在生活中学习有用的地理知识 / 张 敏
- 浅析《罪与罚》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人生哲学的表现 / 王 典
- 教学中的导入法初探 / 纪艳萍
- 高职高专学院辅导员提升职业自豪感新探 / 高 娟
- 论素质教育和课程改革 / 闫长珍
- 试评儿童文学作品《小海蒂》的翻译 / 康 健
- 高职学院实践教学质量监控体系构建初探 / 张 洋 蒋兰芬
- 例谈高中师生信息行为 / 吴正香
- 如何利用网络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 王百玲 沈 强
- 浅论水意象在《老子》中的多重审美意蕴 / 张兴茂
- 浅析国外中职招生策略 / 肖 赛 杜祥培 饶异伦
- 浅析范长江的新闻思想 / 李 涛
- 革命畅想曲之换了人间 / 李先宇
- 论译者职业伦理 / 蒲红英
- 玛格丽特.杜拉斯的白日梦 / 黄水源
- 中美职业教育师资状况的比较与分析 / 安 艳
- 浅析洛克儿童心理健康教育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 江 玲
- 谈谈新课程背景下语文教师的角色定位 / 魏兴隆
- 比喻与寓言辨析 / 李守卿
- 一段精彩的“电影语言” / 谢妙婉
- 浅析大学生英语听力障碍及对策 / 朱品品
- 试论中国古代文论中的“味”范畴 / 曹小欣
- 浅谈新课改理念下的阅读教学 / 李秀卿
- 浅析基于学生个性差异的高职英语分层教学 / 闰 宇 季静静
- 农村孩子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 / 张瑞珍
- 试论大学英语学习中的困难与对策 / 朱晓伟
- 高职本科的定位探析 / 毛艳青 李 宁
- 刍议英语副词及形容词的运用 / 肖新元
- 开放性的实践美学 / 胡亚民
- 绘画过程中艺术心态的培养 / 朱庆财
- 音乐教育的魅力 / 董丹丹
- 新课程下的高中英语写作教学 / 温春花
- 浅谈初中音乐欣赏课教学 / 龙曼丽
- 浅议电影名与电视剧名 / 张 萍
- 在教学中实施素质教育 / 贾小兰
- 情思飞扬 以歌育人 / 孙 华
- 浅析音乐教育中的美育功能 / 刘 冰
- 任务型教学法和中学英语教学 / 张 琴
- 中国民间儿童服饰图案的艺术特点与文化内涵 / 许晓慧
- 美学价值与审美教育 / 王荣国
- 中学语文的教育功能与培养 / 肖 璘
- 因特网在英语写作教学中的应用 / 苗 珺
- 大学语文教育的现状与教改刍议 / 李公文
- 《导游景点讲解》课程教学模式 / 黄小芳
- 初中语文教学中渗透人文教育的思考 / 黄建文
- 浅谈识字教学 / 文 静
- 以用促学注重实践 / 黄伟飞
- 职业中专美术教育的问题及对策 / 徐 燕
- 浅谈信息技术下的语文教学 / 王翠芳
- 论现代汉语规范化的重要性 / 李 宁
- 小议课堂中的情境教学 / 翟永胜
- 发挥语文教学的德育功能 / 凌希明
- 培养学生的汉字书写能力迫在眉睫 / 王德胜
- 培养写作兴趣提高写作能力 / 王建位
- 浅谈高中作文教学 / 潘海燕
- 心领神会话悦读 / 白孝全
- 浅谈如何做好班级管理工作 / 姚冬梅
- 浅谈激发和培养学生学习兴趣的原则 / 柏洪芳
- 职高语文教学之我见 / 周 勇
- 在愉悦的气氛中学好知识 / 张顺土
- 浅析《民事诉讼法》课程的教学改革 / 崔玉华
- 阅读教学中教师角色的转变 / 王文忠
- 《隔海相望》教学浅谈 / 许仕中
- 浅议本科体育教学中的弊端 / 王永志
- 浅析中学教学与信息技术的整合 / 刘明亮
- 高职院校体育师资的现状分析 / 宋 辉 周艳杰
- 浅谈语文课堂教学 / 李显顺
- 略谈高一学生走出学习困境的策略 / 罗国浩
- 对学生篮球裁判员手势基本功的培养 / 单思葵
- 农村小学体验性作文教学之探析 / 卢伟伟
- 刍议当前语文课堂教学评价 / 石刘保
- 《演讲与口才》课程教学设计 / 肖守琴
- 活化信息技术课堂 培养学生学习能力 / 田念祖
- 班级管理与德育教育 / 姚君安
- 语文教学需要模式吗 / 王玲英
- 加强教学技巧提高教学效果 / 田海忠
- 让学生在和谐中成长 / 白永强
- 课堂教学中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 金 玲
- 教学中类比方法的应用 / 常和梅
- 中学班级管理探索 / 张孝顺
- 小学语文教学创新谈 / 王 梅
- 提升师德品质打造魅力教师 / 陈俊秋
- 论教育技术理论研究中关注新兴媒体的必要性 / 李国文 魏红霞
- 母性奏响的浪漫牧歌 / 王佳静
- 课堂是师生生命成长的主阵地 / 赵 华
- 作文评语之我见 / 郑培炜
- 寻觅人的本真反抗荒诞世界 / 李照冰
- 班主任工作经验谈 / 马廷桂
- 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 张春英
- 初三语文教学感想 / 程 洁
- 信息技术与小学语文教学协同整合研究 / 孔 娟 朱酉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