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语文教学与研究·综合天地 2011年第11期
ID: 140849
语文教学与研究·综合天地 2011年第11期
ID: 140849
陌生之旅
◇ 陈青山
华莱士·马丁在其著作《当代叙事学》中指出:“在绝大多数当代叙事作品中,正是叙事视点创造了兴趣,冲突,悬念乃至情节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讲,作家在一篇小说中采用什么样的视角,有时候是判断其作品成败的关键点。朱山坡的《小五的车站》因为选择了独特的少年视角而让整个故事充满张力。青春期是人生中的一个特殊阶段,少年人在生理上开始出现一些显著的变化,心理上也对周边万物敏感起来,处于一种好奇而困惑的生存状态。他们既没有摆脱童年的懵懂天真,也未能完全地认知和融入社会,是区别于儿童和成人世界的“他者”。站在他们的角度来说故事,能捕捉到成年人忽略或者已经习以为常的感觉,产生异于其他视角的陌生化效果。
对故事里的小五而言,这是一趟完全陌生的旅程。一个人第一次出远门,拥挤的火车,互不相识的旅客,只知道下车的地点是一个叫玉林的小站。他觉得一切都很新鲜,同时心存戒备,以至于自己的座位被人占了,也只是当了一回阿Q,在心理上暗暗较劲,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这种少年人独有的心理活动,加上故事大多发生在黑夜,奠定了小说悬疑压抑的基调。不过少年人总能找到乏味旅程的刺激点,对面坐着的一个年轻女人给小孩喂奶的动作,唤起了小五潜藏的性本能,“在我的眼里,世界上最陌生、最新鲜的东西便是喷着新鲜乳汁的乳房”。他的内心里交织着欲望、善良和胆怯,用自以为“勇敢”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爱憎。当一个彪形大汉涎着脸盯着女人的胸脯时,他认为“身为她的保护神”,应该严厉阻止这种亵渎美的行为,于是“大胆”地放了一个响屁。此外,少年人往往偏于感性,看人做事以第一印象为准,小五不喜欢胡子拉茬的男子,对哺乳的少妇一见“倾心”,都是基于直觉的主观判断,这也导致他轻信了女人的“谎言”误了下车,成为改变情节走向的转折点。
在小说的前半部分,小五的身份是一个旁观者,他一直在看别人上演的戏码,内在汹涌的情绪在心理层面的潜流中回荡,除了咳嗽之外,连一句话都没说,叙述节奏相对舒缓。当读者以为故事就这么平淡地进行下去时,一个小插曲像一枚投入河面的石子,打破了眼前轻松愉悦的气氛——他坐过了站,今天已经没有火车去玉林了。在这之后,小说的节奏陡然加快,小五的身份变成了一个行动者,行文的重点也开始从心理活动向语言和动作场景倾斜。他慌张地跑向汽车站,被当成小偷揍了一顿之后也顾不上疼,打算沿着公路跑到玉林。对一个茫然无助的少年来说,在这个危急时刻,他需要一个英雄人物来指引他脱离困境。
这个英雄不是别人,恰是之前那头在火车上睡得很沉的“死猪”。他霸占了原本属于小五的位置,杂乱无章地打呼噜,在出站时调戏“女神”,是小五心中的大恶人。可是走在这条漆黑的泥路上,只有这个粗俗的男人和他的自行车能给小五安全感。无边夜色下,小五抓紧男人的裤袋,觉得他“粗壮的喘息,比呼噜还响,但没有呼噜讨厌”,修车时为了赶时间,男人“大声地骂街,骂得地动山摇要打要杀的”,扰人清梦是不对的,但这种冒险精神和大无畏的气势,正是小五缺乏并且期望的。等小五见到外婆时,男人已经默默地离开了。在这个刑满释放人员的身上,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一个真实人物可爱和可憎的两面性,他的性格充满矛盾而又和谐统一,闪耀着淳朴、善良的人性之美。在叙事性作品中,如果一个人物对整个事件的发展有推动作用,我们一般把他称之为人物的“行动元”作用,而其他人物对他性格的塑造就是“角色”的作用。小五是这次旅行的“行动元”,这个男子则很好地扮演了“角色”,在他的映衬和帮助下,小五青涩单纯的一面在无形中被放大,成功地区分了少年和成人的世界。
实际上,纯粹意义的少年视角是不存在的。年轻的写作者基本上还处于“少年不识愁滋味”的阶段,因此站在这些少年背后的大多是成熟的作家。就这篇小说而言,少年视角只是朱山坡用来创作的一个手段和工具,他是为了还原自我的旧时记忆,去找回那种泯灭已久的悸动和希望,还是热心地帮助少年来重构他们的成长历程?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每一个曾有过相似经历或心境的读者,都陪着小五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那个把小五带离恐惧和偏见的男人已经隐入雨幕,“我将再也看不到他”,不过没关系,每个人都必须经过这么一个脱离陌生的过程。这个少年经过这一夜的洗礼,对社会对生活已经有了崭新的认知,逐渐开始成长起来。
陈青山,男,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研究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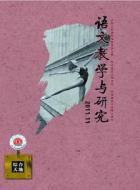
- 引领学生享受语文之美 / 张翠华
- 古代诗歌教学与审美教育 / 刘艳
- 小五的车站 / 朱山坡
- 陌生之旅 / 陈青山
- 教师专业发展的途径 / 董爱秀
- 如何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 / 谭义专
- 文言文翻译的几个小技巧 / 曹红
- 文言文教学的三重境界 / 赵红
- 重视学段之间的教学衔接 / 陈卫平
- 引导中职学生自主学习的策略 / 张泽良
- 在综合性学习中提升学生语文素养 / 刘涛
- 例说语文教学的人文性 / 李卉
- 文言文教学应加强诵读指导 / 牛传福
- 演讲比赛有助于提高学生语文水平 / 拉参
- 在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 / 杜丽娟
-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 范辉 王先福
- 快乐语文教学法 / 马婷
- 让学生真正成为语文学习的主人 / 沈小娟
- 语文教学中如何实施有效评价 / 王正属
- 让诵读成为文言文教学的敲门砖 / 陈成
- 高中语文教学中的美育渗透 / 房丽
- 在课文空白处插上想象的翅膀 / 吴广华
- 思悟课堂下的高中语文阅读教学策略 / 袁艳磊
- 学生创新思维的激发方式 / 吴培河
- 文本解读新思考 / 杨秀雯
- 简约型阅读教学的有效策略 / 仲雪箐
- 让阅读成为培养学生想象力的主阵地 / 徐爱兰
- 阅读教学要做到四个到位 / 孙联东
- 多则材料作文的审题方法 / 姜悦
- 如何加强农村初中生的课外阅读 / 崔春
- 网上冲浪对学生写作的影响 / 王帅
- 对作文教学现状的理性思考 / 赵昌福
- 阅读教学中教师的主导作用 / 姚娜
- 课外训练写作可以扭转作文僵局 / 王泽田
- 化用古诗文让作文熠熠生辉 / 孙奎彦 葛兰云
- 阅读教学主问题的定位策略 / 吴美凤
- 让写作之花自由盛开 / 时粉钧
- 中学作文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 蒋锡娟
- 《我与地坛》对中学生写作的启示 / 王佳
- 农村中学作文教学反思 / 陈桂香
- 信息技术与课堂探究式学习模式 / 丁海蓉
- 转变教学方式打造全新语文课堂 / 刘如英
- 拔响课堂求知的心弦 / 王雪芹
- 语文课堂教学流程评价的几个关注点 / 陈贵有
- 多媒体在语文教学中的作用 / 李春伦
- 互动的课堂精彩纷呈 / 韩振芳
- 语文课堂活动的探索与实践 / 杨顺琴
- 课堂提问要问出层次 / 侯彦君
- 以学生的说激活课堂 / 曹旭东 龙美蓉
- 如何提高语文课堂教学效果 / 姜汉梅
- 语文课堂教学中的结课艺术 / 许瑞军
- 给学生一瓢灵动的“活水” / 刘云飞
- 让生活点亮语文课堂 / 刘方玲
- 新课标下的导入教学 / 苏中原
- 活动单导学课堂中教师的作用 / 丁佐林
- 《林黛玉进贾府》中的衣纹学 / 刘元朋
- 语文课堂中教师要善于引导 / 成克刚
- 六有互助教学模式浅探 / 赵艳艳
- 在言语实践中获得语言的活性 / 蒋辉
- 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应心存敬畏 / 方忠木
- 例说散文教学内容的确定 / 杨兆红
- 体验活动作文教学设计 / 孙秀琴
- 《氓》创新教学设计 / 李文光 万美莉
- 如何创设良好的教学情境 / 李家峰
- 《猫》的探究式教学设计 / 王芳
- 现代信息技术在课堂教学中的运用 / 田晋敏
- 《与韩荆州书》第二课时教学设计 / 杨艳苓
- 高中语文体验式阅读教学初探 / 朱曼雯
- 谈谈我国中小学语文教材中的基本篇目 / 肖建云
- 《家》和《雷雨》中少爷与丫环的爱情 / 刘于飞
- 心理定势引起学习障碍的成因及对策 / 刘铭
- 语感培养的方法与步骤 / 夏月香
- 关于语言学习的思考 / 余芳
- 新材料作文的审题立意 / 李何云 来五星
- 高考作文突显个性的基本技巧 / 葛彩云
- 古代诗歌鉴赏题五大置疑角度 / 李绪文
- 他山之“实”可以攻“语” / 郭毅峰
- 浅谈高中语文教学的有效性 / 蒋建祥
- 高中语文有效教学的误区与对策 / 尹兰珍
- 自育式学习方略在名著阅读中的运用 / 张五芳
- 教会学生在阅读中品味语言 / 刘秀云
- 语文教学与多媒体技术的整合 / 李健
- 语文自主学习中需解决的问题 / 刘丛光
- 语文教学新课改的反思 / 赖建萍
- 语文拓展教学的根在何处 / 白现峰 吕茂峰
- 语文教学对传统教育的继承与创新 / 杜江伟
- 致女儿 / 陈新萍
- 职业学校教师职业倦怠问题及对策 / 李春桃
- 文人的居所 / 程丽
- 基于传统文化理念的小学语文教育 / 匡翠娥
- 餐桌上的语文 / 胡裕林
- 爷爷的象棋 / 蔡晨
- 构建三维课堂模式 提升课堂教学效率 / 帅亚成
- 语文教学与民族精神的培养 / 李庆泉
- “爬楼梯”与教育转型 / 汪厚旬
- 读书是对语文教师的必然要求 / 李慧
- 在语文教学中进行德育渗透 / 夏红霞
- 在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健康的心理 / 彭仕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