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语文教学与研究·综合天地 2011年第11期
ID: 140901
语文教学与研究·综合天地 2011年第11期
ID: 140901
《林黛玉进贾府》中的衣纹学
◇ 刘元朋
“人是衣服马是鞍”,“佛靠金装,人靠衣装”,“三分人才,七分打扮”,这些俗话虽失之偏颇,却也道出了衣饰打扮在人物美中的作用。中华是个衣冠古国,全人类的衣饰之考究精美,没有能与中国比拟的。衣饰也是人的身份、性情、风度、处境的“标志”,令人一望而可以大致判断此为何许人也。黑格尔曾说:“人通过改变外在事物来达到这个目的,在这些外在事物上面刻下他自己内心生活的烙印。”又说,“不反对外在事物的人是这样办的,就是对他自己,他自己的自然形态,他也不是听其自然,而要有意地加以改变。一切装饰打扮的动机也就在此。”所以,在小说中写人,无不先“交待”此人如何“穿戴”的,说评书也免不掉这一节。谁带一项“中冠”,谁穿一件“蓝绸直裰”,谁蹬一双“小靴”,总有那么几句。
曹雪芹虽不落窠臼,但没有废除衣饰的叙写,倒是加强了细度。雪芹为何注重这个“外表”?因为他是位大画家。画人物除了“头脸儿”,神态是用功夫的部位,不待赘言之外,另一重要的就是“衣纹”。而曹雪芹描写衣纹之巧妙绝伦,堪用“衣纹学”来称呼。
《林黛玉进贾府》一回中,雪芹借黛玉之眼,来写出府中人物的衣饰,譬如王熙凤——
……这个人打扮与众姊妹不同,彩绣辉煌,恍若神仙妃子——头上戴着金丝八宝珠髻,绾着朝阳五凤挂珠钗,顶上带着赤金盘璎珞圈,裙边系着豆绿宫绦,双衡比目玫瑰佩。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褃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
可谓极力铺陈、工笔重彩!在衣饰上选取了头饰、裙饰和服装三个点道出了王熙凤珠光宝气及俗不可耐的特点,也反映了她内心的空虚。“那些偶像穿戴和装饰得看起来很华丽,但是,可惜!他们是没有心的。”达芬奇也曾说:“你们不见美貌的青年穿戴着朴素无华的衣服反比盛装的妇女美得多么?”过分的装饰,往往反映内容的空虚,求美反而失去美,甚至得到的是丑。曹雪芹写王熙凤的衣纹,收到了上述美学效果,使我们对王其人有了深层次的了解。
至于宝玉,在本回则是叠笔——
一语未了,只听外面一阵脚步响,丫鬟进来笑道:“宝玉来了!”黛玉心中正疑惑着:“这个宝玉,不知道是怎生个惫懒人物,懵懂顽童?——倒不见那蠢物也罢了。”心中想着,忽见丫鬟话未报完,已进来了一位年轻的公子:头上戴着束发嵌宝紫金冠,齐眉勒着二龙抢珠金抹额;穿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剪袖,束着五彩丝攒花结长穗宫绦,外罩石青起花八团委缎排穗褂;蹬着青缎粉底小朝靴。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桃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面如桃瓣,目若秋波。虽怒时而若笑,即瞋视而有情。顶上金璃璎珞,又有一根五色丝绦,系着一块美玉。……一时回来,再看,已换了冠带:头上周围一转的短发,都结成小辫,红丝细束,共攒至顶中胎发,总编一根大辫,黑亮如漆,从顶至梢,一串四颗大珠,用金八宝坠角;身上穿着银红撒花半旧大袄,仍旧带着项圈、宝玉、寄名锁、护身符等物;下面半露松花撒花绫裤腿,锦边弹墨袜,厚底大红鞋……
只这一段,叠写了宝玉的两处衣纹,宝玉便活现于纸上,在黛玉眼里的宝玉分明是一个眉清目秀、英俊多情的年轻公子,不但看不出有什么惫懒与懵懂,而且眼熟,产生亲切感。其实,在整部《红楼梦》中,曹雪芹对男人的衣饰一字不屑去写(严格之至)。宝玉虽为男性,却写他的衣饰,而且是重笔叠笔。何也?雪芹著书不为男子,只传女儿,宝玉虽属于男,但性与女亲,甚异于世俗“浊物”——原系一部书的真正主人公,故持笔“优待”。
在“黛玉入府”一回中,除宝玉外,雪芹也是只写女儿衣饰,对迎春、探春、惜春,虽只是一笔带过,“其钗环裙袄,三人皆是一样妆饰”,但也不放过。即使写与“别家不同”的丫鬟,也有一句“只见一个穿红绫袄青缎掐牙背心的丫鬟”。宝玉初见黛玉,只写她眉眼态度,却一字不提衣饰。难道在大家心目中位置最高最重的女主角,倒不需要写她出场亮相的打扮?——而且整部《红楼梦》中,也没有写她的衣饰(只在“白雪红梅”回中写了她的斗篷和小靴。当时写众人斗篷各异,当然包括黛玉。)这恐怕就是曹雪芹对她这个人有一种超衣饰的认识,此为一画衣饰,会把她“框”住了,即“定型化”了。他以为一些她的衣饰会有害无益,有损黛玉的形象,像黛玉这种人是不需衣饰的,不用包装的。而衣纹服饰这些外在的东西,正是曹雪芹所不齿的。
在《林黛玉进贾府》中,可以看出曹雪芹的“衣纹学”,我们也能领会到《红楼》艺术的真魅力之所在,可以体会到《红楼》“衣纹学”的美学价值。
刘元朋,教师,现居山东平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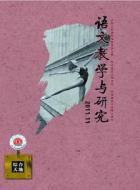
- 引领学生享受语文之美 / 张翠华
- 古代诗歌教学与审美教育 / 刘艳
- 小五的车站 / 朱山坡
- 陌生之旅 / 陈青山
- 教师专业发展的途径 / 董爱秀
- 如何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 / 谭义专
- 文言文翻译的几个小技巧 / 曹红
- 文言文教学的三重境界 / 赵红
- 重视学段之间的教学衔接 / 陈卫平
- 引导中职学生自主学习的策略 / 张泽良
- 在综合性学习中提升学生语文素养 / 刘涛
- 例说语文教学的人文性 / 李卉
- 文言文教学应加强诵读指导 / 牛传福
- 演讲比赛有助于提高学生语文水平 / 拉参
- 在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 / 杜丽娟
-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 范辉 王先福
- 快乐语文教学法 / 马婷
- 让学生真正成为语文学习的主人 / 沈小娟
- 语文教学中如何实施有效评价 / 王正属
- 让诵读成为文言文教学的敲门砖 / 陈成
- 高中语文教学中的美育渗透 / 房丽
- 在课文空白处插上想象的翅膀 / 吴广华
- 思悟课堂下的高中语文阅读教学策略 / 袁艳磊
- 学生创新思维的激发方式 / 吴培河
- 文本解读新思考 / 杨秀雯
- 简约型阅读教学的有效策略 / 仲雪箐
- 让阅读成为培养学生想象力的主阵地 / 徐爱兰
- 阅读教学要做到四个到位 / 孙联东
- 多则材料作文的审题方法 / 姜悦
- 如何加强农村初中生的课外阅读 / 崔春
- 网上冲浪对学生写作的影响 / 王帅
- 对作文教学现状的理性思考 / 赵昌福
- 阅读教学中教师的主导作用 / 姚娜
- 课外训练写作可以扭转作文僵局 / 王泽田
- 化用古诗文让作文熠熠生辉 / 孙奎彦 葛兰云
- 阅读教学主问题的定位策略 / 吴美凤
- 让写作之花自由盛开 / 时粉钧
- 中学作文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 蒋锡娟
- 《我与地坛》对中学生写作的启示 / 王佳
- 农村中学作文教学反思 / 陈桂香
- 信息技术与课堂探究式学习模式 / 丁海蓉
- 转变教学方式打造全新语文课堂 / 刘如英
- 拔响课堂求知的心弦 / 王雪芹
- 语文课堂教学流程评价的几个关注点 / 陈贵有
- 多媒体在语文教学中的作用 / 李春伦
- 互动的课堂精彩纷呈 / 韩振芳
- 语文课堂活动的探索与实践 / 杨顺琴
- 课堂提问要问出层次 / 侯彦君
- 以学生的说激活课堂 / 曹旭东 龙美蓉
- 如何提高语文课堂教学效果 / 姜汉梅
- 语文课堂教学中的结课艺术 / 许瑞军
- 给学生一瓢灵动的“活水” / 刘云飞
- 让生活点亮语文课堂 / 刘方玲
- 新课标下的导入教学 / 苏中原
- 活动单导学课堂中教师的作用 / 丁佐林
- 《林黛玉进贾府》中的衣纹学 / 刘元朋
- 语文课堂中教师要善于引导 / 成克刚
- 六有互助教学模式浅探 / 赵艳艳
- 在言语实践中获得语言的活性 / 蒋辉
- 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应心存敬畏 / 方忠木
- 例说散文教学内容的确定 / 杨兆红
- 体验活动作文教学设计 / 孙秀琴
- 《氓》创新教学设计 / 李文光 万美莉
- 如何创设良好的教学情境 / 李家峰
- 《猫》的探究式教学设计 / 王芳
- 现代信息技术在课堂教学中的运用 / 田晋敏
- 《与韩荆州书》第二课时教学设计 / 杨艳苓
- 高中语文体验式阅读教学初探 / 朱曼雯
- 谈谈我国中小学语文教材中的基本篇目 / 肖建云
- 《家》和《雷雨》中少爷与丫环的爱情 / 刘于飞
- 心理定势引起学习障碍的成因及对策 / 刘铭
- 语感培养的方法与步骤 / 夏月香
- 关于语言学习的思考 / 余芳
- 新材料作文的审题立意 / 李何云 来五星
- 高考作文突显个性的基本技巧 / 葛彩云
- 古代诗歌鉴赏题五大置疑角度 / 李绪文
- 他山之“实”可以攻“语” / 郭毅峰
- 浅谈高中语文教学的有效性 / 蒋建祥
- 高中语文有效教学的误区与对策 / 尹兰珍
- 自育式学习方略在名著阅读中的运用 / 张五芳
- 教会学生在阅读中品味语言 / 刘秀云
- 语文教学与多媒体技术的整合 / 李健
- 语文自主学习中需解决的问题 / 刘丛光
- 语文教学新课改的反思 / 赖建萍
- 语文拓展教学的根在何处 / 白现峰 吕茂峰
- 语文教学对传统教育的继承与创新 / 杜江伟
- 致女儿 / 陈新萍
- 职业学校教师职业倦怠问题及对策 / 李春桃
- 文人的居所 / 程丽
- 基于传统文化理念的小学语文教育 / 匡翠娥
- 餐桌上的语文 / 胡裕林
- 爷爷的象棋 / 蔡晨
- 构建三维课堂模式 提升课堂教学效率 / 帅亚成
- 语文教学与民族精神的培养 / 李庆泉
- “爬楼梯”与教育转型 / 汪厚旬
- 读书是对语文教师的必然要求 / 李慧
- 在语文教学中进行德育渗透 / 夏红霞
- 在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健康的心理 / 彭仕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