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语文建设·下半月 2015年第8期
ID: 422698
语文建设·下半月 2015年第8期
ID: 422698
论《诗经》的音乐性与结构探析
◇ 杨健
摘要:《诗经》是我国流传下来最早的文献之一,居于“六经”之首位。《诗经》的结构以四言和三段式的重复结构为主,这和几千年前人们的审美心理是分不开的。本文从《诗经》的韵律语言开始探讨,分析了齐言之乐与长短句之乐的差别,最后针对《诗经》的结构进行阐释。
关键词:古诗词 音乐韵律 诗词结构 空间结构
引言
从古至今,对于《诗经》的研究数不胜数。尤其是近现代,对于《诗经》的研究成果的角度各不相同,如果单纯将其作为音乐韵律方面的研究明显是浅薄的,对《诗经》的研究直接影响到对其艺术本体认定的问题。首次提出将音乐看作是《诗经》分类标准的是宋代的郑樵,渐渐地,这种观点被诸多学者所认同。后续很多的学者包括顾炎武、朱熹、章炳麟、梁启超等人都认同《诗经》的《风》《雅》《颂》的划分标准是音乐,《诗经》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几千年前的周朝文明将“礼”作为核心的文化,周朝的“礼”主要体现在当时贵族们经常举行的礼典方面,这是《诗经》中所收录诗文的大时代背景。以上对《诗经》的研究已经基本上形成了共识。诗歌的形式比较短,而且语言精练,结构紧凑。但是,《诗经》的《风》并没有沿袭这种诗歌形式,但是其内在的感情和自然质朴的语言却使得诗歌达到了一种“晦其光而得其璞”的优美境界。《诗经》中所收录的诗歌在语言、结构方面都成为后人竞相学习的对象。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诗经》的音乐韵律与结构特点。
一、《诗经》的音乐韵律语境
由于《诗经》的韵律强弱直接与押韵效果相关,所以在研究《诗经》时,首先需要了解音乐韵律语境。例如最典型的例子是学者王力在其著作《诗经韵读》里总结了《诗经》中诗歌的押韵情况,书中表达了押韵的三个方向:第一,“韵”在《诗经》中整体的位置,包括虚字脚、韵与非韵、韵脚;第二,“韵”在《诗经》中章节的位置,这种情况又细分为四种位置:一“韵”到底,两韵以上的诗章,疏韵、密韵、叠韵、无韵、叠句;第三,“韵”在《诗经》中篇中的位置,分为整齐和参差、尾声、遥韵、回环……四种类型。而在《古代汉语》一书中王力认为:“《诗经》305篇里仅仅8篇无押韵现象,这7篇全部集中在祭祀诗里”。但专家们根据王力的《诗经韵读》一书来分析“韵律”,整篇“无韵”现象的8篇全部集中在《周颂》里。再加上学者符定一编写的《联绵字典》一书中,了解到《诗经》里除去46个篇目之外,都有连绵词的现象。《诗经》中韵律语境下连绵词的应用需要从读诵时的语速、节奏、押韵及平仄等各方面来了解。为了更好地分析《诗经》中韵律语境,可以以此作为研究对象,将其框定在是否押韵的框架中,分析连绵词与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分析其押韵的情况,再来对韵脚等进行全面分析。
二、《诗经》的齐言与长短句之乐
《诗经》一共收录了三百多篇诗歌,严格来讲,“齐言之乐”就占了将近一半的数量。其中,《诗经·风》这部分的齐言之乐就有八十多首,《诗经·雅》这部分则有近六十首,《诗经·颂》这部分有将近二十首。这一百多首齐言之乐中大都是“四言齐言”,只有《魏风·十亩之间》一首除外,它是五言齐言。由此我们可以进行初步的判断,齐言之乐的曲调都具有节奏工整、语言整齐的特点。四言句式也较容易规整,便于民间流传与传颂。
除了齐言之乐以外,其他的诗歌都是长短句之乐,也占据了一半的数量。其中,在《风》这部分长短句之乐有八十多首,《雅》这部分有五十多首,《颂》这部分占据了三十首。基于这些数据分析,看似是长短句之乐的数量多于齐言之乐,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在《诗经》一共有七千多句诗句,其中百分之九十多都是“四言”句,剩下不到百分之十的是非四言句,由此可见语言工整的四言诗体是《诗经》的主要语言形式。经过仔细分析我们发现,即使是齐言之乐的数量比不上长短句之乐,但是从整体上看大多数的诗歌句式仍旧是以四言为主。除个别的句子长短不齐外,可以说长短句之乐占整体比重并不多。[1]
《诗经》主要是入乐演唱的乐歌文体,歌词语言和歌风必然要符合当时的音乐特点,也因此造就了《诗经》的四言为主、较为朴素的音乐韵律语言风格。归根结底,对其工整结构和韵律语言风格起到决定性因素的还是它直接受到当时礼乐文化的深刻影响。首先,周礼尚和的观念影响了《诗经》的创作内容。《诗经》中言语敦厚,其思想观念充分表示出了“和”的内在涵义,对《诗经》创作产生观念影响。其次,礼为乐辅、器为乐设造就了《诗经》语言的韵律特质。《诗经》中的乐器描写大多数都是早期的打击乐器钟、鼓、磬等,这类器乐的共同点是节奏感强。因此,其中的语言韵律必然是较平缓的语句。正是由于当时的审美习惯形成了舒缓悠扬的音乐特征,和当时节奏感相吻合的恰恰是四言诗体。所以,《诗经》的基本句式便是节奏感强的且舒缓的“四字齐言”。但是,这其中也离不开周代语言形式的影响。当时周代的语言形式刚刚突破二言形式,最新的四言诗句是最为合适的表达形式。这种形式对《诗经》创作的语言韵律产生影响。其优点是句式上稍有延长,更加能够充分地表达内心的情感。当说话人的情绪波动较大时,长短句的语言形式就显示出它独特的优点。但是要表达敦厚稳定的人类感情时,“四言齐言”当属最为合适的表达选择,因此《诗经》中齐言流传最多。有学者对《诗经》中长短句有精辟的诠释,他说《诗经》中诗句短非蹇也,长非冗也,其韵律节奏感是现代诗歌无法超越的。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诗经》中句式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以四言为基本句式。例如:《诗经》里面《国风》中的《周南·汉广》写道:“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在四言音乐韵律的吟咏中感慨生活。后又在“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的感叹中回归到了现实生活之中。此诗的韵律结构异常明显,吟咏朗朗上口。作者从现实到想象,又回到现实的结构,反映了对现实生活的深深遗憾。“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傩”,语句工整,尾字押韵,讲的是一群小伙伴在淇水边嬉闹的场景。诗中通过对童年故乡无忧无虑生活的描写,更加衬托出了时过境迁、尝遍苦辣的辛酸和悲凉,我们的心情也跟随作者“驾言出游,以写我忧”。这一韵律语言特点的形成其实和当时时代的音乐风格的韵律语言密不可分。
三、《诗经》的结构分析
《诗经》的空间结构也就是想象和现实这两种结构。通过想象和现实空间的转换来组织作品,虚虚实实,转接无象,但是看上去却又无不意脉贯通。由现实转入想象的虚空,进而开启无限的想象空间。立足现实,却通过思维的飞跃引向过去、未来或者是能够想象到的任何一方,这中间确是联系紧密的,对于想象的、虚幻空间的描述,突出人类对于理想期盼的同时,更加彰显了人们在现实中的生活状态。也是经由人们对梦想世界的描述,带给人们以无限的满足。《诗经》中的诗歌通过虚实空间结构的转换,给人结构上强烈的层次感和美感,这样不会产生因过分的直叙而引发的枯燥感。想象的虚空对现实产生出强烈的映衬作用,使得情感的表达更为激烈,它也可以是对现实的一个补充,将现实空间的感情更加清晰地表达出来。想象和现实空间的转换这一结构的应用,给诗歌增加了无穷的感染力。
《邶风·击鼓》这篇诗歌中尤其对空间表现得突出。战士们离家出征的路上,历经了重重困难和战乱,心里面是无比地凄凉。在这种饱受战乱的年代,将士们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能否活着回到故乡都是未知。诗中将士们回想当初在家中和爱人之间甜蜜的誓言,一幕幕越加清晰,深深地刻在脑海中,他们只有在梦中才能重温那甜蜜的时光。[2]每次的回忆都让人难以忘怀,可是每次回忆过后,回归到现实生活中,才发现自己仍然身处战乱的地方。每次回忆之后的回归现实都只会使人感觉到现实的痛苦,而且是感觉越来越痛苦,出征的将士们喊到“于嗟阔兮,不我活兮”,这是对他们内心的真实写照。此诗中由于想象和现实之间的转换,给此诗带来了非常明显的效应:对昔日快乐时光的回想,让将士们的情感更加生动真实。回忆过后,所展示的悲伤也更加令人印象深刻,也更能切身体会到那种无助的荒凉。这两种感情所形成的巨大对比,带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双方的情感都更加地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原来的甜蜜生活会让人感觉更加甜蜜,而现实的痛苦生活让人感觉到更加地痛苦,甜蜜和痛苦的落差加大,整篇诗的感染力由此而增强不少。
另外一篇诗作《豳风·东山》使得虚实之间的转换达到了顶峰,可称得上是想象艺术的代表作。和上一篇诗相同,它们都是通过将士的回忆来展现全诗的感情对比。所不同的是,此诗是将士在回家的途中所作出的想象,在我们面前形成了几幅画面,第一幅是将士在离家从军征战途中的生活;第二幅是接近战场的村子,在这个场景中,将士们看到荒凉的村子,想到自己的家乡也可能如此,但是即使如此,那也还是家乡,只要能够回乡,那么一定要战胜归来;第三幅画面是战士想象当家人们知道我要归去的消息时,一定会安心快乐地打扫准备迎接;第四幅画面是将士回想到妻子美丽的笑脸,更加深了归家的迫切心情。[3]每一幅画面都是诗人强烈感情的传递。这些画面有机地统一起来,更加生动地展现出将士们在不同时空不同的心理变化,将离家出征的艰苦、对家乡和妻子深情的爱恋和重建家乡的信念等等感情都表露得更加深刻。实际上,本诗全篇丰富的情感正是通过结构上虚实转换和曲折的层次来表达的。《诗经》让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将四言作为诗文的基本句式,对某些字词进行变换是为了重复地吟唱,强烈的音乐韵律感让人感到朗朗上口,而段落则是以三段为主。这些特点都是我们研究和理解《诗经》上下文涵义、分清逻辑关系的重要依据。语
参考文献
[1]周振甫.诗经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2.
[2]闻一多.诗经研究[M].成都:巴蜀书社,2002.
[3]张晓娟.《诗经》音乐结构探微[J].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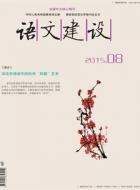
- 试论宋诗话中的杜诗“风格”艺术 / 黄关蓉
- 荒诞剧中的三维叙述视角探析 / 杜永青
- 网络文学审美影响研究 / 张敏
- 《飘》中主人公斯嘉丽形象研究 / 沈红
- 论对外汉语教学原则 / 黄蕾
- 语文教育对高校学生传统文化教育的影响与路径 / 杜海燕
- 基于生成性教学的高中作文课堂研究 / 张团思
- 高职院校语文的教学现状与对策探析 / 熊炜炜
- 景物描写学习:语文教学不该忽视的一隅 / 赵宏梅
- 高校语文教学的德育功能论略 / 李东
- 我国古代文学中的情景运用探讨 / 吴佳佳
- 关于构建高职语文教学模式的思考 / 刘娟
- 网络环境中大学生阅读心理研究 / 邓彦
- 探析英美文学《金色笔记》的叙事结构 / 刘秀云 李彦美
- 福克纳小说《野棕榈》的文本叙事研究 / 陶超
- 论王安忆《长恨歌》的叙事策略 / 罗忆南
- 《哈姆雷特》的“独白”语言话语评析 / 姚先林
- 红色经典《红岩》文学价值与启示研究 / 于兰
- 弗罗斯特诗歌的语言创作特点研究 / 卫娜
- 认知诗学理论下的外国文学阅读 / 曹鸿娟
- 《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的语言风格阐释 / 卢丙华
- 《爱玛》与《红楼梦》比较研究 / 刘瑞娜
- 论什梅廖夫作品中的主题内涵研究 / 孙忠霞
- 英国文学的叙事模式综述研究 / 杨眉
- 外国文学奈保尔《大河湾》中的意象阐释 / 东思伟
- 生态主义理论下莱辛文学作品评析 / 闫海燕
- 斯宾塞《牧人月历》诗歌特色阐释 / 张莹
- 书信体文学《克拉丽莎》叙事语言研究 / 周荻
- 象征主义在莎翁《雅典的泰门》中的呈现 / 陈修铭
- 小说《林海雪原》的文学叙事研究 / 赵艳艳
- 探索《赝品》中的人性光芒 / 陈华杰 刘洁
- 门罗短篇小说叙事策略研究 / 陈实
- 《热铁皮屋顶上的猫》中布里克疏离境遇的叙事修辞 / 邹园艳
- 外国文学对中国小说创作的影响分析 / 徐文君
- 对《飘》中典型女性形象的解读 / 王景明
- 对荒诞派小说《等待戈多》的文本分析 / 魏蔡连
- 《献给爱米丽的玫瑰》的英语教学设计 / 王秀芳
- 海明威文学作品专题教学研究 / 倪方
- 从谭恩美小说看中美教育观念的差异 / 贾继南
- 罗伯特·弗罗斯特及其诗歌中的象征主义浅析 / 杨东益
- 中西文化差异下对《鲁滨逊漂流记》的解读 / 谭丽娜
- 生态女权主义视角下对哈代小说的解读 / 李萌
- 英语语言隐喻在《夜色温柔》中的体现 / 张晶
- 《十一种孤独》的语言特征 / 周晓春
- 《榆树下的欲望》的模糊语言语义分析 / 黄玉秀
- 沈祖棻《涉江词》创作分析撷例 / 张悦
- 明代文学家赵贞吉的诗文题材 / 陈世英
- 日本文学《万叶集》的诗型与结构研究 / 彭程
- 李清照作品中的清新婉约与离别之愁 / 齐海棠
- 唐代文学作品中体育活动描写阐释 / 梁娟 赵凯
- 论《诗经》的音乐性与结构探析 / 杨健
- 汉语指人专名词语的语义泛化探析 / 王丹 吉晓光
- 频率副词“还”、“再”、“又”重复义之比较 / 王敏凤
- 汉语语言学中语义指向原则与结构研究 / 郭建华
- 论司马迁《报任安书》的语言修辞 / 付晓丽
- 大学生语言表达能力培养路径探索 / 贺广琰
- 论爱德华·萨丕尔的语言理论研究 / 李学勤
- 诠释的不确定性 / 刘俊英
- 功能主义理论下赖斯文本语言研究 / 刘霞
- 象征主义理论下爱尔兰诗人叶芝的诗歌语言 / 倪静
- 基于纽马克语言学的文本分类模式研究 / 姜莉
- 探析《爱玛》中的反讽语言艺术 / 刘宁宁
- 后现代语境下《哈姆雷特》语体研究 / 宋相瑜
- 语用交际功能视角下的语言翻译研究 / 闫丽俐
- 冲破标准,力臻完美:谈苏曼殊诗歌翻译风格 / 梁春丽
- 中国诗歌外宣翻译的语言特征解读 / 宣菡静
- 汉语语言迁移下的英语教学研究 / 杨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