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语文建设·下半月 2015年第8期
ID: 422675
语文建设·下半月 2015年第8期
ID: 422675
书信体文学《克拉丽莎》叙事语言研究
◇ 周荻
摘要:《克拉丽莎》作为书信体小说的典范,小说由一系列书信构成,在看似零散的形式下饱含了深刻的情节。作者通过书信形式将主人公的复杂情感展现出来。由于书信体小说本身存在文本内部、文本外部两种阅读进程,这种表述充满了不确定性。本文将会对小说中“密码”的含义与思想进行阐述。
关键词:书信体小说 《克拉丽莎》 不确定性
引言
《克拉丽莎》是一部以书信形式为主体的悲剧小说,由英国著名小说家理查逊于1747年与1748年间创作。这部小说完美地把小说内和小说外之间的关系通过书信形式呈现于读者眼前。两种不同的解密者存在于这部小说之中,即故事中以书信形式作为交流载体——四个人与阅读小说的读者之间形成互动。前者之间彼此争论、互相欺骗,使对方陷入煎熬;而后者在阅读这类以书信形式为主体的小说时,存在着话语和故事两种不同的概念,小说里人物与人物之间的书信往来被法国语言学者本维尼斯特归于“故事”这个分类,而读者阅读小说的行为则被其归于“话语”的分类。
一、密码的含义
在辛克莱尔家中,克拉丽莎将自己比作一个密码,把密码所含有的含义赋予了拉夫里斯,而选择将无尽的悲伤与痛苦留与自己一个人默默承受。关于孤独的独白,克拉丽莎没有任何的解释,只是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就像晴空万里的秋日天空中飞过一只鸿雁,只留下几声长鸣,当你抬起头想去寻找它的踪迹时却早已不见了踪影。但她那将自己比作密码的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就如那一声长鸣留给读者以无尽的遐想。她在不经意间将这个比喻与其所处的状态完美地契合。密码是她对自己的定义,拉夫里斯是一个解密者,而她就是那等待着被揭开神秘面纱的密码。更深一层来说,在克拉丽莎周边的人眼中,她同样是一个等待着被解读的密码;而对于现实世界的读者而言这本书同样是一个密码。对于阅读本书的每一个阅读者,《克拉丽莎》都是公平的,但不同的读者能从这相同的密码中解析出不同的答案,因为在阅读的过程中,这本书的文本也被阅读者们进行了二次创作。
通过书信这一载体,理查逊把小说内人物解码和小说外读者之间进行互动,在最后小说中所有人物的真实想法呈现在读者眼前。故事中的四个主人公将书信作为交流的载体,欺诈与被欺诈,煎熬与被煎熬,这一切都在他们之间进行着。而现实世界中的读者则是将自己带入了小说中的角色,并从这个角色之中将混乱的、没有秩序的线索一一进行解析。那些有着漏洞、分散的内容被读者抽丝剥茧,最终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每位读者的思想都是不同的,所以对文中各种线索的解读也是不同的,所以本应是一枝独秀的场面变成了百花齐放。
二、《克拉丽莎》的内容思想
解析《克拉丽莎》里的内容,并不像表面表现出来的那么简单,它所富有的含义更加广阔和让人难以琢磨。这本小说中,每一个角色都是破译文本活动中的一员。他们醉心于阅读信件,他们享受着阅读带来的快乐,也承受着随着阅读而来的迷惑。从创作角度上来说,阅读这种行为是本书中角色存在的根基。小说中故事内容由各个人物写给对方的书信所构成,托多罗夫对《一千零一夜》的阐释与描述我们可以用于此处,他认为:“在《一千零一夜》中,讲故事和听故事是被人们所依赖的,一个人是否存在于这本书中的唯一标识就是他是否有故事要讲给大家听。存在的意义是讲故事,否则便是死亡。”而在《克拉丽莎》中,尝试着解读是克拉丽莎存在的标识,她是作为一个信件的阅读者与接受者而存在。在这本书中,主人公把小说虚拟世界呈现在真实的读者面前,但在小说中主人公参与到创作中的最具代表性的行为便是阅读,阅读最基本的含义在他们身上得到了体现。但是小说中人物的这种阅读行为却向另一个方向发展,事件发展中的细枝末节他们都想去了解,他们想知道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所有事情的答案。小说中的人物都清楚自己的双重身份——参与事件的人和阅读书信的人。
《克拉丽莎》中解析密码是每一个出场的人物作为解密者所背负的任务,通过解码得到所谓的答案。作为一种基本文本单位——书信不仅仅是一种写作,更是一种阅读互动活动。《克拉丽莎》中的人物克拉丽莎、拉夫里斯等人物的内心表达可以界定为祈愿书信形式,用语言将他们的私人空间用书信诉说出来。法国批评家罗兰·巴特曾提出用语言把握现实,而在《克拉丽莎》中,写信行为验证了这一说法,变成了一种使自身价值得以体现的方式。每一个写信的人都带着自己主观色彩的眼睛去看待这个世界。小说世界里的人物阅读信件行为是对信件的理解与诠释,这是一种不信任他人与带有浓重的个人色彩的行为。小说中的人物用他们所特有的方式去诠释这些信件,却又在自己主观意识驱使下将这些信件浅尝辄止地加以理解,从而得出他们想要的结论,尽管这些被抽取出来的含义根本与信件的原作者意图没有丝毫的交汇。书信在这种错误的解读下变成了一种不能够确定的交流方式,传达作者意图这一最基本的目的无法实现。
这种不能够确定的方式使小说内容好似陷入了混乱,《克拉丽莎》中出场的人物(即信件的阅读者们)可以将他们所曲解出来的答案强加给任何人或事物。因为文字含义的多元化解读,不同的理解而产生的差异,各种千奇百怪的解释与看法充斥其中,每个人都试图发出自己的声音主导他人话语,把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强加于其他人物身上。而小说的男女主角克拉丽莎与拉夫里斯是这些不同声音中的两个极端,他们对小说中的内容有着自己的看法,在书信这个载体的承载下呼吁发出自己的声音。克拉丽莎单纯地看待这一切,满怀善意地阅读并诠释拉夫里斯的信件和他曾经的行为,但她最后被拉夫里斯欺骗和玩弄于鼓掌之中。而拉夫里斯则将欺骗看成是世间万物的本质,即使对天真的克拉丽莎也不例外,他们的言语之争与观点差异的碰撞被书信这一形式完美地体现出来。
这场斗争并不止步于主观意识的碰撞,还延伸到了社会的层面上。克拉丽莎在这场斗争中没有优势,而她失败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她没有话语权,小说中观点与声音被压制和掩盖的总是她。人物安娜·豪与克拉丽莎的信件曾被拉夫里斯所截下并篡改,话语权的丢失是造成克拉丽莎悲剧收场最根本的原因。在书信体中,话语权通过纸笔工具表达,唾手可得的工具被拉夫里斯肆无忌惮地使用。他的特权不止于此,他还可以阻拦别人发信,还可以将自己的观点通过书信这个载体发送出去,因此克拉丽莎言说的权利遭到压迫甚至被禁止发声。《克拉丽莎》一次次地证明了人物话语权的重要性,话语权被谁所主导和掌握,谁就能做主人。
三、对《克拉丽莎》的外部形式解读
《克拉丽莎》作为一部以书信形式为主体的悲剧小说在当时轰动了整个文学界。女性对包办婚姻的抵抗,对新生活的渴望与追求在文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中产阶级平和的道德层面的说教与自由恋爱婚姻自由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克拉丽莎在英国家庭小说的大路上另辟了一条小径。关于故事的特性众说纷纭,有人说它意在弘扬女权抨击不平等的现状,并赞美了平和的人生追求;有人认为当时的社会结构与社会价值观在本文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由于很多读者将其作为一部普通的小说来阅读,作为一本书信体小说,《克拉丽莎》颠覆了传统小说的叙事方式,所以很多自相矛盾的观点被读者一一列举,这也为开放式的结局埋下伏笔。
书信体小说中,人物之间虚拟的信件交流构成了文章的主体,因此而区别于传统叙事小说的讲述。小说中不同性格的人物相互之间交流的载体——信件,成为了书信体小说剧情发展的线索。人物把自己的全部情感完全用书信准确表达是十分困难的事,所以发生了小说中人物误会了信的意思而做出错误的决定的事情,这一幕也常常在现实生活中呈现。所以小说的情节也是来源于生活,被作家创作加工又高于生活。
英国作家约翰·普瑞斯通认为理查逊的以书信形式为主体的小说具有独特性——人物的行动被出现在小说中的书信语言所代替。现实世界中的读者在辨别叙述者的过程中可以从情节发展上得到帮助,但是这些帮助是有限的,读者无法从这些零碎的线索中在明确的事实与说话人之间得到一个正确的判断。书信是书信体小说后续内容展开的线索,但这些充当线索的书信是被书中的主角以个人意志加工过的,因此故事的叙述者这一身份它们并不能胜任。而通过信件所叙述的故事,也并不是完全可信,也会存在着误导。如何去伪存真,在混乱的线索中摸索出正确的道路,这是在现实世界中的读者应该做的。
阅读这一行为充满了个人感情色彩,小说的真正含义并不取决于内容,而是取决于读者的态度。法国文学评论家罗兰巴特曾提出语言的随意性,并阐明了不同的环境下相同的读者对同一文章会有不同的解读,由此可以体现出在阅读过程中,读者并不只是被动地接受作者所传达的一切,也会在潜移默化中用自己的态度对文章进行二次创作,创作与阅读这两个过程是相依相存的。
综上所述,以书信形式为主体的小说《克拉丽莎》,不管是现实世界中的读者亦或是文章中的读者(出场的人物们),他们通过书信所了解的世界并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而极有可能是他们一厢情愿所虚拟出来的符号。而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书信也有可能是书内或书外的作者玩的一个文字游戏,通过这些文字所塑造出来的世界可能是被强加了某人的意识而着重放大某些表象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传统小说中那种“叙述的便是事实的”,这样的常理不再受到信任,事实与文字描述合一的思想被人们所怀疑。在以书信为主体形式的小说中,他们能指与所指不再紧密联系在一起,有可能是分离开的。语言学之父索绪尔所提出的“就语言而研究语言”在《克拉丽莎》一文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对于现实生活中的读者来说,《克拉丽莎》颠覆了传统小说驾驭在读者思想上的定势——小说中叙述的便是真实的。在《克拉丽莎》中语言充满了不确定性,想要知道事情的真相,就必须一层层地剥开伪装的外衣去找寻那被掩盖的本质。当然,这仅仅是个人所理解的本质,每一位读者在阅读中都参与了这本书的再创作,而最终的密码答案也是大相径庭的。语
参考文献
[1]布斯.小说修辞学[M].华明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2]托马斯·卡莱尔.文明的忧思[M].宁小银译.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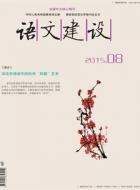
- 试论宋诗话中的杜诗“风格”艺术 / 黄关蓉
- 荒诞剧中的三维叙述视角探析 / 杜永青
- 网络文学审美影响研究 / 张敏
- 《飘》中主人公斯嘉丽形象研究 / 沈红
- 论对外汉语教学原则 / 黄蕾
- 语文教育对高校学生传统文化教育的影响与路径 / 杜海燕
- 基于生成性教学的高中作文课堂研究 / 张团思
- 高职院校语文的教学现状与对策探析 / 熊炜炜
- 景物描写学习:语文教学不该忽视的一隅 / 赵宏梅
- 高校语文教学的德育功能论略 / 李东
- 我国古代文学中的情景运用探讨 / 吴佳佳
- 关于构建高职语文教学模式的思考 / 刘娟
- 网络环境中大学生阅读心理研究 / 邓彦
- 探析英美文学《金色笔记》的叙事结构 / 刘秀云 李彦美
- 福克纳小说《野棕榈》的文本叙事研究 / 陶超
- 论王安忆《长恨歌》的叙事策略 / 罗忆南
- 《哈姆雷特》的“独白”语言话语评析 / 姚先林
- 红色经典《红岩》文学价值与启示研究 / 于兰
- 弗罗斯特诗歌的语言创作特点研究 / 卫娜
- 认知诗学理论下的外国文学阅读 / 曹鸿娟
- 《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的语言风格阐释 / 卢丙华
- 《爱玛》与《红楼梦》比较研究 / 刘瑞娜
- 论什梅廖夫作品中的主题内涵研究 / 孙忠霞
- 英国文学的叙事模式综述研究 / 杨眉
- 外国文学奈保尔《大河湾》中的意象阐释 / 东思伟
- 生态主义理论下莱辛文学作品评析 / 闫海燕
- 斯宾塞《牧人月历》诗歌特色阐释 / 张莹
- 书信体文学《克拉丽莎》叙事语言研究 / 周荻
- 象征主义在莎翁《雅典的泰门》中的呈现 / 陈修铭
- 小说《林海雪原》的文学叙事研究 / 赵艳艳
- 探索《赝品》中的人性光芒 / 陈华杰 刘洁
- 门罗短篇小说叙事策略研究 / 陈实
- 《热铁皮屋顶上的猫》中布里克疏离境遇的叙事修辞 / 邹园艳
- 外国文学对中国小说创作的影响分析 / 徐文君
- 对《飘》中典型女性形象的解读 / 王景明
- 对荒诞派小说《等待戈多》的文本分析 / 魏蔡连
- 《献给爱米丽的玫瑰》的英语教学设计 / 王秀芳
- 海明威文学作品专题教学研究 / 倪方
- 从谭恩美小说看中美教育观念的差异 / 贾继南
- 罗伯特·弗罗斯特及其诗歌中的象征主义浅析 / 杨东益
- 中西文化差异下对《鲁滨逊漂流记》的解读 / 谭丽娜
- 生态女权主义视角下对哈代小说的解读 / 李萌
- 英语语言隐喻在《夜色温柔》中的体现 / 张晶
- 《十一种孤独》的语言特征 / 周晓春
- 《榆树下的欲望》的模糊语言语义分析 / 黄玉秀
- 沈祖棻《涉江词》创作分析撷例 / 张悦
- 明代文学家赵贞吉的诗文题材 / 陈世英
- 日本文学《万叶集》的诗型与结构研究 / 彭程
- 李清照作品中的清新婉约与离别之愁 / 齐海棠
- 唐代文学作品中体育活动描写阐释 / 梁娟 赵凯
- 论《诗经》的音乐性与结构探析 / 杨健
- 汉语指人专名词语的语义泛化探析 / 王丹 吉晓光
- 频率副词“还”、“再”、“又”重复义之比较 / 王敏凤
- 汉语语言学中语义指向原则与结构研究 / 郭建华
- 论司马迁《报任安书》的语言修辞 / 付晓丽
- 大学生语言表达能力培养路径探索 / 贺广琰
- 论爱德华·萨丕尔的语言理论研究 / 李学勤
- 诠释的不确定性 / 刘俊英
- 功能主义理论下赖斯文本语言研究 / 刘霞
- 象征主义理论下爱尔兰诗人叶芝的诗歌语言 / 倪静
- 基于纽马克语言学的文本分类模式研究 / 姜莉
- 探析《爱玛》中的反讽语言艺术 / 刘宁宁
- 后现代语境下《哈姆雷特》语体研究 / 宋相瑜
- 语用交际功能视角下的语言翻译研究 / 闫丽俐
- 冲破标准,力臻完美:谈苏曼殊诗歌翻译风格 / 梁春丽
- 中国诗歌外宣翻译的语言特征解读 / 宣菡静
- 汉语语言迁移下的英语教学研究 / 杨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