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语文建设·下半月 2014年第12期
ID: 421414
语文建设·下半月 2014年第12期
ID: 421414
《白鹿原》艺术品位的重新评定
◇ 崔晓莉
摘要:陈忠实的《白鹿原》一经发表便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不仅仅获得了第四届茅盾文学奖,更被译为多国语言在世界上进行流传。本文通过对《白鹿原》的全面解读,通过该作品与作者早期作品的分析,试图重新对《白鹿原》这部鸿篇巨著的艺术品位进行评定。
关键词:《白鹿原》 陈忠实 艺术品位 重新评定
引言
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中一部不可忽略的经典之作,《白鹿原》凭借着严谨的故事结构、波澜壮阔的情节设置、丰满充实的人物形象和深邃的思想特征,成为“比之那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并不逊色(梁亮语)的大作品”。由于该作品的超高艺术成就,其先后被日本、韩国、蒙古等国学者引入介绍给国人。
一、从人物塑造角度重新评定《白鹿原》的艺术品位
通过分析陈忠实早期创作发表的小说,不难发现,在诸多早期作品中,陈忠实的人物塑造并不成功,众多人物形象基本上走的是“模板式”道路,人物性格往往扁平,并没有过多的特点以及复杂性,基本上属于可以一览无余型的,不要说体现出人格的复杂性以及深刻的人格内涵,连具备基本的鲜明个性特点都难以拥有。在其创作的早期作品中,可以发现早期的人物设定基本上都属于善良、勇敢具有传统美德的“好人”,尽管在其早期作品中也会出现一些具有性格缺陷的角色,然而这些人物经过一系列的经历后,最终无一例外地走向了人间正道,实现了人生选择的华丽转变。那些一开始便以好人面貌出现的角色绝大多数秉承与弘扬的是人间真善美精神,并且一直传承到故事结尾个别人性败坏的例子中,涉及到的具体人物性格构成十分单一,且一旦经过恶的侵蚀后便不再挣扎,整个心理活动便处于波澜不惊的状态,没有经过一点点的思想斗争与挣扎。这样的创作方式严重违反了人类本身的复杂性格特点与心理活动,创作人物难以深入人心。举例说明,在陈忠实的早期作品《尤代表轶事》中,作者便十分失败地塑造了尤喜明这个呆滞、平面化的角色。尽管必须承认,陈忠实在实际的创作过程中本来意图是想为读者展现出一个“真实”的人物形象,希望达到“使所有奇人异事相形见绌,黯然失色”的创作目的,然而由于创作经验的不足,陈忠实在体现人物特色时,并没有大量地运用情节渲染,从而达到塑造一个“现实生活中人物”的目的,一切都只是其自说自话,至于讽刺笔法的运用,也往往显得浮夸,无法收放自如,这使得作品中的主角尤喜明与实际生活中的人物有相当大的差距。而在创作《白鹿原》时,作者的人物塑造能力则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作者运用对比、讽刺、渲染等手法成功地塑造出了一个个有血有肉、生动形象的角色。在具体的故事展开中,作者运用原乡绅鹿子霖这个负面人物与白嘉轩的多次较量,通过具体的情节向读者展示出白嘉轩始终将仁义道德作为自己的信仰,鹿子霖却口蜜腹剑,工于心计,其本人不仅贪图私利,还十分好色,为了报复白嘉轩甚至不惜设计将白孝文拉入到自己的设计中,使得白嘉轩在族人面前丢尽了面子。在一系列的故事展现中,陈忠实成功地将鹿子霖这个大恶人的十恶不赦展现得入木三分,可以说通过与早期作品的对比,不难得出陈忠实在人物塑造上的不断完善与创新,使得其作品《白鹿原》在艺术品位上更加接近现实,易于被受众接受。
二、从象征手法的运用上评定《白鹿原》的艺术品位
陈忠实在早期的文学创作尝试中,并不注重修辞方式的运用,只是简单遵循着将现实经历过的生活体验生搬硬套运用到文学创作中去,最为致命的是在具体的文学创作中,陈忠实秉承的是肯定创作理念,这就造成了其文学创作中不可能出现富有鲜明生命力的人物形象,所有创作人物基本上都遵循着同样的创作模板,在对其早期作品的研究中,研究着几乎找不到一个成功富有鲜明象征形象的人物,其遵循的完美人物塑造原则,与《白鹿原》的创作特色有着十分鲜明的对比。即便在早期的文学创作过程中,陈忠实会或多或少地使用象征手法进行文学作品创作,然而这些创作手法都十分浅显,没有过高艺术水准的,通常只要简单地一扫便可以得出个八九不离十的结论,这样原始阶段的象征手法运用十分常见,举例说明,早期小说中的稍微能够体现象征意味的语段中,集中在故事展开过程中的自然景物及物象的描写上,作者在采用象征表达的时候,几乎都是通过对小说中天气的修辞方法展现,而且体现象征意味的手段还往往集中在对美好生活事务的赞扬和歌颂上,少有的象征手法运用不仅形式单一、枯燥,而且象征的内容也千篇一律,难以达到较高的艺术创作水平。举例说明作者在早期创作中为了体现出自己的象征目的,会机械、简单地运用点缀的修辞放置在《珍珠》《铁锁》《田园》《土地——母亲》《霞光灿烂的早晨》这一类缺乏实质象征意味,只单纯凭借着一个简单的意向就可以让读者猜测出作品的宗旨让人觉得兴趣索然。而《白鹿原》的创作过程中,作者告别了以往机械化的象征手法使用,选择将白鹿作为贯穿于作品始终的一个经典意象。作者不遗余力地将其塑造成为一个代表着真善美的象征,使其在整部作品中熠熠闪闪,举例说明:“那是一只连脚都是白色的鹿,白得像雪,蹦着跳着,又像是飞着飘着……”这样的创作方式不仅仅向读者展现了一个生动的白鹿形象,更为读者理解其美好的象征意味提供了直观而富有层次的意象,可以说象征手法的有效运用使得《白鹿原》这部作品在艺术品位上告别了以往低层次的简单创作手法使用,为其步入巨著行列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三、从语言方面的创作特色的运用上评定《白鹿原》的艺术品位
语言是构成小说的基本单位,语言的运用情况直接关系到小说能否被读者接受、认可,在陈忠实早期的文学创作过程中,其语言特征是句子朴实、干瘪,且通常有大段大段的句子构成,句子结构单一,平铺直叙是最基本的创作手法,比喻、拟人、夸张之类的修辞手段几乎没有运用,更少出现对情节以及人物心理的细微刻画,就好似一个步入迟暮之年的老人,失去了生机,一切语言运用都显得单调、乏味,叙事重点就在于叙事,并不注重对叙事目的和鼓励读者进行深入自考,尽管必须承认这种质朴、坚持求真的语言创作值得提倡,然而中国自古便拥有“做人要直,写文要曲”的创作理念,文学作品构思中以“不平”作为最高的创作标准,因此平铺直叙的创作手段并不一定能够达到良好的反馈效果。在《白鹿原》的创作中,作者有意识地进行曲写创作,例如,对比的使用,陈忠实在强调老太爷遗言已经深深地刻入每一个人的心里时,使用了“老太爷的尸骨肯定早已化作泥土,他的遣言却似窖葬的烧酒愈久愈鲜”的小说语言,不仅仅形象地说明老太爷已经离世相当长的时间,更能够用巧妙的对比,展现出人们对老太爷遗嘱的重视,尽管时光漫长,但是,每个人都会牢牢记住老太爷遗言,并坚决将其落实到自己的行为中。再比如双关语的使用,陈忠实在进行《白鹿原》创作中大量使用了谐音双关语,这在其以往的创作中是十分罕见的。举例说明,《白鹿原》故事中出现了史维华县长在被罢免后,上级指派何德治担任了新的县长,本县的居民便会在茶余饭后,纷纷议论“走了一个死(史)人,换了一个活(何)人,死的到死也没维持(维华)得下,活的治得住(德治)治不住还难说。”这样的创作方式,不仅仅揭示出了不同县长的姓名,也揭示出了这些人在本县人民心中的形象,更加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双关语还进一步地揭示了两任县长的不同命运,这样的语言表述方法使用极大地增强了作品可读性,通过多样化的语言表述,《白鹿原》在艺术品位上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对现实生活的体现,而是在充满曲折与深厚的意味和趣味下引导读者进行阅读。
结语
本文通过对陈忠实《白鹿原》的全面解读,通过该作品与作者早期作品的分析,得出丰富的人物形象塑造、象征手法的运用以及多元化的语言表述,是作品能够在艺术成就上拥有非凡品位的重要支撑,广大文学爱好者在进行文学创作时,必须要牢牢地把握住这几点,提高自身创作的水平。语
参考文献
[1] 李兆虹.黑娃论——解读《白鹿原》[J]. 名作欣赏,2011(05):465-467.
[2]贺敏.文化的颠覆与救赎——试论《白鹿原》的文化内涵[J].湖南社会科学,2013(02):354-356.
[3]夏爱华.穿越历史云烟回归心灵宁静——读陈忠实《白鹿原》[J].中国职工教育,2013(01):465-467.
[4]卫燕.关注历史深度与现实质感的王全安电影[J].剧作家,2013(02):680-682.
[5]付俊雄.从类型学角度论《白鹿原》及《百年孤独》[J].剑南文学:经典阅读,2013(03):580-582.
[6]房媛.陈忠实小说《白鹿原》中女人的婚俗观[J].剑南文学:经典阅读,2013(03):576-577.
[7]朱洁.无“代”时代的个性彰显——评电影《白鹿原》、《二次曝光》、《浮城谜事》[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3(01):543-5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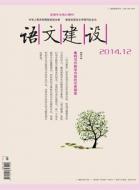
- 重构写作教学内容的可贵探索 / 张卫红 王学义
- 外国文学作品中的文化内涵研究 / 阎晓雅
- 巴尔扎克小说中的浪漫主义风格探究 / 任燕
- 由《老人与海》探析海明威的创作风格 / 董春华
- 品读《青春之歌》中的爱国精神 / 李剑虹
- 职业院校语文教学策略的创新研究 / 尚建乐
- 语文教师的继续教育发展问题研究 / 刘希富?宋大学
- 语文课堂教学活动的教育管理研究 / 陈玲玲
- 基于多元文化视角谈语文教学中的思政教育 / 宋喜荣
- 大学语文教学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分析 / 王海波
- 大学生就业实力和能力培养中大学语文的作用 / 相萌萌
- 论汉语教学对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 罗智勇
- 通识教育下语文教学对人才培养的创新研究 / 陆纯梅
- 高中语文活动课教学方法浅谈 / 黄卫华
- 课堂教学管理的人文素养培育功能探析 / 唐明?徐素珍
- 提高汉语文化教学层次,深入传播中华传统文化 / 张文莉
- 《简·爱》中语言特点与语用研究 / 李同奇
- 论莎士比亚悲剧的戏剧冲突 / 贺华
- 海明威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探析 / 冯小燕
- 从《雪国》看川端康成笔下的女性之美 / 宗瑛
- 《白鹿原》艺术品位的重新评定 / 崔晓莉
- 从《红楼梦》看曹雪芹的文学思想特点 / 雷玉梅
- 海明威作品中的女性意识探析 / 熊洁
- 自然主义视角下对《嘉莉妹妹》的解读 / 王燕
- 偏见下的诙谐 / 周媛?罗茜
- 狄更斯《远大前程》主题思想评析 / 杨天地
- 言语行为理论与《傲慢与偏见》中的反讽 / 李笑秋 蒋承
- 卡夫卡小说中蕴含的荒诞表现方式 / 许昌学院?王惠娟
- 《傲慢与偏见》中语言修辞艺术研究 / 赵雪
- 三生石畔三生爱 / 郑志平
- 意识流视角下小说《墙上的斑点》的解读 / 温晶晶
- 《荒凉山庄》中狄更斯文学叙事写作手法解读 / 李辉
- 苏轼和陆游豪放词异同研究 / 李紫薇
- 对《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中主题思想的解读 / 孔沛琳
- 论马克?吐温笔下的“男孩”形象 / 王婧媛
- 试论狄更斯作品中人物的双重人格塑造 / 刘国生
- 论《榆树下的欲望》中的悲剧冲突 / 杨春霞?李小艳?肖莉
- 浅谈《老人与海》陌生化手法的运用 / 霍向宁?李超
- 《红高粱家族》中生命意识与民族精神的解读 / 邓焱
- 《德伯家的苔丝》的悲剧意识解读 / 莫颖
- 海明威短篇小说叙事中“冰山原则”的运用及其艺术效果 / 何晴霞?詹悦兰
- 《金粉世家》中女性人物探微 / 王培
- 《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人物形象的解读 / 刘茂媛
- 美国生态文学与生态批评研究 / 李秀芝
- 海明威及其相关作品评析 / 李季美
- 普埃托拉斯短篇小说评析 / 余林茂
- 试论唐诗宋词中的民俗户外活动文化 / 王维朋?陈文继
- 中国古典诗词中的建筑艺术之美 / 徐阳杰
- 古诗词中女性体育活动的文学解读 / 王安治
- 现代汉语中的名词重叠现象 / 李红梅?杨天美
- 写作中常用的词语修饰 / 马晓刚
- 语境与对外汉语同义词辨析 / 王倩
- 特字“跪”的声母 / 邓楠
- 从《围城》看钱钟书的幽默讽刺艺术 / 左佳
- 英国文学家王尔德小说中的语言悖论研究 / 刘晓宁
- 亨利·米勒小说思想和语言关联性分析 / 莫宇芬
- 《桃花源记》“悉如外人”解读 / 刘富汉
- 古今字产生的原因和途径 / 许俊芳
- 易安词中“花”意象的认知解读 / 唐斌?王肖丽
- 网络热词“秒杀”“山寨”的生成及泛化研究 / 杨文忠
- 汉语教育下维吾尔族大学生语言态度问题研究 / 卡米力江·阿不都克力木
- 语言服务视角下的语言应用研究 / 刘素勤
- 普通高校艺术传播效果研究 / 可婷婷?王怡
- 《红楼梦》中刻意曲解对话的语用标记研究 / 刘琴
- 关于体育文学的内涵探析 / 王维
- 新媒体下英语语言对汉语语言的影响研究 / 马志馨
- 语文教育视角下体育专业学生文化素质的培养 / 杨木森
- 社会文化视域下的教师课堂话语研究 / 王艳
- 汉语词汇对英语语言的影响问题探究 / 粟芳
- 借鉴语文作文写作方式指导英语写作 / 朱晓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