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语文教学与研究·综合天地 2011年第6期
ID: 140449
语文教学与研究·综合天地 2011年第6期
ID: 140449
从《丹柯》看高尔基在中国的误读
◇ 郑燕明
对高尔基的印象,一直滞留于那只在暴风雨来临之夜疾呼“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的勇敢《海燕》,而高尔基的长篇小说《母亲》更强化了这一印象。事实上这也是高尔基及其作品在中国传播的主流方向,高尔基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为中国人民所景仰。
中国读者知道高尔基的《母亲》始于上世纪20年代末。1929年夏衍根据日文首先翻译《母亲》,小说人物的内容与中国人民所进行的革命很相似,所以高尔基的名字及其《母亲》这部小说很快被中国人民关注。20世纪30年代,经瞿秋白鲁迅等宣传推荐,尤其是中共中央1937年举行了一系列活动宣传纪念高尔基,更是让高尔基在为数不多的外国作家中以革命者的形象深入人心。在“高尔基热”中,高尔基被简单地符号化。而他作为文学家的复杂性和作品的丰富性被悄悄抹煞。对他的阅读走向程式化和政治化,则是对他的严重误读,更是作为艺术家的高尔基之大不幸。
外国小说选读中的《丹柯》,提供我们重新认识一个更为丰富饱满的艺术家高尔基的机会。《丹柯》改编自高尔基创作于1895年的《伊则吉尔老婆子》,是其早期浪漫主义代表作。高尔基通过对民间传说的情节和形象的借用,塑造具有高尚理想的新人丹柯形象。在族人面临困境即将灭亡之时,丹柯挺身而出,试图带领全族人走出“黑森林”。途中面对着族人的质疑、责难甚至生命威胁时,丹柯勇敢地掏出自己的心,照亮前行的路。当族人终于走出困境欢呼时,一个族人悄悄地“拿脚踏在骄傲的心上”,丹柯的心变成了散落在草原上的星星。这样一群哀伤、软弱、胆怯的人,丹柯仍旧怀着着对他们无私的“爱”,以宽容博大的胸怀,无比坚定的信念与意志和杀身成仁的牺牲精神,实现对族人的拯救。与过去《海燕》中勇敢无畏的革命者相比,丹柯多了一份对“人”的悲悯和同情。事实上,在高尔基的长长的一生里面,在他的全部著作里面,贯穿着一根耀眼的粗大的红线,那就是追求“无限的爱人们和世界”。如今反思我们多年的教学,正是这个“人”字在高尔基身上被忽视了。
丹柯并不因为族人身上存在的弱点而摒弃他们,甚至到最后他燃烧的心也被族人卑劣地践踏,他依旧没有怨言。这是源于对这个民族深切的爱,而不是简单的革命。《丹柯》虽是高尔基早期的浪漫主义作品,但完全可以把丹柯看做是高尔基一生的真实写照,一个充满了人道主义关怀的艺术家。
因为政治的因素,他的许多适合于社会主义现实派的作品被宣扬,其它作品却默而不言。鲜有人知高尔基曾写过《不合时宜的思想》一书,异常激烈地反对俄国十月革命。因为他认为俄罗斯民族还不成熟,大众还需要形成必要的知觉才能从他们的不幸中起义。过早的革命会使民众受到伤害,他认为“不应忘记,我们生活在亿万政治上一无所知,没有受过社会教育的庸人群众之中”(《不合时宜的思想》高尔基 花城出版社 2010年6月)正如丹柯对族人的悲悯一样,带领族人走出黑森林,开始新的生活。他提出“新一代的革命的重要任务就是创造能够建设国家的文化力量发展的各种条件”。高尔基也深刻认识到“在俄国不稳定的沼泽上‘播种’理智善良永恒‘是件极不寻常的艰难的事,而且我们已经知道,在俄国的平原上播种我们最好的鲜血,我们最好的神经液汁,也只能得到不太茂盛的可悲的力量,但是尽管如此也还是应当播种(《不合时宜的思想》同上)这是始终不失俄罗斯民族的“良心”却又不合时宜的先觉者高尔基,深刻而又“天真”,宽厚又是那样犀利,高远而又真实。
1998年《不合时宜的思想》一经与读者见面就引起了广泛而热烈的反响,让我们看到了更为悲悯的高尔基。如瞿秋白指出的,高尔基是“揭穿旧社会和一切欺骗的作家,他挖出了自己的心,把它的火焰来照耀走到新社会去的道路”(《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五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为了俄罗斯民族,高尔基愿意像丹柯一样付出自己的全部,而不仅仅是大声疾呼的海燕。他的悲悯情怀使得他对时代的认识有了前瞻性,然而在当时他的见解并没有被更多的人知道和了解,但他是一个永远时刻准备着为自己的民族献身的理想主义者,哪怕践行的道路上充满不解和误会,在戴着荣耀的光环下,他对民族的关切却这样不被同时代的人所理解,我们要全面了解高尔基也仍有很长的路,只有深刻理解了高尔基作为艺术家血液里流淌的悲悯,我们才能在教学中真正理解丹柯“举心照路”之壮举。
郑燕明,教师,现居浙江杭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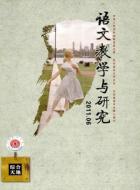
- 线性阅读教学课型论 / 陈祥春
- 兆吉 / 方格子
- 多元智能理论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 / 金辉
- 理想在别处 / 陈青山
- 有效朗读原来如此精彩 / 王平
- 经典诵读活动的开展 / 张青芬
- 有效解读应咬定文本 / 殷德忠
- 语文课外阅读课的研究与实验 / 楼利香
- 腹中藏诗书 笔下著美文 / 李玉莲
- 阅读教学中导语设计的有效性 / 戴志梅
- 整合阅读教学与探究性学习 / 李涛
- 初中记叙文写作教学中片段式训练 / 郭雄
- 文本整体把握的方法谈 / 杨海燕
- 小学作文教学浅析 / 陈耀芳
- 新课标下作文的选材 / 罗银龙
- 活化作文教学的三点心得 / 林潮
- 高中应用文写作教学的困境与对策 / 刘嘉
- 让学生在阅读活动中学会“发现” / 杨晓梅
- 作文材料积累的厚积薄发 / 王凡
- 浅谈《与朱元思书》的写作技巧 / 刘成
- 多元智能理论与阅读教学“互动” / 徐爱元
- 不再让作文成为拦路虎 / 狄奇静
- 议论文用例技法浅探 / 郭深山
- 语文教学“老三法”新谈 / 李鹏飞
- 创设语文情景 激发语文兴趣 / 姜霞
- 本色语文的整体思路和教学构想 / 杨益国
- 语文教学中的符号标划法 / 邢宗和
- 利用教材做好作文素材积累 / 刘俊峰
- 中学生创新作文写作三要素 / 李铃川
- 学生写作能力的培养 / 张智育
- 翻译与习作结合的尝试 / 潘信华
- 如何充分发挥语文教学的人文性 / 陈红
- 语文教学中的情感教育 / 张建军
- 突破文言文“言”的教学 / 赖凤翔
- 变传统的预习为备习 / 廖菊英 薛贻奎
- 阅读教学中有效对话方法的探究 / 刘家龙
- 利用教材进行读写结合的尝试 / 骆亮亮
- 小学语文课前的预习与预设谈 / 刘军
- 语文学习空间的开发 / 胡金凤
- 探讨古文的兴趣教学模式 / 蓝爱婕
- 在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独立意识 / 王言波
- 初中语文教学适应课改浅议 / 刘伟
- 语文课要上出情感味 / 孙贵红 孙怀平
- 古诗词教学要“三到” / 祝青娟
- 调动学生课堂积极性的有效对策 / 郁红剑
- 比较教学的好处 / 姚飞云
- 语文课堂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 谢晓艳
- 语文课的时代性需要强化 / 康吉松
- 让语文课堂“亮”起来 / 王云娟
- 在尝试中感悟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 陈柏文
- 作文教学中的互评 / 王玉琼
- 语文课提问初探 / 曾细胜
- 谈谈整体语言教学法 / 李彩香
- 初中语文“综合性学习”教学策略谈 / 肖友明
- 语文教学中的文字教学 / 袁瑞丽
- 语文课堂呼唤绿色提问 / 周妙芬
- 如何提高语文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 黄华招
- 苏教版《唐诗宋词选读》的美丽解读 / 梁民伟
- 影响教学语言艺术的几种因素 / 田华
- 《荷塘月色》和《天山景物记》中的“大美” / 谢增伟
- 《故都的秋》的艺术特色 / 胡蓉 周俊荣
- 新课标下的语文综合性学习 / 王凯
- 让语文活动课“动”起来 / 王彩娟
- 《故都的秋》中四组对比之我见 / 杨志康
- 《钱塘湖春行》《天净沙.秋思》教案 / 雷玲
- 《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教学设计 / 王安逸
- 在“预设”中“生成”课堂展示 / 杨权应
- 《明湖居听书》教学谈 / 曹峥嵘
- 比较探究型课程教法例谈 / 段书英
- 《归去来兮辞》执教札记 / 刘力 谢同育
- 八年级下册第一单元整合教学策略 / 贾树林
- 苏教版初中语文教材质疑 / 秦峰
- 从《丹柯》看高尔基在中国的误读 / 郑燕明
- 诗歌中的民俗教学 / 周爱群
- 《江城子.密州出猎》赏析 / 孙叶丽
- 学生语文自主学习之我见 / 姜勇军
- 新课程下课堂教学的改革 / 许娜
- 解读《史记》要抓好“审丑”的切入口 / 吴艳辉
- 高考写作生活化与个性化策略 / 谭志永
- 培养小学生语文创造思维的思考 / 贾玉君
- 文言文高效复习三字诀 / 张红宇
- 编制语文探究题应遵循的三大原则 / 吴军伟
- 说“托儿” / 詹英顺 苏静
- 关于农村中学语文创新教育的思考 / 周梅娟
- 多媒体在语文教学中的弊端 / 田红玲
- 学生口语交际中的听与评 / 姚海燕
- 古诗文中的数学味 / 张少伶
- 浅谈初中生的养成教育 / 陈绍良
- 农村作文教学之路探幽 / 张春华
- 栖息在梦想之源 / 武旸
- 致妈妈的一封信 / 王佳红
- 旗袍 / 蔡慧
- 让语文课堂成为创新精神培养的殿堂 / 王东生
- 如何在语文教学中渗透思想教育 / 杨建宏
- 拓展小学生语文学习空间的策略 / 吴兴林
- 那场雪 / 陈丹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