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语文教学与研究·综合天地 2011年第6期
ID: 140434
语文教学与研究·综合天地 2011年第6期
ID: 140434
苏教版《唐诗宋词选读》的美丽解读
◇ 梁民伟
[教情呈现]:
师:《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表达的是思念家乡的伤感。《滕王阁》抒发的是时移物换的沧桑。《春夜别友人》表现的是与友人分别时的愁思。《春江花月夜》传递的是人生短暂宇宙无穷的感伤以及对情人的深深思念。
《与诸子登岘山》、《望月怀远》……
生:老师,为什么我们学的这些诗歌总让人感到愁苦呢?诗人们难道就没有快乐的时候吗?
许多学生都附和:是啊!是啊!太悲了!上得人越来越没劲。
面对学生们不胜其悲的样子,我也觉得深有同感:是啊,才上了两个专题十二首诗,倒有八首诗明确表达出伤感的情绪,另外四首诗也或多或少跟伤感有点联系。似乎一提到唐诗宋词就只能是离愁别恨。再翻翻课本里其它的作品,表达伤感的作品占据了绝对的地位。
悲情浓郁是《唐诗宋词选读(选修)》无法避开的一个事实。
我决定改变,换一个角度重新解读这些历经千古的诗词,从悲情中开出希望的花朵。
尝试之一:化悲为“乐”———以《望月怀远》为例。
盛唐诗人张九龄的《望月怀远》是一首怀人之作,诗人想像情人的一举一动,借助“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宏阔的背景,将有情人之间的思念扩大到天地间,无疑为诗作蒙上了淡淡的伤悲。
为了减淡诗里悲伤,我扣住尾联“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引导学生:月光遍洒,天地间不含一丝纤尘,月光所到之处,皎洁空灵,让人忍不住想掬一捧送给心爱的人。如此美丽的举动,如果不是内心痴情无邪是不会做出来的。虽然情人也知道无法为对方送去月光,可是她并不忧伤,因为她坚信梦里还会有一个美丽的约定在等着她。
尝试之二:悲中索“乐”———以《春江花月夜》为例。
被誉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的《春江花月夜》通过一幅春江月夜的壮丽画面勾起诗人对人生短暂、宇宙无穷的感叹。月光下,短暂的人生似大江急流,奔腾远去,再也不回。诗里充溢着伤感的情调,而诗的后半部分表现的男女相思的离愁别绪则更是为诗作蒙上了深深的悲情。
在教授这首诗时,我分别紧扣住“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以及“不知乘月几人归”引导学生从悲情中看到希望。“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表面上表达的是人生的短暂、宇宙的永恒,然而无穷无尽代代相继的人生不正好成为人类形成发展的历史吗?一个人的人生固然短暂,然而一代又一代的人的人生却没有穷尽,最终成为跟高挂天空月亮一样的永恒。这世上还有比生命不停的延续更美的事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短暂的一生也并不渺小,它是永恒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不知江月待何人”则是古人面对浩瀚宇宙发出的疑问,更是古人对宇宙纯朴的探求。江月究竟在待何人?古人也向我们发出了盛情的邀请,古人不能解决的问题,留给21世纪的我们去探索出它的奥秘。
有情的人各居天涯音信不通当然令人愁苦,可是我们依然能从“不知乘月几人归”看到诗人美丽的期盼与祝愿:银辉满地,不知道会有多少满怀思念的人踏着月色归来。这样一幅景象,带给我们的是美丽又令人动容的希望,更令人回味悠长。
尝试之三:悲中插“乐”——以“豪放飘逸”的李白诗专题为例。
这一专题选了李白的四首诗:《梦游天姥吟留别》《月下独酌四首其一》《送友人》《将进酒》。除《送友人》格调比较清新明快之外,其它三首诗都含有李白怀才不遇的悲愤或消极。为了给学生一个完整的李白的形象,同时为了冲淡本专题中的悲情,我又精心挑选了另外两首李白的诗作:《客中作》《夜下征虏亭》。《客中作》的李白嗜美酒,爱游历。《夜下征虏亭》背后的李白显现出少见的细腻柔情。两首诗的插入,丰富了李白原本单薄的形象。
[教情反思]:
悲情成就了古今中外绝大多数的经典作品,也成就了一代代的文学大师。在艺术品的鉴赏中,古今中外的艺术大家都将悲剧审美视为至高境界,认为悲剧审美相对于喜剧而言,更容易让欣赏者产生情感共鸣的认同感和愉悦感。悲情审美,更是具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时空穿透力,在人类的文学艺术的宝殿里,沉积的大多正是具有某种悲剧色彩的忧愤之情,而正是这种悲剧性的忧愤,成就了一部部熠熠生辉的传世佳作。然而相当长一段时间沉浸在这些悲情里,难免产生“审美疲劳”,对审美对象的兴奋减弱,不再产生较强的美感,甚至对对象表示厌弃。
梁民伟,教师,现居江苏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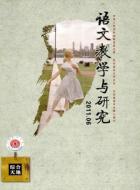
- 线性阅读教学课型论 / 陈祥春
- 兆吉 / 方格子
- 多元智能理论在语文教学中的应用 / 金辉
- 理想在别处 / 陈青山
- 有效朗读原来如此精彩 / 王平
- 经典诵读活动的开展 / 张青芬
- 有效解读应咬定文本 / 殷德忠
- 语文课外阅读课的研究与实验 / 楼利香
- 腹中藏诗书 笔下著美文 / 李玉莲
- 阅读教学中导语设计的有效性 / 戴志梅
- 整合阅读教学与探究性学习 / 李涛
- 初中记叙文写作教学中片段式训练 / 郭雄
- 文本整体把握的方法谈 / 杨海燕
- 小学作文教学浅析 / 陈耀芳
- 新课标下作文的选材 / 罗银龙
- 活化作文教学的三点心得 / 林潮
- 高中应用文写作教学的困境与对策 / 刘嘉
- 让学生在阅读活动中学会“发现” / 杨晓梅
- 作文材料积累的厚积薄发 / 王凡
- 浅谈《与朱元思书》的写作技巧 / 刘成
- 多元智能理论与阅读教学“互动” / 徐爱元
- 不再让作文成为拦路虎 / 狄奇静
- 议论文用例技法浅探 / 郭深山
- 语文教学“老三法”新谈 / 李鹏飞
- 创设语文情景 激发语文兴趣 / 姜霞
- 本色语文的整体思路和教学构想 / 杨益国
- 语文教学中的符号标划法 / 邢宗和
- 利用教材做好作文素材积累 / 刘俊峰
- 中学生创新作文写作三要素 / 李铃川
- 学生写作能力的培养 / 张智育
- 翻译与习作结合的尝试 / 潘信华
- 如何充分发挥语文教学的人文性 / 陈红
- 语文教学中的情感教育 / 张建军
- 突破文言文“言”的教学 / 赖凤翔
- 变传统的预习为备习 / 廖菊英 薛贻奎
- 阅读教学中有效对话方法的探究 / 刘家龙
- 利用教材进行读写结合的尝试 / 骆亮亮
- 小学语文课前的预习与预设谈 / 刘军
- 语文学习空间的开发 / 胡金凤
- 探讨古文的兴趣教学模式 / 蓝爱婕
- 在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独立意识 / 王言波
- 初中语文教学适应课改浅议 / 刘伟
- 语文课要上出情感味 / 孙贵红 孙怀平
- 古诗词教学要“三到” / 祝青娟
- 调动学生课堂积极性的有效对策 / 郁红剑
- 比较教学的好处 / 姚飞云
- 语文课堂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 谢晓艳
- 语文课的时代性需要强化 / 康吉松
- 让语文课堂“亮”起来 / 王云娟
- 在尝试中感悟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 陈柏文
- 作文教学中的互评 / 王玉琼
- 语文课提问初探 / 曾细胜
- 谈谈整体语言教学法 / 李彩香
- 初中语文“综合性学习”教学策略谈 / 肖友明
- 语文教学中的文字教学 / 袁瑞丽
- 语文课堂呼唤绿色提问 / 周妙芬
- 如何提高语文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 黄华招
- 苏教版《唐诗宋词选读》的美丽解读 / 梁民伟
- 影响教学语言艺术的几种因素 / 田华
- 《荷塘月色》和《天山景物记》中的“大美” / 谢增伟
- 《故都的秋》的艺术特色 / 胡蓉 周俊荣
- 新课标下的语文综合性学习 / 王凯
- 让语文活动课“动”起来 / 王彩娟
- 《故都的秋》中四组对比之我见 / 杨志康
- 《钱塘湖春行》《天净沙.秋思》教案 / 雷玲
- 《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教学设计 / 王安逸
- 在“预设”中“生成”课堂展示 / 杨权应
- 《明湖居听书》教学谈 / 曹峥嵘
- 比较探究型课程教法例谈 / 段书英
- 《归去来兮辞》执教札记 / 刘力 谢同育
- 八年级下册第一单元整合教学策略 / 贾树林
- 苏教版初中语文教材质疑 / 秦峰
- 从《丹柯》看高尔基在中国的误读 / 郑燕明
- 诗歌中的民俗教学 / 周爱群
- 《江城子.密州出猎》赏析 / 孙叶丽
- 学生语文自主学习之我见 / 姜勇军
- 新课程下课堂教学的改革 / 许娜
- 解读《史记》要抓好“审丑”的切入口 / 吴艳辉
- 高考写作生活化与个性化策略 / 谭志永
- 培养小学生语文创造思维的思考 / 贾玉君
- 文言文高效复习三字诀 / 张红宇
- 编制语文探究题应遵循的三大原则 / 吴军伟
- 说“托儿” / 詹英顺 苏静
- 关于农村中学语文创新教育的思考 / 周梅娟
- 多媒体在语文教学中的弊端 / 田红玲
- 学生口语交际中的听与评 / 姚海燕
- 古诗文中的数学味 / 张少伶
- 浅谈初中生的养成教育 / 陈绍良
- 农村作文教学之路探幽 / 张春华
- 栖息在梦想之源 / 武旸
- 致妈妈的一封信 / 王佳红
- 旗袍 / 蔡慧
- 让语文课堂成为创新精神培养的殿堂 / 王东生
- 如何在语文教学中渗透思想教育 / 杨建宏
- 拓展小学生语文学习空间的策略 / 吴兴林
- 那场雪 / 陈丹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