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7年第10期
ID: 356270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7年第10期
ID: 356270
分析方法的可操作性(下)
◇ 孙绍振
情感逻辑的“还原法”
艺术家在艺术形象中表现出来的感觉不同于科学家的感觉。科学家的感觉是冷静的、客观的,追求的是普遍的共同性,而排斥的是个人的感情;一旦有了个人情感色彩,就不科学了,没有意义了。可是在艺术家,则恰恰相反,艺术感觉(或心理学的知觉)之所以艺术,就是因为它是经过个人主观情感或智性的“歪曲”。正是因为“歪曲”了,或者用一个术语来说“变异”了,这种表面上看来是表层的感觉才成为深层情感乃至情结的可靠索引。有些作品,往往并不直接诉诸感觉,尤其是一些直接抒情的作品,光用感觉还原就不够了。例如“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好在什么地方?它并没有明确的感知变异,它的变异在它的情感逻辑之中。
这时用感觉的还原就文不对题了,应该使用的是情感逻辑的还原。这里的诗句说的是爱情是绝对的,在任何空间、时间,在任何生存状态,都是不变的,永恒的。爱情甚至是超越主体的生死界限的。这是诗的浪漫,其逻辑的特点是绝对化。用逻辑还原的方法,明显不符合理性逻辑。理性逻辑是客观的、冷峻的,是排斥感情色彩的,对任何事物都取分析的态度。按理性的逻辑的高级形态,亦即辩证逻辑,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是不变的。在辩证法看来,世界上没有永恒不变的东西,一切都随时间、地点、条件而变化。把恋爱者的情感看成超越时间、地点、条件是无理的,但是,这种不合理性之理,恰恰又是符合强烈情感的特点。清代诗话家吴乔把这叫做“无理而妙”。为什么妙?无理对于科学来说是糟糕的,是不妙的,但,因为情感的特点恰恰是绝对化,无理了才有情,不绝对化不过瘾,不妙。所以严羽才说:“诗有别才,非关理也。”
自然,情感逻辑的特点不仅是绝对化,至少还有这么几点,它可以违反矛盾律、排中律、充足理由律。人真动了感情就常常不知是爱还是恨了,明明相爱的人偏偏叫冤家,明明爱得不要命,可见了面又像贾宝玉和林黛玉那样互相折磨。臧克家纪念鲁迅的诗说:“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这按通常的逻辑来说是绝对不通的。可要避免这样的自相矛盾,就要把他省略了的成分补充出来:“有的人死了,因为他为人民的幸福而献身,因而他永远活在人民心中。”这很符合理性逻辑了,但却不是诗了。越是到现代派诗歌中,扭曲和程度越大,现代派诗人甚至喊出“扭曲逻辑的脖子”的口号。在小说中,情节是一种因果,一个情感原因导致层层放大的结果,按理性逻辑来说理由必须充分,这叫充足理由律。可是在情感方面是充足了,在理性方面则不可能充足。说贾宝玉因为林黛玉反抗封建秩序,思想一致才爱她,理由这么清楚,就一点感情也没有了。在现代派小说中,恰恰有反逻辑因果的,如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整个小说的情节的原因和结果都是颠倒的,似乎是无理的。情节的发展好像和逻辑因果开玩笑,反因果性非常明显。例如,主人公以敬烟,对司机表现善意,司机接受了善意,却引出粗暴地拒绝乘车的结果;“我”对他凶狠呵斥,他却十分友好起来。半路上,车子发动不起来了,本来应该是焦虑的,但,司机却无所谓。车上的苹果让人家给抢了,本该引发愤怒和保卫的冲动的,司机也无动于衷。“我”本能地去和抢夺者作搏斗,被打得头破血流,“鼻子软塌塌地挂在脸上”,本该是非常痛苦的,却一点痛苦的感觉也没有。一车苹果被抢光了,司机的表情却“越来越高兴”。抢劫又一次发生,“我”本能地奋不顾身地反抗抢劫,被打得“跌坐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司机不但不对“我”同情和加以慰问,相反却“站在远处朝我哈哈大笑”,这就够荒谬的了。可是作者显然觉得这样的荒诞,还不够过瘾,对荒诞性再度加码。抢劫者开来了拖拉机,把汽车上的零件什么的,能拆卸的都拿走了。司机怎么反应呢?他和那些抢劫的人们,一起跳到拖拉机上去,在车斗里坐下来,“朝我哈哈大笑”。仔细研读,你会发现,在表面上绝对无理的情节中,包含着一种深邃的道理,当然,可能阐释的空间是多元的。我的解读是这样的:小说的荒谬感虽然是双重的,首先,被损害者对于强加于己的暴力侵犯,毫无受虐的感觉,相反却感到快乐;其次,被损害者对为之反抗抢劫付出代价的人,不但没有感恩,相反对之加以侵害,并为之感到快乐;再次,除了施虐和受虐,还有更多的荒谬,渗透在文本的众多细节之中。这篇小说,有时很写实,有时,又常常自由地、突然地滑向极端荒诞的感觉,鼻子软塌塌地,不是贴着而是挂在脸上了,这样的血腥,居然连一点疼痛的感觉都没有涉及。用传统现实主义的“细节的真实性”原则去追究,恐怕是要作出否定的判决的。然而文学欣赏不能用一个尺度,特别不能光从读者熟悉的尺度去评判作家的创造。余华之所以不写鼻子打歪了的痛苦,那是因为他要表现人生有一种特殊状态,是感觉不到痛苦的痛苦,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痛苦不已,呼天抢地,而在性命交关的大事上麻木不仁。这是人生的荒谬,但人们对之习以为常,不但没有痛感,相反乐在其中。
……这是现实的悲剧,然而在艺术上却是喜剧。
喜剧的超现实的荒诞,是一种扭曲的逻辑。然而这样的歪曲逻辑,启发读者想起许多深刻的悖谬的现象,甚至可以说是哲学命题:为什么本来属于你自己的东西被抢了你却感觉不到痛苦?为什么自己的一大车子东西被抢了而无动于衷,却把别人的一个小背包抢走还沾沾自喜呢?缺乏自我保卫的自觉,未经启蒙的麻木、愚昧,从现实的功利来说,是悲剧,从艺术哲学的高度,来看,则是喜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这最为荒谬的现象背后潜藏着深邃的睿智:没有痛苦的痛苦是最大的痛苦。
这样的哲学深邃性,就是无理中的有理,这样的无理,比之一般的道理要深邃得多。如果不把理性逻辑与情感逻辑分化出来,就无法进行深入的分析。这样的分析,很显然,显然已经进入了深邃的层次,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已经不完全属于情感的范畴,而是属于情感和理性交融的范畴了。这个范畴的分野,其实,已经是进入价值的范畴。
价值的还原
价值还原,是个理论问题,但是得从具体的个案讲起。《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并不完全是吴敬梓的发明,而是他对原始的真人真事改编的结果。清朝刘献廷的《广阳杂记》卷四中有一段记载:明末高邮有袁体庵者,神医也。有举子举于乡,喜极发狂,笑不止。求体庵诊之。惊曰:“疾不可为矣!不以旬数矣!子宜亟归,迟恐不及也。若道过镇江,必更求何氏诊之。”遂以一书寄何。其人到镇江而疾已愈,以书致何,何以书示其人,曰:“某公喜极而狂。喜则心窍开张而不可复合,非药石之所能治也。故动以危苦之心,惧之以死,令其忧愁抑郁,则心窍闭。至镇江当已愈矣。”其人见之,北面再拜而去。吁!亦神矣。①“吁!亦神矣。”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啊!医道真是神极了。”可以说这句话是这段小故事的主题:称赞袁医生的医道高明。他没有用药物从生理的病态上治这个病人,而是从心理方面成功地治好了他。其全部价值在于科学的实用性,很严肃的。而在《儒林外史》中却变成胡屠户给范进的一记耳光,重点在于出胡屠户的洋相。范进的这个丈人本来极端藐视范进,可一旦范进中了举人,为了治病硬着头皮打了他一个耳光,却怕得神经反常,手关节不能自由活动,以为是天上的文曲星在惩罚他,连忙讨了一张膏药来贴上。这样一改,就把原来故事科学的、实用的理性价值转化为情感的非实用审美价值了。这里不存在科学的真和艺术的美的统一问题,而是真和美的错位。如果硬要真和美完全统一,则最佳的选择是把刘献延的故事全抄进去。而那样一来,《范进中举》的喜剧美将荡然无存。把科学的实用价值搬到艺术形象中去,不是导致美的升华,而是相反,导致美的消失。②
情感逻辑的“还原法”
艺术家在艺术形象中表现出来的感觉不同于科学家的感觉。科学家的感觉是冷静的、客观的,追求的是普遍的共同性,而排斥的是个人的感情;一旦有了个人情感色彩,就不科学了,没有意义了。可是在艺术家,则恰恰相反,艺术感觉(或心理学的知觉)之所以艺术,就是因为它是经过个人主观情感或智性的“歪曲”。正是因为“歪曲”了,或者用一个术语来说“变异”了,这种表面上看来是表层的感觉才成为深层情感乃至情结的可靠索引。有些作品,往往并不直接诉诸感觉,尤其是一些直接抒情的作品,光用感觉还原就不够了。例如“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好在什么地方?它并没有明确的感知变异,它的变异在它的情感逻辑之中。
这时用感觉的还原就文不对题了,应该使用的是情感逻辑的还原。这里的诗句说的是爱情是绝对的,在任何空间、时间,在任何生存状态,都是不变的,永恒的。爱情甚至是超越主体的生死界限的。这是诗的浪漫,其逻辑的特点是绝对化。用逻辑还原的方法,明显不符合理性逻辑。理性逻辑是客观的、冷峻的,是排斥感情色彩的,对任何事物都取分析的态度。按理性的逻辑的高级形态,亦即辩证逻辑,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是不变的。在辩证法看来,世界上没有永恒不变的东西,一切都随时间、地点、条件而变化。把恋爱者的情感看成超越时间、地点、条件是无理的,但是,这种不合理性之理,恰恰又是符合强烈情感的特点。清代诗话家吴乔把这叫做“无理而妙”。为什么妙?无理对于科学来说是糟糕的,是不妙的,但,因为情感的特点恰恰是绝对化,无理了才有情,不绝对化不过瘾,不妙。所以严羽才说:“诗有别才,非关理也。”
自然,情感逻辑的特点不仅是绝对化,至少还有这么几点,它可以违反矛盾律、排中律、充足理由律。人真动了感情就常常不知是爱还是恨了,明明相爱的人偏偏叫冤家,明明爱得不要命,可见了面又像贾宝玉和林黛玉那样互相折磨。臧克家纪念鲁迅的诗说:“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这按通常的逻辑来说是绝对不通的。可要避免这样的自相矛盾,就要把他省略了的成分补充出来:“有的人死了,因为他为人民的幸福而献身,因而他永远活在人民心中。”这很符合理性逻辑了,但却不是诗了。越是到现代派诗歌中,扭曲和程度越大,现代派诗人甚至喊出“扭曲逻辑的脖子”的口号。在小说中,情节是一种因果,一个情感原因导致层层放大的结果,按理性逻辑来说理由必须充分,这叫充足理由律。可是在情感方面是充足了,在理性方面则不可能充足。说贾宝玉因为林黛玉反抗封建秩序,思想一致才爱她,理由这么清楚,就一点感情也没有了。在现代派小说中,恰恰有反逻辑因果的,如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整个小说的情节的原因和结果都是颠倒的,似乎是无理的。情节的发展好像和逻辑因果开玩笑,反因果性非常明显。例如,主人公以敬烟,对司机表现善意,司机接受了善意,却引出粗暴地拒绝乘车的结果;“我”对他凶狠呵斥,他却十分友好起来。半路上,车子发动不起来了,本来应该是焦虑的,但,司机却无所谓。车上的苹果让人家给抢了,本该引发愤怒和保卫的冲动的,司机也无动于衷。“我”本能地去和抢夺者作搏斗,被打得头破血流,“鼻子软塌塌地挂在脸上”,本该是非常痛苦的,却一点痛苦的感觉也没有。一车苹果被抢光了,司机的表情却“越来越高兴”。抢劫又一次发生,“我”本能地奋不顾身地反抗抢劫,被打得“跌坐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司机不但不对“我”同情和加以慰问,相反却“站在远处朝我哈哈大笑”,这就够荒谬的了。可是作者显然觉得这样的荒诞,还不够过瘾,对荒诞性再度加码。抢劫者开来了拖拉机,把汽车上的零件什么的,能拆卸的都拿走了。司机怎么反应呢?他和那些抢劫的人们,一起跳到拖拉机上去,在车斗里坐下来,“朝我哈哈大笑”。仔细研读,你会发现,在表面上绝对无理的情节中,包含着一种深邃的道理,当然,可能阐释的空间是多元的。我的解读是这样的:小说的荒谬感虽然是双重的,首先,被损害者对于强加于己的暴力侵犯,毫无受虐的感觉,相反却感到快乐;其次,被损害者对为之反抗抢劫付出代价的人,不但没有感恩,相反对之加以侵害,并为之感到快乐;再次,除了施虐和受虐,还有更多的荒谬,渗透在文本的众多细节之中。这篇小说,有时很写实,有时,又常常自由地、突然地滑向极端荒诞的感觉,鼻子软塌塌地,不是贴着而是挂在脸上了,这样的血腥,居然连一点疼痛的感觉都没有涉及。用传统现实主义的“细节的真实性”原则去追究,恐怕是要作出否定的判决的。然而文学欣赏不能用一个尺度,特别不能光从读者熟悉的尺度去评判作家的创造。余华之所以不写鼻子打歪了的痛苦,那是因为他要表现人生有一种特殊状态,是感觉不到痛苦的痛苦,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痛苦不已,呼天抢地,而在性命交关的大事上麻木不仁。这是人生的荒谬,但人们对之习以为常,不但没有痛感,相反乐在其中。
……这是现实的悲剧,然而在艺术上却是喜剧。
喜剧的超现实的荒诞,是一种扭曲的逻辑。然而这样的歪曲逻辑,启发读者想起许多深刻的悖谬的现象,甚至可以说是哲学命题:为什么本来属于你自己的东西被抢了你却感觉不到痛苦?为什么自己的一大车子东西被抢了而无动于衷,却把别人的一个小背包抢走还沾沾自喜呢?缺乏自我保卫的自觉,未经启蒙的麻木、愚昧,从现实的功利来说,是悲剧,从艺术哲学的高度,来看,则是喜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这最为荒谬的现象背后潜藏着深邃的睿智:没有痛苦的痛苦是最大的痛苦。
这样的哲学深邃性,就是无理中的有理,这样的无理,比之一般的道理要深邃得多。如果不把理性逻辑与情感逻辑分化出来,就无法进行深入的分析。这样的分析,很显然,显然已经进入了深邃的层次,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已经不完全属于情感的范畴,而是属于情感和理性交融的范畴了。这个范畴的分野,其实,已经是进入价值的范畴。
价值的还原
价值还原,是个理论问题,但是得从具体的个案讲起。《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并不完全是吴敬梓的发明,而是他对原始的真人真事改编的结果。清朝刘献廷的《广阳杂记》卷四中有一段记载:明末高邮有袁体庵者,神医也。有举子举于乡,喜极发狂,笑不止。求体庵诊之。惊曰:“疾不可为矣!不以旬数矣!子宜亟归,迟恐不及也。若道过镇江,必更求何氏诊之。”遂以一书寄何。其人到镇江而疾已愈,以书致何,何以书示其人,曰:“某公喜极而狂。喜则心窍开张而不可复合,非药石之所能治也。故动以危苦之心,惧之以死,令其忧愁抑郁,则心窍闭。至镇江当已愈矣。”其人见之,北面再拜而去。吁!亦神矣。①“吁!亦神矣。”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啊!医道真是神极了。”可以说这句话是这段小故事的主题:称赞袁医生的医道高明。他没有用药物从生理的病态上治这个病人,而是从心理方面成功地治好了他。其全部价值在于科学的实用性,很严肃的。而在《儒林外史》中却变成胡屠户给范进的一记耳光,重点在于出胡屠户的洋相。范进的这个丈人本来极端藐视范进,可一旦范进中了举人,为了治病硬着头皮打了他一个耳光,却怕得神经反常,手关节不能自由活动,以为是天上的文曲星在惩罚他,连忙讨了一张膏药来贴上。这样一改,就把原来故事科学的、实用的理性价值转化为情感的非实用审美价值了。这里不存在科学的真和艺术的美的统一问题,而是真和美的错位。如果硬要真和美完全统一,则最佳的选择是把刘献延的故事全抄进去。而那样一来,《范进中举》的喜剧美将荡然无存。把科学的实用价值搬到艺术形象中去,不是导致美的升华,而是相反,导致美的消失。②
情感逻辑的“还原法”
艺术家在艺术形象中表现出来的感觉不同于科学家的感觉。科学家的感觉是冷静的、客观的,追求的是普遍的共同性,而排斥的是个人的感情;一旦有了个人情感色彩,就不科学了,没有意义了。可是在艺术家,则恰恰相反,艺术感觉(或心理学的知觉)之所以艺术,就是因为它是经过个人主观情感或智性的“歪曲”。正是因为“歪曲”了,或者用一个术语来说“变异”了,这种表面上看来是表层的感觉才成为深层情感乃至情结的可靠索引。有些作品,往往并不直接诉诸感觉,尤其是一些直接抒情的作品,光用感觉还原就不够了。例如“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好在什么地方?它并没有明确的感知变异,它的变异在它的情感逻辑之中。
这时用感觉的还原就文不对题了,应该使用的是情感逻辑的还原。这里的诗句说的是爱情是绝对的,在任何空间、时间,在任何生存状态,都是不变的,永恒的。爱情甚至是超越主体的生死界限的。这是诗的浪漫,其逻辑的特点是绝对化。用逻辑还原的方法,明显不符合理性逻辑。理性逻辑是客观的、冷峻的,是排斥感情色彩的,对任何事物都取分析的态度。按理性的逻辑的高级形态,亦即辩证逻辑,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是不变的。在辩证法看来,世界上没有永恒不变的东西,一切都随时间、地点、条件而变化。把恋爱者的情感看成超越时间、地点、条件是无理的,但是,这种不合理性之理,恰恰又是符合强烈情感的特点。清代诗话家吴乔把这叫做“无理而妙”。为什么妙?无理对于科学来说是糟糕的,是不妙的,但,因为情感的特点恰恰是绝对化,无理了才有情,不绝对化不过瘾,不妙。所以严羽才说:“诗有别才,非关理也。”
自然,情感逻辑的特点不仅是绝对化,至少还有这么几点,它可以违反矛盾律、排中律、充足理由律。人真动了感情就常常不知是爱还是恨了,明明相爱的人偏偏叫冤家,明明爱得不要命,可见了面又像贾宝玉和林黛玉那样互相折磨。臧克家纪念鲁迅的诗说:“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这按通常的逻辑来说是绝对不通的。可要避免这样的自相矛盾,就要把他省略了的成分补充出来:“有的人死了,因为他为人民的幸福而献身,因而他永远活在人民心中。”这很符合理性逻辑了,但却不是诗了。越是到现代派诗歌中,扭曲和程度越大,现代派诗人甚至喊出“扭曲逻辑的脖子”的口号。在小说中,情节是一种因果,一个情感原因导致层层放大的结果,按理性逻辑来说理由必须充分,这叫充足理由律。可是在情感方面是充足了,在理性方面则不可能充足。说贾宝玉因为林黛玉反抗封建秩序,思想一致才爱她,理由这么清楚,就一点感情也没有了。在现代派小说中,恰恰有反逻辑因果的,如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整个小说的情节的原因和结果都是颠倒的,似乎是无理的。情节的发展好像和逻辑因果开玩笑,反因果性非常明显。例如,主人公以敬烟,对司机表现善意,司机接受了善意,却引出粗暴地拒绝乘车的结果;“我”对他凶狠呵斥,他却十分友好起来。半路上,车子发动不起来了,本来应该是焦虑的,但,司机却无所谓。车上的苹果让人家给抢了,本该引发愤怒和保卫的冲动的,司机也无动于衷。“我”本能地去和抢夺者作搏斗,被打得头破血流,“鼻子软塌塌地挂在脸上”,本该是非常痛苦的,却一点痛苦的感觉也没有。一车苹果被抢光了,司机的表情却“越来越高兴”。抢劫又一次发生,“我”本能地奋不顾身地反抗抢劫,被打得“跌坐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司机不但不对“我”同情和加以慰问,相反却“站在远处朝我哈哈大笑”,这就够荒谬的了。可是作者显然觉得这样的荒诞,还不够过瘾,对荒诞性再度加码。抢劫者开来了拖拉机,把汽车上的零件什么的,能拆卸的都拿走了。司机怎么反应呢?他和那些抢劫的人们,一起跳到拖拉机上去,在车斗里坐下来,“朝我哈哈大笑”。仔细研读,你会发现,在表面上绝对无理的情节中,包含着一种深邃的道理,当然,可能阐释的空间是多元的。我的解读是这样的:小说的荒谬感虽然是双重的,首先,被损害者对于强加于己的暴力侵犯,毫无受虐的感觉,相反却感到快乐;其次,被损害者对为之反抗抢劫付出代价的人,不但没有感恩,相反对之加以侵害,并为之感到快乐;再次,除了施虐和受虐,还有更多的荒谬,渗透在文本的众多细节之中。这篇小说,有时很写实,有时,又常常自由地、突然地滑向极端荒诞的感觉,鼻子软塌塌地,不是贴着而是挂在脸上了,这样的血腥,居然连一点疼痛的感觉都没有涉及。用传统现实主义的“细节的真实性”原则去追究,恐怕是要作出否定的判决的。然而文学欣赏不能用一个尺度,特别不能光从读者熟悉的尺度去评判作家的创造。余华之所以不写鼻子打歪了的痛苦,那是因为他要表现人生有一种特殊状态,是感觉不到痛苦的痛苦,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痛苦不已,呼天抢地,而在性命交关的大事上麻木不仁。这是人生的荒谬,但人们对之习以为常,不但没有痛感,相反乐在其中。
……这是现实的悲剧,然而在艺术上却是喜剧。
喜剧的超现实的荒诞,是一种扭曲的逻辑。然而这样的歪曲逻辑,启发读者想起许多深刻的悖谬的现象,甚至可以说是哲学命题:为什么本来属于你自己的东西被抢了你却感觉不到痛苦?为什么自己的一大车子东西被抢了而无动于衷,却把别人的一个小背包抢走还沾沾自喜呢?缺乏自我保卫的自觉,未经启蒙的麻木、愚昧,从现实的功利来说,是悲剧,从艺术哲学的高度,来看,则是喜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这最为荒谬的现象背后潜藏着深邃的睿智:没有痛苦的痛苦是最大的痛苦。
这样的哲学深邃性,就是无理中的有理,这样的无理,比之一般的道理要深邃得多。如果不把理性逻辑与情感逻辑分化出来,就无法进行深入的分析。这样的分析,很显然,显然已经进入了深邃的层次,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已经不完全属于情感的范畴,而是属于情感和理性交融的范畴了。这个范畴的分野,其实,已经是进入价值的范畴。
价值的还原
价值还原,是个理论问题,但是得从具体的个案讲起。《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并不完全是吴敬梓的发明,而是他对原始的真人真事改编的结果。清朝刘献廷的《广阳杂记》卷四中有一段记载:明末高邮有袁体庵者,神医也。有举子举于乡,喜极发狂,笑不止。求体庵诊之。惊曰:“疾不可为矣!不以旬数矣!子宜亟归,迟恐不及也。若道过镇江,必更求何氏诊之。”遂以一书寄何。其人到镇江而疾已愈,以书致何,何以书示其人,曰:“某公喜极而狂。喜则心窍开张而不可复合,非药石之所能治也。故动以危苦之心,惧之以死,令其忧愁抑郁,则心窍闭。至镇江当已愈矣。”其人见之,北面再拜而去。吁!亦神矣。①“吁!亦神矣。”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啊!医道真是神极了。”可以说这句话是这段小故事的主题:称赞袁医生的医道高明。他没有用药物从生理的病态上治这个病人,而是从心理方面成功地治好了他。其全部价值在于科学的实用性,很严肃的。而在《儒林外史》中却变成胡屠户给范进的一记耳光,重点在于出胡屠户的洋相。范进的这个丈人本来极端藐视范进,可一旦范进中了举人,为了治病硬着头皮打了他一个耳光,却怕得神经反常,手关节不能自由活动,以为是天上的文曲星在惩罚他,连忙讨了一张膏药来贴上。这样一改,就把原来故事科学的、实用的理性价值转化为情感的非实用审美价值了。这里不存在科学的真和艺术的美的统一问题,而是真和美的错位。如果硬要真和美完全统一,则最佳的选择是把刘献延的故事全抄进去。而那样一来,《范进中举》的喜剧美将荡然无存。把科学的实用价值搬到艺术形象中去,不是导致美的升华,而是相反,导致美的消失。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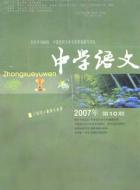
- 我对经典作品教学的一些看法 / 钱理群
- 分析方法的可操作性(下) / 孙绍振
- 关于现代教育技术与中学语文教学融合的冷思考 / 吴 堂
- 从“心”开 / 乔 晖
- 深入中学语文教育第一线,乐作草根博导 / 伍明春
- 教材改革:突破与创新 / 孙慧玲
- “情”到深处不讲“理” / 品茂峰 宋 斌
- 对文学作品语言的敏感性及其训练摭谈 / 胡象光
- 设“专题”探讨,促深化理解 / 陈 桦
- 反思教学找对策,提高学生阅读能力 / 黄玉琼
- 尊重伦理生 / 吕晓乐
- 也谈中学生“作文生活化” / 张 瑛
- 作文访谈录之实用技巧篇 / 赵俊辉
- 高考作文“母语”写作失误例谈 / 钟 瑛
- 谈谈《秦晋殽之战》的节选及叙述艺术 / 李建生
- 亲情的礼赞,生命的高歌 / 李双红
- 《孔雀东南飞》九悲 / 李茂略
- 同为“秋声”赋,寄托大不同 / 罗献中
- 余映潮:《我的叔叔于勒》教学实录与评点 / 余映潮
- 巧设四环节,活化一堂课 / 凌荣毅
- 《最后一片藤叶》多重主题探究 / 周旭荣
- 《阿长与〈山海经〉》一文中情感的跳跃与过渡 / 李朝霞 石海波 石生银
- 《论语》的原生态理解 / 孙铮明
- 文言文诵读五步 / 徐 斌
- 文人、文心与文章 / 陈 菁 何兴楚
- 中学语文教材注释辨误 / 谢序华
- “青鸟”新义 / 李玉洁
- 对父亲的误读 / 陈 涛
- 作文评分:到语言为止! / 黄助昌
- 预支五百年新 / 李弗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