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7年第10期
ID: 356286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7年第10期
ID: 356286
同为“秋声”赋,寄托大不同
◇ 罗献中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咏秋之作遍及各代,不计其数。其中虽然诗歌、散文数量众多,异彩纷呈,而赋体作品亦为数不少,且多为佳作。在这些咏秋佳赋中,有两篇名家同题之作格外引人注目,它们在文学的星空中交相辉映,光彩夺目,为绚丽多姿的文学园地增添了色彩。它们就是《秋声赋》,作者分别为中唐的刘禹锡和北宋的欧阳修。
有趣的是,虽然这两篇佳赋同出名家之手,且取材命题也完全相同,但在主旨、寄托和风格上却迥然不同,可谓名同实异。究其原因,乃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作者的生活经历和个人秉性等均不相同使然。这种同题异旨、风格各异的文学作品为我们在阅读上提供了不同的美的享受,同时也为我们在写作的构思立意上提供了十分直观的借鉴。下面,我们就将两篇作品分别作一赏析并予以比较。
刘禹锡的《秋声赋》作于唐武宗会昌元年(841年)。当时作者虽已年届古稀,老病在身(次年就去世了),但他的意志并未消沉,仍然意气风发,昂扬进取。我们知道,刘禹锡的一生充满了曲折和坎坷,历经磨难,饱经风霜。刘禹锡青年时代即有施道展志的政治理想。早年入仕后就积极参加了王叔文领导的政治革新运动,成为“永贞革新”的重要成员。可惜革新运动很快夭折,刘禹锡遭到了沉重打击,被贬到遥远的蛮荒之地充任卑微的闲职,失去了在朝廷中施展才干、实现抱负的机会。其后的几十年,刘禹锡就在崎岖的宦途上艰难跋涉,颠沛流离,其间屡受挫折,身心备受摧残。“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便是其早期贬谪生涯的真实写照。在长期的磨难和打击中,刘禹锡磨练出了一种坚毅顽强、坚忍不拔的精神。这种精神在他身上历久弥坚,至死未衰。因而在这篇赋里,他一反历来文人、名士的悲秋情调,借秋声寄托岁月蹉跎、壮志难酬的孤愤,对人生的晚秋发出了顽强不屈的呐喊,唱出了人生的最强音,充分显示了他虽然历经逆境坎坷、饱受风霜打击却始终乐观进取的顽强意志。正如他在赋中说的:“嗟乎!骥伏枥而已老,鹰在鞲而有情。聆朔风而心动,眄天籁而神惊。力将瘳兮足受绁,犹奋迅于秋声!”
读刘禹锡的这篇赋,不禁让我们联想起三国曹操的励志名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又会让人联想起作者咏秋的《秋词》一诗:“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作者豪放、乐观的情怀跃然纸上。
所以,明人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十五说:“刘禹锡播迁一生,晚年洛下闲废,与绿野(裴度)、香山(白居易)诸老,伏游诗酒间,而精华不衰,一时以‘诗豪’见推。公亦自有句云:‘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盖道其实也。”
欧阳修的《秋声赋》作于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其时作者五十又三,刚过知天命之年,比刘禹锡创作此赋时要年轻得多。值得玩味的是,欧赋虽沿用刘禹锡《秋卢赋》之题,但主旨乃在悲秋,与刘赋大异其趣。当时作者已由多年的地方官调入朝廷任要职,高官厚禄,地位显赫,正可谓飞黄腾达。然而,由于作者恪守儒家传统思想中“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准则,以及他对民生社稷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所以作者此时并未感到轻松愉快;相反,北宋王朝的朝政积弊,官场倾轧,内外交困,风雨飘摇,使他内心产生深刻的苦闷。欧阳修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创作了《秋声赋》。他借此赋抒发秋声降临时自己的独特感触,并借以排遣内心的苦闷。作者由万物的凋零联想到人生的衰老,表达了“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的烦恼,寄托了“思其力之所不及,忧其智之所不能”、改革现实无望的深沉感慨。这让人们不禁想起晚唐李商隐的悲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这篇赋和历代悲秋之作在基调上是相似的。就赋这种体裁来说,人们由此可以联想起战国宋玉的《九辩》、西晋潘岳的《秋兴赋》、初唐卢照邻的《秋霖赋》、元初元好问的《秋望赋》等。例如宋玉咏秋曰:“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惊栗兮,若在远行。”潘岳咏秋曰:“嗟秋日之可哀兮,谅无愁而不尽。”这些悲秋的声调是几乎相同的,而欧赋悲秋无疑是最深沉的,在主旨上也是最深刻的,因为他悲叹的并不是个人的盛衰荣辱,而是国家的前途命运,可谓“大悲”也,故最能感动后人,成为悲秋之千古绝唱。
由上可知,刘禹锡和欧阳修两位文学巨人,虽然具有同样高尚的人格和崇高的精神境界,虽然具有同样卓越的审美才能,但他们根据自身的独特经历和审美思辨,在文学创作中对同一题材进行了截然相反的开掘和立意,造就了作品中迥然不同的文学风格。他们用同一题材表达了不同的内心感受,寄托了不同的思想情感,具有令人耐人寻味的无穷魅力,创造了文学史上的一则佳话。
在艺术方面,刘、欧两赋也迥乎不同,各有千秋。刘赋在写法上的最大特点是先反后正,先抑后扬,前面主要抒写前人悲秋思乡、衰残寂寥之感,最后发出作者以老骥、雄鹰自励,闻秋声而“奋迅”的感叹。于正反对比之中,突现了作者顽强的意志和不屈的精神,以及积极进取、不懈追求的人生观。而欧赋的突出特点则是以贴切的比喻和多方烘托的方式,将难以捉摸的秋声描绘成有声有色的具体形象,并以散文的笔势写赋,句式灵活,骈散相间,错落有致,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作者内心深处的悲凉情感。
总之,刘禹锡和欧阳修的两篇咏秋之赋,虽然立意不同,风格各异,但同样脍炙人口而千古流传,成为咏秋的佳作妙品,堪称咏秋佳赋的姊妹篇。换言之,它们正因为旨趣和风格各不相同,各具特色,才成为文学百花园中的两朵艳丽的奇葩。文学创作最忌陈陈相因,面目相似。所以,刘、欧两大杰出作家的同题佳作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更为我们提供了创作上力求多姿多彩的示范。
[作者通联:湖北大学文学院2006级研究生]
语文教学生态论的滥觞
语文教学的历史源远流长,即使作为我国普通教育阶段的一门独立学科,即以1903年的《奏定学堂章程》的施行为标志,语文教学也有了近100年的历史。先辈们对语文教学体系的建立付出了大量的心血,筚路蓝缕之功不可没。但语文教学的质量至今仍不能令人满意,社会对语文教学质量的低下多有微词,可以说语文教学一直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要劈开荆棘走出一条适合汉语学习的道路,必须借鉴前人的经验,同时还要利用最新的理论成果。牛顿曾经说过,他之所以成功是因为站到伟人的肩膀上,但站在伟人肩膀上的不一定都能成功。现在已经不是牛顿的时代,当代科学由分科细密逐渐转向综合发展,各种学科原理相互融通,相互借鉴,相互促进。以系统科学为基础的信息论、突变论、协同论、耗散结构理论及认知科学的兴起,使人们能够对研究对象进行全方位的观照。现代生态学以自然界的物质、能量、信息为基础,研究生物系统与环境系统的相互作用和运动规律,同时把在地球生态巨系统中处于重要地位的人群系统作为研究对象,探索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及其运动规律。现代生态学的理论与培养人的语言能力的语文教学有相通之处,这就使语文教学生态论的产生有了一定的基础。
选自《存在与发展—语文教学生态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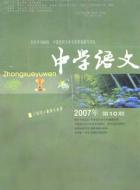
- 我对经典作品教学的一些看法 / 钱理群
- 分析方法的可操作性(下) / 孙绍振
- 关于现代教育技术与中学语文教学融合的冷思考 / 吴 堂
- 从“心”开 / 乔 晖
- 深入中学语文教育第一线,乐作草根博导 / 伍明春
- 教材改革:突破与创新 / 孙慧玲
- “情”到深处不讲“理” / 品茂峰 宋 斌
- 对文学作品语言的敏感性及其训练摭谈 / 胡象光
- 设“专题”探讨,促深化理解 / 陈 桦
- 反思教学找对策,提高学生阅读能力 / 黄玉琼
- 尊重伦理生 / 吕晓乐
- 也谈中学生“作文生活化” / 张 瑛
- 作文访谈录之实用技巧篇 / 赵俊辉
- 高考作文“母语”写作失误例谈 / 钟 瑛
- 谈谈《秦晋殽之战》的节选及叙述艺术 / 李建生
- 亲情的礼赞,生命的高歌 / 李双红
- 《孔雀东南飞》九悲 / 李茂略
- 同为“秋声”赋,寄托大不同 / 罗献中
- 余映潮:《我的叔叔于勒》教学实录与评点 / 余映潮
- 巧设四环节,活化一堂课 / 凌荣毅
- 《最后一片藤叶》多重主题探究 / 周旭荣
- 《阿长与〈山海经〉》一文中情感的跳跃与过渡 / 李朝霞 石海波 石生银
- 《论语》的原生态理解 / 孙铮明
- 文言文诵读五步 / 徐 斌
- 文人、文心与文章 / 陈 菁 何兴楚
- 中学语文教材注释辨误 / 谢序华
- “青鸟”新义 / 李玉洁
- 对父亲的误读 / 陈 涛
- 作文评分:到语言为止! / 黄助昌
- 预支五百年新 / 李弗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