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语文建设 2008年第4期
ID: 81151
语文建设 2008年第4期
ID: 81151
文本分析的七个层次(续)
◇ 孙绍振
第四,价值的“还原”
价值还原是个理论问题,但得从具体的个案讲起。《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中举”,并不完全是吴敬梓的发明,而是他对原始真人真事改编的结果。清朝刘献廷《广阳杂记》卷四中有一段记载:
明末高邮有袁体庵者,神医也。有举子举于乡,喜极发狂,笑不止。求体庵诊之。惊曰:“疾不可为矣!不以旬数矣!子宜亟归,迟恐不及也。若道过镇江,必更求何氏诊之。”遂以一书寄何。其人到镇江而疾巳愈,以书致何,何以书示其人,曰:“某公喜极而狂。喜则心窍开张而不可复合,非药石之所能治也。故动以危苦之心,惧之以死,令其忧愁抑郁,则心窍闭。至镇江当已愈矣。”其人见之,北面再拜而去。吁!亦神矣。
“吁!亦神矣。”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啊!医术真是神极了。”可以说这句话是这个小故事的主题:称赞袁医生医术高明。他没有用药物从生理上治这个病人。而是从心理方面成功地治好了他。其全部价值在于科学的实用性,而在《儒林外史》中却变成胡屠户给范进的一记耳光,重点在于出胡屠户的洋相。范进这个丈人本来极端藐视范进。可一旦范进中了举人,为了治病硬着头皮打了他一个耳光,却怕得神经反常,手关节不能自由活动。以为是天上文曲星在惩罚他,连忙讨了一张膏药贴上。这样一改。就把原来故事科学的、实用的理性价值转化为情感的非实用的审美价值了。这里不存在科学的真和艺术的美统一的问题,而是真和美的错位。如果硬要真和美完全统一,则最佳选择是把刘献廷的故事全抄进去,而那样一来,《范进中举》的喜剧美将荡然无存。把科学的实用价值搬到艺术形象中去,不是导致美的升华,而是相反,导致美的消失。
创作就是从科学的真的价值向艺术的美的价值转化。因为理性的科学价值在人类生活中占有优势,审美价值常常处于被压抑的地位。正因为这样。科学家可以在大学课堂中成批成批地培养。而艺术家却不能。
要欣赏艺术,摆脱被动,就要善于从艺术的感觉、逻辑中还原出科学的理性,从二者的矛盾中。分析出情感的审美价值。为什么李白在白帝城向江陵进发时只感到“千里江陵一日还”的速度。而感觉不到三峡礁石的凶险呢?因为他归心似箭。为什么李白觉得并不一定很轻的船很轻呢?因为他流放夜郎,“中道遇赦”,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解除政治压力后。心里感到轻松了。因而即使船再重。航程再险,他也感觉不到。这种感觉的变异和逻辑的变异成为诗人内心激情的一种索引,诗人用这种外在的、可感的、强烈的效果去推动读者想象诗人情感产生的原因。为什么阿Q在被押上刑场之时不大喊冤枉,反而为圆圈画得不圆而遗憾?按常理来还原,正是因为画了这个圆才完成判死刑的手续。通过这个还原。益发见得阿Q的麻木。阿Q越是麻木,在读者心目中越是能激发起焦虑和关注,这就是艺术感染力,这就是审美价值。如果阿Q突然叫起冤枉来。而不是叫喊“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好汉)”,这就和常规的逻辑缩短了距离,喜剧效果就消失了。正因如此,逻辑的还原最后必须走向价值的还原。’而从价值的还原中,就不难分析出真正的艺术奥秘了。
第五,历史的“还原”和比较
艺术感知还原、逻辑还原和价值还原,都不过是分析艺术形式的静态的逻辑方法,属于一种入门方法。入门以后对作品的内容还得有一个历史的动态的分析,因而需要更高级的方法,这就是“历史还原”。
从理论上说。对一切对象的研究最起码的要求就是把它放到历史环境里去。不管什么样的作品,要作出深刻的分析,只是用今天的眼光去观察是不行的,必须放到产生这些作品的时代(历史)背景中去。还原到产生它的那种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艺术的气候中去。历史的还原,目的是抓住不同历史阶段中艺术倾向和追求的差异。关键是内在的艺术本身的景物、人物内心情感的进展。比如武松打虎,光从一般文学的价值准则来看。当然也可能分析出它对英雄的理解:从力量和勇气来说,武松是超人的:但是从心理上说。他又是平凡的。和一般小人物差不多。分析到这个层次,可以说已经相当有深度了。但是。如果把它放到中国古典小说对英雄人物的想象的过程中去,就可能发现,这对于早于《水浒》的《三国演义》是一个伟大的进步。在《三国演义》中。英雄人物是超人的,面临死亡和磨难是没有痛苦的,如关公刮骨疗毒。虽然医生的刀刮出声音来。但他仍然面不改色,没有武松那种活老虎打死了、死老虎却拖不动的局限。也没有类似下山以后,见了两只假老虎就惧怕的心理。
艺术和文学的历史是对人类内心探索的记录。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家虽然表面上各自独立,但是在表现人物内心的发现方面,却是前赴后继,有相当明显的继承性,只有把他们之间的历史的差异揪住不放。才能把那隐性的变幻揭示出来。
除了人物内心的历史深化过程以外,另一个重要方面,就要看文体的历史差异。艺术形式是不断重复的。审美情感往往通过艺术形式的发展巩固下来。如余秋雨,虽然许多媒体起哄。攻了他好几年,但是并没有损害他的文学地位,因为余秋雨对中国当代散文的发展有历史性的贡献。他创造了一种文化散文的文体。把人文景观用之于自然景观的阐释,还把散文所少有的思想容量扩大了。这种历史性的贡献,是任何喧嚣的媒体都不能扼杀的。
第六,流派的“还原”和比较
还原到历史语境中去还只是一个比较笼统的说法。一切历史语境,对文学作品来说。都是历史的审美语境。一切审美语境都不但与形式(文类),而且与流派分不开。要真正理解经典文学作品的历史发展。必须分析不同流派的艺术差异。
如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和闻一多的《死水》。孤立地分析这两首诗是比较困难的。徐志摩的抒情是相当潇洒优雅的,以美化为目标。而闻一多却是以丑为美。这不仅是个性不同。而且是因为受了两个不同流派的诗歌的影响。徐志摩是受了欧洲浪漫主义诗潮的影响,所以他的诗不像郭沫若早期的诗那样暴躁凌厉。到了闻一多。诗的情绪是激烈的,但是明显地把本来很强烈的情绪提炼成了一种统一的情绪,把强烈的感情提炼成了单纯的想象的意象。徐志摩虽然倾向于浪漫主义,但是他不仅善于抒写强烈的感情,而且善于作温情潇洒的抒发。如果把《再别康桥》让闻一多或者郭沫若来写,可以想象不知有多少强烈的意象要喷发出来。徐志摩是很收敛的,他反复强调“轻轻的”“悄悄的”,虽然表面上说,心里有一首别离的歌,可实际上却反复申说,不能放歌,一切的一切都是沉默的,“沉默是今晚的康桥”,也就是静静地自我享受,默默地自我体验。这样的情感和语言提炼,正是徐志摩在艺术上成熟的表现。他把情感集中在告别的一刹那,凝聚在内心无声的沉静中,借助西欧浪漫主义诗歌艺术方法,把自我情感美化到了极致。而闻一多的诗作则不单纯追求美化,相反,从第一节就开始极尽丑化之能事,不但是死水,而且 [##] 是绝望的,不但是破铜烂铁,而且还丢下剩菜残羹。到了第二节。又反过来,把铁锈转化为桃花。铜绿变为翡翠,油腻升华为云霞,发臭的死水居然还能成为碧酒,泡沫化为珍珠。这一切都显示他所追求的是另外一个流派的美学原则,那就是象征派“以丑为美”的原则。正是这样的美学原则。帮助闻一多表现了对黑暗现实特有的愤激情绪。哪怕拿给恶魔来“开垦”,也比什么都是老样子、死水一潭好得多。
第七,风格的“还原”和比较
把作品的形式发展、作家的审美价值观念、所属的流派、所处的历史背景都弄清楚了。是不是就解决了作品分析的一切问题呢?还没有。 。因为上述一切,都还只是揭示了你所要分析的作品和其他同样的形式、同样的流派、同样的历史语境中的作品的共同性,而作品分析的最终目标却不应该是这一作品与其他作品之间的共同点。而是其特殊点。
可是现在许多教参中,所谓的写作特点很少真正接触到特点,常常是把许多作品的共同点拿来冒充。比如说,把《荷塘月色》说成是表现大革命失败后小资产阶级的苦闷和彷徨。这就不是《荷塘月色》一篇文章的特点。而是这一个时期许多文章的共同点。朱自清作为一个人,精神世界是多方面的,如《背影》《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哪来什么政治的影子呢?
要真正抓住作品的特点,第一,要把作者作为一个个人和他所属的阶层区别开来;第二,要把作者一时一事的感兴和通常个性区别开来。像《荷塘月色》这样的作品,它的妙处就在那离开妻子和回到妻子身边的一段很短的时间里,内心“骚动”和平复的过程。文章把似乎是瞬息即逝的、没有任何实用价值的思绪刻画出来了。如果不写下来,生活似乎没有什么损失,但是艺术上的损失却永远不可弥补,这就是审美价值与实用价值的不同。
从创作论来说,一切艺术创造都不是凭空的,它是在前人艺术积累基础上前进的。这种积累,首先是形式和流派。艺术是审美情感的表现。任何审美情感都是不可重复的,但这并不意味一切艺术创作都要从零开始,因为审美情感虽然不能重复,但艺术形式和流派却是在不断地重复的。正是在形式和流派中,积累着的人类审美情感升华为审美规范。有了这种规范,作家就不用从零开始,而是把艺术的历史的水准作为自己的起点了。但是,形式和流派毕竟是共同的,作家要遵循它的规范,但是又不能完全拘守它。完全拘守它。就变成重复了,就没有创造可言了。因而艺术的特性。又不断突破和颠覆形式和流派的积累。最可贵的是不但要遵循其规范。而且要突破其规范。最大的突破就是对形式和流派全部规范的颠覆。但是,这是一个很长历史时期的事,像唐诗从沈约搞平平仄仄到李白等盛唐诗人写出成熟的诗篇,前后经历了几百年。新诗打破旧诗的镣铐,已经八十多年,至今形式规范仍然得不到大家的认同。至于流派,当然比形式的变动要快一些。但是,不能指望大部分作家都有创立流派的才能。一般有才华的作家,他的个性、他的情感的许多方面与现成的流派和形式不能相容,经过反复探索,往往也只能在遵循形式和流派的审美规范的同时。作小量的突破,有了这种突破,他就表现出一些前人所没有表达出来的东西,这就算是有风格了。
在同样的形式和流派中,在同样的历史条件下。有风格。就是有创造;没有风格。就是没有创造:没有创造。就只能因循。而因循与艺术的本性是不相容的。余秋雨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散文风格,他把自然景观拿来阐释人文景观,而且把宏大的文化思考放到和小品联系在一起的散文中去。这种风格在中国当代散文史上是影响深远的。
对于作品分析来说,最为精致的分析就是在经典文本中,把潜在的、隐秘的、个人的创造性风格分析出来。比如。同样是抒情,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和郁达夫的《故都的秋》不同。朱自清的抒情,是一种温情,用温情把环境美化,而郁达夫却不写温情,他所强调的是一种悲凉之情,说秋天的美在于它的萧索、幽远和落寞。这两个人的风格显示了他们不同的文化和美学追求。善于在对比中分析不同,对于拓展学生的精神境界和审美情操是有好处的。如果满足于把这两种风格的文章说得差不多,就可能把学生的心灵窒息了,到写作的时候,就难免是千篇一律的滥情了。
要把独特的风格概括出来,就要善于比较,这就要有精致的辨析力。
不但善于从看来相同的作品中看出相异的地方,而且要善于从看来相异的作品中,看出相同的地方。这是科学抽象的基本功,是需要长期自我培养的。最关键的是,要使思想活跃起来。在别人看不到联系的地方,你能看到联系。
如在《荷塘月色》中,朱自清有意省略了树上的蝉声和水里的蛙声,郁达夫在《故都的秋》中则特别写了故都那衰弱的快要死亡的秋蝉的鸣声。一般的人不会把这两者联系起来,而一个有心人就应该从中看到郁达夫和朱自清在情调和风格上的差异。许多人读余光中《牛蛙记》的时候。往往又忘记了朱自清和郁达夫的作品。而一个善于异中求同的人就会情不自禁地把余光中笔下的蛙和朱自清笔下省略了的蛙联系起来。一个唯恐写蛙声会破坏诗意。而另一个却偏偏大写特写,把最杀风景的情景写得淋漓尽致,形成了一种与朱自清的美化环境的自我风格完全不同的自我调侃的幽默风格。
对于风格的分析,不能蜻蜓点水,要层层深入,同样是幽默的风格,不同作家的特点要穷追不舍。例如钱钟书、王小波和舒婷都是幽默的,但我们不能肤浅地以指出他们都是幽默为满足,要把他们的特点分析出来,这需要精致的比较。比如,舒婷的散文,虽然幽默,但她的幽默带有抒情性,而王小波的幽默则更带智性的深邃,钱钟书的幽默和王小波不同,他更带进攻性,也就是更多讽刺的尖锐性。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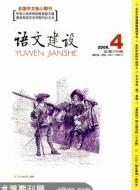
- 浅析2008年高考《考试大纲》语文学科的四点变化 / 张秋玲 张心科
- “八小”锁定高考一类作文 / 姜有荣
- “轰趴”正流行 / 汤晓玲
- “火星文”来了 / 邹 贞
- “轻熟女”·“轻熟男”·“轻熟长靴” / 孙建强
- 门到底破了没有 / 李小军 金木根
- “元典”与“原典” / 宋闻兵
- “紧箍咒”不仅可以念更可以戴 / 尹海良
- 这个“鲜”当作何解? / 董秋成
- 释“仅” / 金 颖
- 《桃花源记》中的“叹惋” / 王够伟
- 《景阳冈》锦心细勾的“十五碗” / 宁夏江
- 也说“木叶” / 李 睿
- 老调新弹 / 田景梅 张丽军
- 一字串 / 张慕元
- 工笔绘“好景”“名画”夸凤池 / 陆精康
- 正确对待学生的真实写作 / 汪益军
- 对有效推进说课活动发展的思考 / 周东华
- 用平常心看待高考作文 / 董晓平
- 食补为主,药补为辅 / 张玉新
- 千万勿忘“我”是谁 / 陈钟梁
- 让语文课像诗歌一样美丽 / 刘占泉
- 走近中国的中国诗人 / 尤立增
- 《我有一个梦想》教学设计 / 冯菊荣
- 《奥斯维辛没有什么新闻》教学设计 / 陈成龙
- 文本阅读助读资料筛选的有效策略 / 雷林宙
- 语文版初中语文实验教材选文字频统计分析 / 吴格明
- 论点摘编 / 佚名
- 文本分析的七个层次(续) / 孙绍振
- 语文教育研究、文学教育与课程改革 / 李 节
- 温故知新 / 饶杰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