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7年第10期
ID: 356297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7年第10期
ID: 356297
作文评分:到语言为止!
◇ 黄助昌
《作文评分:到语言为止?》(见《中学语文》2007年第3期)对我的拙文《作文评分:到语言为止》(见《中学语文》2006年第12期)提出质疑,一个“?”号表明了李运淼、李在荣先生的全部观点。在两位先生看来,《出得厅堂入得厨房之王国维》被判为零分,判得无比正确,判得不可动摇。二位先生之所以如此坚决,是因为基于这样的前提:一切文章“不能突破人性道德底线、社会道德底线、伦理道德底线、民族尊严底线、时代主旋律底线”,否则“只能得低分或零分,没有理由叫屈”,因为“对作文的评判从来就重视考生作文中反映的‘道’,现在如此,将来亦如此”。
我本不想笔战,但以作文教学的前景计,不敢高挂“免战牌”。其实我的拙文最为看重的就是“道”,与二位先生的论点是一致的:文以载道。但我主张:此“道”既指可已知之“道”或人云亦云之“道”,也可指“个人之道”即个人的观点或“政治思想”,并认为突破性的创新一定萌芽于“个人之道”中,所以就学生的作文而言,只要语言表述“道”或“个人之道”方面属上乘,就应当判高分。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百道并行而不相悖”。以斯陀夫人《汤姆叔叔的小屋》和米切尔《飘》为例,前者歌颂解放黑奴的斗争,被公认为影响历史进程的经典小说,后者赞美南方蓄奴制度,被改编为《乱世佳人》,风靡世界,至今不衰,被公认为经典电影。就道德价值层面而言,前者进步,后者反动。“道”绝然对立,但并不影响人们的评价,仍被公认同是世界名著,何故?语言之效也!何况那得零分的作文,事实上也并没有触犯所谓的“五种底线”。
我之所以特强调“语言”的重要性,是因为基于这样的考虑:无“道”之文则言而无绪,无文之“道”则行之不远。同“道”相争,比的是语言;异“道”相竞,比的也还是语言(语言不好的“道”自行淘汰了)。此“道”与彼“道”,在文化价值层面上并无优劣高低之分,有道是“圣人不曾高,众人不曾低”(李贽语),但在读者个人的价值判断上却有优劣高低或好恶之分的。因此,阅卷者个人的道德价值判断不能成为评分的标准。阅卷者不是“完人”。
有人会说:对呀,所以要有“五种底线”。我说:不对,这“五种底线”仍是个人的价值判断,并不能放之四海而皆服。《飘》就与“主旋律”唱反调;张志新、林昭、顾准等人的思想就与当时的“主旋律”相异。除非有人扮演“上帝”的角色,绝对地“真理在握”,否则谁也没有资格在“道”上自定标准,唯我独尊。我们不能再犯“焚书坑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类的错误,“多元之道”总比“一花独放”更能启人心智。利用话语霸权强制学生围绕“一花”作文,学生怎能全面感受春天?让学生自由表达吧!未来在他们手里,评分者不要杞人忧天,越俎代庖,不要以落伍的作文理念去钳制、扼杀超前或“另类”的思维。
那位写《出得厅堂入得厨房之王国维》的女生,深知“另类”将会使自己“罪孽深重”,万劫不复:“最后一句,老师,你就看着给个分数吧,只要你出则对得起天地间的浩然正气,入则经受得了良心的拷问,你就随便给。不然也无可奈何,就算我在任何一条街上咒骂,也不能损伤你一根毫毛。”从这段话乃至整篇,我上看下看左看右看也看不出触犯“五种底线”的地方,除非深文周纳大兴“文字狱”。
在我看来,写作的底线是:不能违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只要不违宪,一切的文字表达都无罪。真正触犯了法律,判决者也当是法官,而不是评分者。要知道得零分的后果是:不仅粉碎了一个考生的大学梦,更可能使她丧失自由表达的勇气。宪法赋予了她“言论自由”的权利,却被评卷者剥夺了她的“受教育”的权利。
在此,我不想过于指责评卷者,因为我、我们也曾犯过这样的错误。但我常常反思,而不是为自己的错误找出冠冕堂皇的理由加以辩护、开脱,甚至于以“一贯正确”自居,继续制造“悲剧”。我们如果在“悲剧”结束之后仍然师心自用,高悬达摩克利斯之剑,那就是“辣手摧花”!
如果这位女生写得语无伦次,偏离考题,判其卷为零分,我百分之百赞同。但如果仅仅是根据两位先生的“这种与时代主旋律极不和谐的音符,是如此刺耳;这种严重的道德偏离,这不仅仅是只是作文的问题,更是做人的问题(注:病句)”的诛心之论,就觉得“不判零分就不足以平民愤”,确实“不仅仅是作文的问题,更是做人的问题”,还尤其是教人的问题。
早在明朝,思想家李贽就认为:“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童心”者,真心也,绝假纯真之思想表达也。这位考生没有曲意逢迎,纯然的童言无忌,全然的不计功利,在不知“恶果”的情况下,仍直率地道出了对社会的个人观点,坦露了真实的内心世界。现在这样的作文被判为零分,“以儆效尤”,只能教会学生说一些四平八稳的话或假话。
两位李先生的高论使我受益匪浅的部分是有关日本作文理念的引述,使我获知日本也“主张作文要有真实性的思想”的。顺着二位先生的路径,也粘贴这几位日本学者的一些语录。
芦田惠之助的“随意选题”说:“阅读之方法即是读自己,写作之方法即是写自己,听话之方法即是听自己,讲话之方法即是讲自己。”
小砂丘忠义的“生活作文”思想:“写真实的事”、“用自己的话写”、“原原本本地、主动地写”;“城市有城市的真实、女人有女人的真实、孩子有孩子的真实、小偷也有三分真实。我期望的就是这种真实的表达,而表达的形式则是第二位的”;“讨厌就写讨厌、愤怒就写愤怒、喜欢就写喜欢,把所想的赤裸裸地表现出来,这样作者对所写的就抱有充分的理由和责任”;“写的题材、表达应是完全自由的。不是要等到要你写才写,不是为了写给别人看才写。学生不是被逼着写,而是(自由地)自己想写,就能写出很好的作文来”;“各人的作文之法就是他的修身、他的历史。换言之就是自己的‘个’之发现”。
野村芳兵卫的“生活学科”思想对“原原本本地、真实地写”的要求作了进一步的具体化:(一)在以成人社会的文化价值标准来论说善恶之前,应让学生自身的眼睛来观察、自己来思考才会有“真实地写”。即是否是学生自身的真实应是第一要求。(二)学生是否能就自己的生活想说什么都说出来了?应当开拓这种发展的自由度——新鲜自由的表达。(三)必须了解学生是否放开眼界涉及生活的各个领域——生活视野的扩大。(四)必须进行将口头语言变成书面的文句的指导。
小川太郎对“自由”是这样诠释的:由于种种偏见,儿童丧失了实事求是地表达自身生活的事实,以及围绕着这些生活的思考、情感的自由。应当让他们从偏见中解放出来,使他们获得观察真实、表达真实的自由。
从这些日本学者的著作中,很容易检索这么两个词:真实、自由。即表达真实情感的自由。没有类似“五种底线”的附加前提。当然,我们应当引导学生写“积极”“光明”的一面,但一旦学生写了“消极”“阴暗”的一面,真实地表露了内心世界或外部世界,也不能棒杀。
我们的作文教学理论也主张学生真实地写出对人生、对社会的感受和认识,真实地表达内心情感。但在实际评价作文时,受“潜规则”操纵,表达了真情实感的作文却屡遭堂而皇之的“屠戮”,让师生寒心。在现实面前,师生都学乖了:既然如此,就世故迎合吧,削平锋芒,“温柔敦厚”。
当只有一条“道”可走的时候,就失去了“自由”,也就无从表达“真实”,师生要做的只剩下机械地进行审题、立意、语言、结构方面的训练。结果,写出来的文章是没有青春应有的活力和激情甚至幼稚、偏激的“新八股”:情感虚假,思想混乱或单调,语言苍白或夸饰,结构套路化,思维模式化。
《作文评分:到语言为止?》(见《中学语文》2007年第3期)对我的拙文《作文评分:到语言为止》(见《中学语文》2006年第12期)提出质疑,一个“?”号表明了李运淼、李在荣先生的全部观点。在两位先生看来,《出得厅堂入得厨房之王国维》被判为零分,判得无比正确,判得不可动摇。二位先生之所以如此坚决,是因为基于这样的前提:一切文章“不能突破人性道德底线、社会道德底线、伦理道德底线、民族尊严底线、时代主旋律底线”,否则“只能得低分或零分,没有理由叫屈”,因为“对作文的评判从来就重视考生作文中反映的‘道’,现在如此,将来亦如此”。
我本不想笔战,但以作文教学的前景计,不敢高挂“免战牌”。其实我的拙文最为看重的就是“道”,与二位先生的论点是一致的:文以载道。但我主张:此“道”既指可已知之“道”或人云亦云之“道”,也可指“个人之道”即个人的观点或“政治思想”,并认为突破性的创新一定萌芽于“个人之道”中,所以就学生的作文而言,只要语言表述“道”或“个人之道”方面属上乘,就应当判高分。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百道并行而不相悖”。以斯陀夫人《汤姆叔叔的小屋》和米切尔《飘》为例,前者歌颂解放黑奴的斗争,被公认为影响历史进程的经典小说,后者赞美南方蓄奴制度,被改编为《乱世佳人》,风靡世界,至今不衰,被公认为经典电影。就道德价值层面而言,前者进步,后者反动。“道”绝然对立,但并不影响人们的评价,仍被公认同是世界名著,何故?语言之效也!何况那得零分的作文,事实上也并没有触犯所谓的“五种底线”。
我之所以特强调“语言”的重要性,是因为基于这样的考虑:无“道”之文则言而无绪,无文之“道”则行之不远。同“道”相争,比的是语言;异“道”相竞,比的也还是语言(语言不好的“道”自行淘汰了)。此“道”与彼“道”,在文化价值层面上并无优劣高低之分,有道是“圣人不曾高,众人不曾低”(李贽语),但在读者个人的价值判断上却有优劣高低或好恶之分的。因此,阅卷者个人的道德价值判断不能成为评分的标准。阅卷者不是“完人”。
有人会说:对呀,所以要有“五种底线”。我说:不对,这“五种底线”仍是个人的价值判断,并不能放之四海而皆服。《飘》就与“主旋律”唱反调;张志新、林昭、顾准等人的思想就与当时的“主旋律”相异。除非有人扮演“上帝”的角色,绝对地“真理在握”,否则谁也没有资格在“道”上自定标准,唯我独尊。我们不能再犯“焚书坑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类的错误,“多元之道”总比“一花独放”更能启人心智。利用话语霸权强制学生围绕“一花”作文,学生怎能全面感受春天?让学生自由表达吧!未来在他们手里,评分者不要杞人忧天,越俎代庖,不要以落伍的作文理念去钳制、扼杀超前或“另类”的思维。
那位写《出得厅堂入得厨房之王国维》的女生,深知“另类”将会使自己“罪孽深重”,万劫不复:“最后一句,老师,你就看着给个分数吧,只要你出则对得起天地间的浩然正气,入则经受得了良心的拷问,你就随便给。不然也无可奈何,就算我在任何一条街上咒骂,也不能损伤你一根毫毛。”从这段话乃至整篇,我上看下看左看右看也看不出触犯“五种底线”的地方,除非深文周纳大兴“文字狱”。
在我看来,写作的底线是:不能违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只要不违宪,一切的文字表达都无罪。真正触犯了法律,判决者也当是法官,而不是评分者。要知道得零分的后果是:不仅粉碎了一个考生的大学梦,更可能使她丧失自由表达的勇气。宪法赋予了她“言论自由”的权利,却被评卷者剥夺了她的“受教育”的权利。
在此,我不想过于指责评卷者,因为我、我们也曾犯过这样的错误。但我常常反思,而不是为自己的错误找出冠冕堂皇的理由加以辩护、开脱,甚至于以“一贯正确”自居,继续制造“悲剧”。我们如果在“悲剧”结束之后仍然师心自用,高悬达摩克利斯之剑,那就是“辣手摧花”!
如果这位女生写得语无伦次,偏离考题,判其卷为零分,我百分之百赞同。但如果仅仅是根据两位先生的“这种与时代主旋律极不和谐的音符,是如此刺耳;这种严重的道德偏离,这不仅仅是只是作文的问题,更是做人的问题(注:病句)”的诛心之论,就觉得“不判零分就不足以平民愤”,确实“不仅仅是作文的问题,更是做人的问题”,还尤其是教人的问题。
早在明朝,思想家李贽就认为:“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童心”者,真心也,绝假纯真之思想表达也。这位考生没有曲意逢迎,纯然的童言无忌,全然的不计功利,在不知“恶果”的情况下,仍直率地道出了对社会的个人观点,坦露了真实的内心世界。现在这样的作文被判为零分,“以儆效尤”,只能教会学生说一些四平八稳的话或假话。
两位李先生的高论使我受益匪浅的部分是有关日本作文理念的引述,使我获知日本也“主张作文要有真实性的思想”的。顺着二位先生的路径,也粘贴这几位日本学者的一些语录。
芦田惠之助的“随意选题”说:“阅读之方法即是读自己,写作之方法即是写自己,听话之方法即是听自己,讲话之方法即是讲自己。”
小砂丘忠义的“生活作文”思想:“写真实的事”、“用自己的话写”、“原原本本地、主动地写”;“城市有城市的真实、女人有女人的真实、孩子有孩子的真实、小偷也有三分真实。我期望的就是这种真实的表达,而表达的形式则是第二位的”;“讨厌就写讨厌、愤怒就写愤怒、喜欢就写喜欢,把所想的赤裸裸地表现出来,这样作者对所写的就抱有充分的理由和责任”;“写的题材、表达应是完全自由的。不是要等到要你写才写,不是为了写给别人看才写。学生不是被逼着写,而是(自由地)自己想写,就能写出很好的作文来”;“各人的作文之法就是他的修身、他的历史。换言之就是自己的‘个’之发现”。
野村芳兵卫的“生活学科”思想对“原原本本地、真实地写”的要求作了进一步的具体化:(一)在以成人社会的文化价值标准来论说善恶之前,应让学生自身的眼睛来观察、自己来思考才会有“真实地写”。即是否是学生自身的真实应是第一要求。(二)学生是否能就自己的生活想说什么都说出来了?应当开拓这种发展的自由度——新鲜自由的表达。(三)必须了解学生是否放开眼界涉及生活的各个领域——生活视野的扩大。(四)必须进行将口头语言变成书面的文句的指导。
小川太郎对“自由”是这样诠释的:由于种种偏见,儿童丧失了实事求是地表达自身生活的事实,以及围绕着这些生活的思考、情感的自由。应当让他们从偏见中解放出来,使他们获得观察真实、表达真实的自由。
从这些日本学者的著作中,很容易检索这么两个词:真实、自由。即表达真实情感的自由。没有类似“五种底线”的附加前提。当然,我们应当引导学生写“积极”“光明”的一面,但一旦学生写了“消极”“阴暗”的一面,真实地表露了内心世界或外部世界,也不能棒杀。
我们的作文教学理论也主张学生真实地写出对人生、对社会的感受和认识,真实地表达内心情感。但在实际评价作文时,受“潜规则”操纵,表达了真情实感的作文却屡遭堂而皇之的“屠戮”,让师生寒心。在现实面前,师生都学乖了:既然如此,就世故迎合吧,削平锋芒,“温柔敦厚”。
当只有一条“道”可走的时候,就失去了“自由”,也就无从表达“真实”,师生要做的只剩下机械地进行审题、立意、语言、结构方面的训练。结果,写出来的文章是没有青春应有的活力和激情甚至幼稚、偏激的“新八股”:情感虚假,思想混乱或单调,语言苍白或夸饰,结构套路化,思维模式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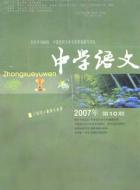
- 我对经典作品教学的一些看法 / 钱理群
- 分析方法的可操作性(下) / 孙绍振
- 关于现代教育技术与中学语文教学融合的冷思考 / 吴 堂
- 从“心”开 / 乔 晖
- 深入中学语文教育第一线,乐作草根博导 / 伍明春
- 教材改革:突破与创新 / 孙慧玲
- “情”到深处不讲“理” / 品茂峰 宋 斌
- 对文学作品语言的敏感性及其训练摭谈 / 胡象光
- 设“专题”探讨,促深化理解 / 陈 桦
- 反思教学找对策,提高学生阅读能力 / 黄玉琼
- 尊重伦理生 / 吕晓乐
- 也谈中学生“作文生活化” / 张 瑛
- 作文访谈录之实用技巧篇 / 赵俊辉
- 高考作文“母语”写作失误例谈 / 钟 瑛
- 谈谈《秦晋殽之战》的节选及叙述艺术 / 李建生
- 亲情的礼赞,生命的高歌 / 李双红
- 《孔雀东南飞》九悲 / 李茂略
- 同为“秋声”赋,寄托大不同 / 罗献中
- 余映潮:《我的叔叔于勒》教学实录与评点 / 余映潮
- 巧设四环节,活化一堂课 / 凌荣毅
- 《最后一片藤叶》多重主题探究 / 周旭荣
- 《阿长与〈山海经〉》一文中情感的跳跃与过渡 / 李朝霞 石海波 石生银
- 《论语》的原生态理解 / 孙铮明
- 文言文诵读五步 / 徐 斌
- 文人、文心与文章 / 陈 菁 何兴楚
- 中学语文教材注释辨误 / 谢序华
- “青鸟”新义 / 李玉洁
- 对父亲的误读 / 陈 涛
- 作文评分:到语言为止! / 黄助昌
- 预支五百年新 / 李弗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