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语文建设 2015年第8期
ID: 359187
语文建设 2015年第8期
ID: 359187
古典诗歌欣赏的基础范畴(四):意境
◇ 孙绍振
意境之美,并不是中国古典诗歌的全部精华所在。王昌龄《出塞》之一,之所以引起争议,就是因为它的后面两句,把豪情直截了当地抒发了出来。王昌龄的绝句,被赞为唐人第一,其实是需要分析的。直抒豪情的诗句,原不是绝句之所长。如《从军行》: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这样的英雄语,固然充满了盛唐气象,但是以绝句这样短小的形式做这样直接的抒情,不免显得单薄,至少不够含蓄,一览无余,缺乏铺垫。最主要的是,缺乏绝句擅长的微妙的情绪瞬间转换。想想李白的“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前前后后,有多少铺垫,有多少跳跃,有多少矛盾,有多少曲折。这种直接抒情,以大起大落为宏大气魄,不是绝句这样精致的形式所能容纳的。意境艺术最忌直接抒发,一旦直接抒发出来,把话说明了,意境就消解了,或者转化为另一种境界了。
这是我国古典诗歌的另一种艺术境界,至今我国的诗学还没有给它一个命名,使之成为一种范畴。它不以意境的含蓄隽永、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为特点,它的特点不是意境式的温情,而是激情,近似于鲍照所说的“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与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的“强烈的感情的自然流泻”亦有息息相通之处。其想象如天马行空,不可羁勒。
中国诗并不仅仅以意境见长,有时直接抒发之杰作也比比皆是;但是,直接抒发容易流于直白,也就是流于“议论”。王昌龄“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之所以引起争议,就是因为其多少有点抽象。当然,并不是所有类似议论的诗句都是命中注定流于抽象的。如李白的“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又如白居易的“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等,皆是千年来脍炙人口的名句。我国古典诗话曾经把这个问题提到理论上得出结论:“无理而妙”。最早是清贺裳(约1681年前后在世)在《载酒园诗话》卷一中所说的:
诗又有以无理而妙者,如李益“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此可以理求乎?然自是妙语。至如义山“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按:李商隐《瑶池》),则又无理之理,更进一尘。总之诗不可执一而论。
他的朋友清吴乔(1611—1695)在《围炉诗话》卷一中发挥说:
余友贺黄公(按:贺裳字)曰:“严沧浪谓‘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而理实未尝碍诗之妙……理岂可废乎?其无理而妙者,如‘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但是于理多一曲折耳。”乔谓唐诗有理,而非宋人诗话所谓理。
这里所说的“无理而妙”,“理”是与人情对立的,与王维形而上的天人合一的物理、事理之“理”有根本的不同,主要是指与情相对立的“实用理性”。最初是宋代《陈辅之诗话》提出来的,说王安石特别欣赏王建《宫词》中的“树头树底觅残红,一片西飞一片东。自是桃花贪结子,错教人恨五更风”,“谓其意味深婉而悠长”。这种说法,太过感性,于理论似乎不着边际。
过了差不多五百多年,明钟惺(1574—1624)、谭元春(1586—1637)在《唐诗归》中联系到唐李益《江南词》中的“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以为其好处是“荒唐之想,写怨情却真切”,“翻得奇,又是至理”,就隐约提出了理论上的“情”与“理”的关系:于情“真切”,乃为“至理”,但又是“荒唐”之想;“无理而妙”,超越通常的“理”(“此可以理求乎”),才是“妙语”,结论是“无理之理”。在思想方法上,他们由此总结出一条,即“诗不可执一而论”。不要以为道理只有一种,从一方面来看,是“荒唐”的,是“无理”的;从另一方面来看,又是有理的,不但有理,而且是“妙理”,很生动。
吴乔在《围炉诗话》卷一中指出“无理而妙”,并不是绝对无理,“但是于理多一曲折耳”。关键是这里的“理”是唐诗的“理”,和宋人诗话所谓“理”,不是一回事。宋人的理是抽象教条之理,而这里的“理”是人情,和一般的理性不同,只是“于理多一曲折”。这就是说,这不是直接的“理”,而是一种间接的“理”。直接就是从理到理,而间接是通过一种什么东西达到理的呢?吴乔没有回答。
徐增(1612一?)在《而庵说唐诗》卷九中尝试做出回答:“此诗只作得一个‘信’字……要知此不是悔嫁瞿塘贾,也不是悔不嫁弄潮儿,是恨‘朝朝误妾期’耳。”意为不是真正要嫁给船夫,而是表达一个“恨”字,恨什么呢?无“信”,就是没有一个准确的期限,造成了“朝朝误妾期”,一天又一天,误了青春。这就是说,这里讲的并不完全是“理”,而是一种“情”。从“情”来说,这个“恨”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过这不是通常的理,可以说叫作“情理”。其境界不是一般的“意境”,而是“情理境”。
通常的理,简而言之,是一种逻辑上的因果关系,因为商人归期无定,所以悔不该误了青春;因为船夫归期有信,所以还不如嫁给船夫。这仅仅是表面的原因,在这原因背后,还有原因的原因。为什么发出这样极端的幽怨呢?因为期盼之切,而这种期盼之切、之深,只是一种激愤。从字面上讲,不如嫁给船夫,是直接的、实用因果关系,而期盼之深的原因,其性质是爱,是隐含在这个直接原因深处的。这就造成了因果层次的转折,也就是所谓“于理多一曲折耳”。沈雄(约1653年前后在世)《古今词话·词辨上卷》说,王士稹(1634—1711)欣赏彭羡门的“落花一夜嫁东风,无情蜂蝶轻相许”,同样可以用贺裳的“无理而入妙”“愈无理则愈入妙”来解释。
从艺术方法上说,意境的内蕴与直接抒发是两条道路,也可以说是一对矛盾,意境回避直白,直白可能破坏意境。要使直白式的抒发变成诗,有一个条件就是要与理(理性逻辑)拉开距离,用我的话来说,就是非理性的,或者超越理性的情感逻辑。可惜这样深刻的规律,古典诗话家往往满足于用篇幅短小的近体诗(律诗和绝句)来阐释,因而显得捉襟见肘。其实,这种无理而妙,妙在理是全面的,而情感是绝对的,《诗经》中比比皆是。如《伯兮》中的:“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这里的好处在于,极端化的,唯一的,这正是情感强烈的表现。又如《黄鸟》中的:“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因为是所爱的,就值得拿一百个人的生命去赎救。
在楚辞中,尤其是《离骚》中更是直接的政治抒情:“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尤未悔。”为了自己的追求,就是死九次(或者多少次)也不后悔。
情感逻辑的绝对化正是诗的妙处所在。宋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中的《有所思》是一首民歌,其于爱情的直白,就更加以情感逻辑的极端化的“痴”为特点: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
何用问遗君,双珠玳瑁簪,用玉绍缭之。
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
摧烧之,当风扬其灰。
从今已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
在古典诗话词话中,与无理而妙类似的还有“痴而入妙”。这样极端的痴法,明明是空想,但骨子里却是极端的爱在起作用。在李白的诗里,主要是歌行体的诗中,与当时或后世的诗人相比,更是把极端化的情感逻辑发挥到以“狂”程度:“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如在被邀人京之时,他竞把自己的狂态不但直接表现出来,而且加以夸耀:“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至于那首著名的《将进酒》中,更是极端:“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如果以理性逻辑来衡量,这是不真实的,历史上因为饮酒则留下美名的,恐怕只有区区的刘伶,名声并不大。
诗的好处恰恰在于这种不符事实、不合逻辑的“无理”。至于白居易《长恨歌》的结尾:
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好就好在,爱情绝对到不受天地空间的限制,而且在时间上也不受宇宙存在的限制。李杨的爱,在这里还是超越了生死的。在开头,李隆基的爱还有“重色”的成分;但是,到了杨玉环“宛转娥眉马前死”以后,已经无色可重了,却仍然爱得神魂颠倒,而杨玉环就是成了仙也不改其爱情。这些都是把感情直截了当地讲了出来,不讲究任何含蓄,不追求“言有尽而意无穷”,谈不上言外之意,完全是言内之意。
这样的经典之作,并不亚于近体的绝句和律诗,原因何在?就在于这种诗歌在理性逻辑来看是无理的,表现了情感逻辑的特征。这种情感逻辑,从内涵上来说,不遵守形式逻辑的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和充足理由律,也不遵守辩证法的对立统一的全面律,而是以片面性绝对化见长。有一点必须再度明确,这种直接抒发绝对化的艺术与意境的艺术,在中国古典诗歌史上是遥遥相对而又息息相通的。
参考文献
[1][清]丁福保编.清诗话:上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27.
[2][清]吴乔.围炉诗话:卷一[M].∥郭绍虞编选.清诗话续编: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478.
[3][清]贺裳.载酒园诗话:卷一[M].∥郭绍虞编选.清诗话续编:第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209,225;[清]吴乔.围炉诗话:卷一,同上477~4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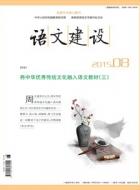
- 卷首语 / 佚名
- 从“去中国化”谈语文教材改革 / 周正逵
- 语文教材呈现传统文化的原则 / 黄厚江
- 也谈传统文化融入语文教材 / 张心科
- 语文教材古代诗词选编刍议 / 胡根林
- 充分发掘汉字的文化内蕴 / 郑飞艺
- 积极语用:为真语文教学注入科学内涵 / 潘涌 杨培培
- 请给文学写作一席之地 / 佚名
- 语文教学也须讲求顶层设计 / 刘仁增
- 关注教学的起点和落点 / 周康平
- 古典诗歌欣赏的基础范畴(四):意境 / 孙绍振
- 那些“看不见”的精彩 / 张小兵
- 《透明的红萝卜》主题的多重意蕴 / 王新惠
- 生而孤独,慰藉常因距离 / 冯永清
- 高考语言文字运用考查的新探索 / 秦思梦
- 高考作文还可以这样考 / 张晋军
- 吴研因语文课程标准研制思想研究 / 翟志峰 王光龙
- 民国国文教材中的胡适新诗 / 刘绪才
- 议论文知识不能如此重构 / 安杨华
- 例谈小学高年级散文教学策略 / 张海滨
- 语言规划范式下的语文教育 / 刘昌华
- 传承经典 文化养心 / 谢惠
- 知天下之脉络 / 赵志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