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语文建设 2008年第11期
ID: 80935
语文建设 2008年第11期
ID: 80935
音乐的连续之美和中断之美
◇ 孙绍振
在唐诗中,以诗表现其他艺术形式的作品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如表现绘画的有杜甫的《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堂上不合生枫树,怪底江山起烟雾……悄然坐我天姥下,耳边已似闻清猿……元气淋漓障犹湿,真宰上诉天应泣。”《丹青引赠曹将军霸》:“良相头上进贤冠,猛将腰间大羽箭。褒公鄂公毛发动,英姿飒爽来酣战。”杜甫追求的艺术效果是用语言形容图画,用连续性的语言表现静态的视觉形象,用文字来表现图画的逼真。
这表明诗人对于诗与画的统一性有着充分的理解,也许正是因为这样,到宋代,就产生了苏东坡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见解。它虽然有些片面地忽略了诗与画的重大区别,但作为诗,用语言表现绘画,追求一种“再现”的效果,功力还是不凡的。但把这种追求逼真的,甚至是乱真的原则,用到表现音乐上去,困难就比较大了。
用诗的视觉意象显示画面,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达到再现的效果,而要以语言来显示音乐的节奏和旋律,就不可能有任何再现的效果。诗人要在诗歌中表现音乐,就必须为音乐旋律寻找诗的语言。
我们来看白居易是怎样承担起这个艰巨的任务的:
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
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
这是一笔反衬,说的是:在动了感情的、送别朋友的现场,却没有音乐。如果光有这样的反衬,还是比较平淡的,因为这只是一般的叙述。接下去,就透露出白居易式的才情了:
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
前面一句用了一个情感比较强烈的“惨”字,和“欢”字构成对比。酒喝醉了,却没有一点欢愉之感倒也罢了,居然产生了一种“惨”的感觉。但是,光是一个“惨”字,毕竟不够具体。为了把这个“惨”具体化,白居易所采取的办法,不是直接去表现诗人的心理,而是提供一幅图画、一个空镜头:茫茫的江水,浸润着月亮,或者月色、月光。无声的画面、寡白的色调,提示着画外一双失神的眼睛。
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
这是音乐的效果:惊异。初闻即如此强烈:改变了心情,“醉”和“惨”都消失了,甚至还改变了主人和客人的原定行动计划,当然也就改变了那画外的失神的眼睛。
寻声暗问弹者谁,琵琶声停欲语迟。
如此急切地追问,可回答却有些卖关子,这是叙事延宕的技巧,是戏剧性叙事的技巧,这个技巧不但用了,而且是加码地用了:
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
这两句成了千古名句,原因在于它创造性地运用了延宕。先是把延宕的效果做足了,“千呼万唤”,是时间的延宕,也是期待的积累;“琵琶半遮”,是时间和人情延宕的二度积累。正是因为这样,这个诗句不但经历了千年的考验,而且在不同的语境中,召唤了、同化了不同读者的心理经验,甚至脱离文本语境,成为独立的谚语、格言。
所有这一切,不过是音乐形象出现之前的背景,为音乐形象出现酝酿氛围。
值得一谈的是,这里用了相当多的叙事手法。主要是事和事的连续性。这对这首诗无疑是必要的。这首诗的立意就带有鲜明的叙事性。但是,中国和西方不同,在中国古典诗歌里,独立的叙事是没有地位的。故叙事往往为抒情所同化,所瓦解。同化和瓦解的特点,就是以抒情诗的想象和跳跃,瓦解叙事的连续性。例如,在《长恨歌》里,唐明皇对杨贵妃的沉迷,导致了安禄山的反叛,唐军兵败,潼关失守,唐明皇仓皇出逃。这么曲折的、连续性的过程,到了《长恨歌》里,就只有两句: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安禄山的战鼓一下子震动了长安宫廷的歌舞,这不是现实的描写,而是抒情诗歌的想象的跳跃,把叙事的连续性过程、其间的现实因果,转变为抒情的、假定的、想象的因果(因为鼓声而惊破)。但《琵琶行》不能像《长恨歌》这样处理,因为《长恨歌》所写的是历史人物,其本事人所共知,不会造成误解,而《琵琶行》所写的却是平凡人物,其故事情节不能用这样大幅度的跳跃性想象。这就给白居易增加了难度:既要有故事情节的连续性,又不能让这种过程性、连贯性妨碍了抒情性。从上面的引文我们可以看到,白居易主要把故事的连续性和人物内在情感的曲折变动结合起来,以内心的动作性来调和叙事和抒情之间的矛盾。一旦进入乐曲本身的描述,故事的过程性就暂停了,白居易面临的任务,就是把曲调和演奏者本人的情感结合起来:
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
诗人写调弦,但又不能停留在曲调上。未成旋律已经有动情之处,什么情?是弹奏者的情感,这是全诗的主线,要注意,相对于这条主线,曲调本身居于次要地位。
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
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
居于主导地位的是演奏者的内心,这是一种简单化的说法。诗人听到的,是不是完全是琵琶女的感情呢?好像又不完全是。诗人从曲调中领悟到的演奏者情感是一种悲抑的情感,这种情感不仅是演奏者的,而且有诗人的,至少是被诗人自己的“不得志”所同化了的。这就使得情感双重化了。但如果仅限于此,还是有所不足,毕竟没有把曲调、旋律之美写透。诗歌当然要以情感人,但如果没有足够的曲调意象,在写曲调旋律时没有超越前人的表现力,动人的情感就可能缺乏载体。
用语言写曲调和旋律,正是难点,就是唐诗,在这方面的积累也很有限。李白有一系列的诗写到听乐曲,如《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
一为迁客去长沙,西望长安不见家。
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还有《春夜洛城闻笛》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
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
这些都是杰作,但并未正面写出音乐之美。因为用语言表现音乐,难度太大,一般的诗人都善于讨巧,大抵取间接的审美感应表现。如高适《和王七玉门关听吹笛》:
胡人吹笛戍楼间,楼上萧条海月闲。
借问落梅凡几曲,从风一夜满关山。
又如李益《夜上西城听梁州曲》,尤其注重从效果上表现曲调:
鸿雁新从北地来,闻声一半却飞回。
金河戍客肠应断,更在秋风百尺台。
至于曲调本身究竟如何,天才如李白也只能从心理效果方面略作敷衍,如他的《听蜀僧?F弹琴》:
蜀僧抱绿绮,西下峨眉峰。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客心洗流水,余响入霜钟。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几重。
这位蜀僧的琴曲究竟美在何处呢?李白没有直接写,而是说,琴声如“万壑松”(涛)一般美好。但是,这只是一种心理效果,细究起来,万壑松涛和一张琴的演奏听觉感受相去甚远。就是白居易本人,也不是每一首都能写出水准的。同样是写琵琶曲的作品,白居易有好几首,如《听李士良琵琶》:
声似胡儿弹舌语,愁如塞月恨边云。闲人暂听犹眉敛,可使和蕃公主闻?
这一首的构思很有代表性,头一句,倒是说到了琵琶的颤音,如胡人卷舌音,第二句说忧愁如塞月,这是对任何乐器都适用的,琵琶曲不过是感兴的由缘而已。
回避正面描写音乐,用情感效果来写乐曲,在绝句中,已经成为一种套路了。正面写出工夫来的,也许可以提到《春听琵琶,兼简长孙司户》:
四弦不似琵琶声,乱写真珠细撼铃。指底商风悲飒飒,舌头胡语苦醒醒。如言都尉思京国,似诉明妃厌虏庭。迁客共君想劝谏,春肠易断不须听。
这里写到了琵琶的弦,写到了弹奏的手指,当然还有对听觉的美好的联想和想象。但是,和大多数的琵琶主题一样,都和征戍和边塞之乡思联系在一起,不但联想而且主题都陷于某种模式。
正面地集中地写曲调旋律,难度太大,因而很是罕见,李颀的《听安万善吹?篥歌》可能值得一提:
世人解听不解赏,长飙风中自来往。枯桑老柏寒飕?,九雏鸣凤乱啾啾。龙吟虎啸一时发,万籁百泉相与秋。忽然更作渔阳掺,黄云萧条白日暗。变调如闻杨柳春,上林繁花照眼新。岁夜高堂列明烛,美酒一杯声一曲。
[##]
比喻很多,但大多比较陈旧,有堆砌之感,对乐曲本身的描写也比较概括。李颀还有一首《听董大弹胡笳声兼寄语弄房给事》算是写到了乐曲演奏本身了:“先拂商弦后角羽,四郊秋叶惊??骸!被坝镆脖冉戏岣唬
空山百鸟散还合,万里浮云阴且晴。嘶酸雏雁失群夜,断绝胡儿恋母声。川为静其波,鸟亦罢其鸣。乌孙部落家乡远,逻娑沙尘哀怨生。幽音变调忽飘洒,长风吹林雨堕瓦。迸泉飒飒飞木末,野鹿呦呦走堂下。……
很明显,用的是赋体,以大幅度的排比的形容来强化乐曲的形象。但是,排比的赋体,是平列的、静态的,缺乏连贯的过程;而乐曲本来是一种时间的艺术,其生命就在于有规律的高低强弱、快慢缓停的变幻之中。
在《琵琶行》中,白居易第一次用诗的语言,以空前的,甚至可以说绝后的气魄,正面集中写了琵琶乐曲的起伏变幻过程,包括演奏乐曲的动作和曲调的程序:
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幺》。
具体到了演奏的动作,连曲调的名称都出现了,这好像有点往叙事方面靠拢的冒险。但接下来更是冒险,居然以赋体的平行句来展开:
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
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
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
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
从纯形式上来说,一连四个句子,好像是平行的,如果真是这样,就成了赋体了。白居易的成就,就在于对赋体的节制性运用,适当地对称,又伴之以错综。实际上,只有前面两句的句法是对称平行的,到了第三四句,句式就变化了,不再用对称的句式,而是用有连贯性的“流水”句式,不再作平面的滑行,而是略带错综的句式。下面的四句,也有类比的考究。两句对称(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接着的两句(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又打破了对称的平衡。这就使得这八句既有统一性又不单调,处于错综的变化之中。
从意象上说,前四句以物质的贵重引发声音美妙的联想。当然,这只是诗的美好想象,实际上,珠落玉盘,并不一定产生乐音。“嘈嘈”“切切”这样的闭塞磨擦音,本身可能并不能产生美好的感觉,但是,和“急雨”和“私语”联系在一起,就比较有情感的含量。“私语”没有问题,有人的心情在内,“急雨”和“私语”对应起来不难逗起对应的情致联想。早在开头的序中就交代了妇女的命运:“本长安倡女,尝学琵琶于穆、曹二善才,年长色衰,委身为贾人妇。”这样的乐曲和这样的语音自然构成了悲郁的沧桑的氛围。接下去的“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错综不仅仅是在句法形式上而且是在声画交替上。这就是,前四句是以听觉的美为主,后四句是视觉图画(花底流莺、冰下流泉)和听觉声音(莺语、幽咽)交织的美。唐?先生曾经在80年代初期撰文,说这四句美在声韵上双声和叠韵(间关、幽咽)。但是,此说似乎太拘泥。诗歌艺术的美和音乐的美不同,只是一种想象联想的美的情致,不能坐实为实际上的声音之美。如果真的把珍珠倒入玉盘,如果把流莺之声和水流之声用录音机录下来,可能并不能成为乐音的。这里意象的综合效果是,珠玉之声、莺鸟之语、花底冰泉,种种意象叠加起来,美的想象交融,诗意格外浓郁。
白居易的惊人笔力不但在于用意象叠加写出了乐曲之美,而且还在于把连贯性的过程作了充分的强调。过程性、时间的连续性是音乐与绘画的重大区别,在这一点上的成功,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简单理论所难以解释的。最为突出的是,乐曲的停顿既无声音又无图画,恰恰又能反衬出旋律的抑扬顿挫。令人惊叹的是这样的句子:
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
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
用美好的声音来形容音乐,是唐诗共同的追求。白居易的突破在于:第一,从“冷涩”这样看来不美的声音中发现了诗意,为主人公和诗人的感情特点(天涯沦落)找到了恰当的交接点。第二,从“凝绝不通”的旋律空白中发现了音乐美。这是声音渐渐停息的境界,从音乐来说是停顿,是旋律的空白,但并不是情绪的空档,相反却是感情的高度凝聚。是声音的渐细渐微,又是倾听者的凝神。外部的凝神必然导致对内在情绪细微的导引,外部乐音的细微,化为听者自我体验的精致。内心深处的情致是以“幽”(愁)和“暗”(恨)为特点的,也就是捉摸不定的、难以言传的,在通常情况下,是被忽略的,自发地沉入潜意识的,而在这种渐渐停息的微妙的聆听中,却构成了一种从外部聆听转入内心凝神的体悟:声音的停息不是情感的静止,而是相反,是“幽”和“暗”愁恨的发现和享受,正是因为这样,“此时无声胜有声”才成为千古佳句。
无声为什么比有声更为动人?因为,无声的内心体验更精彩、更难得。在千百年的流传中,“此时无声胜有声”成了家喻户晓的格言,不但是诗,而且是哲理的胜利。停顿之所以有力,是因为它和前面的音响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一般说,如果停顿安排在结尾,这是很平常的,但白居易却把它安排在当中,在两个紧张的旋律之间。在停顿之后又接着来了紧张的旋律:
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
诗人强调了有声旋律出现的突然性(乍破、突出),增加了戏剧性的冲击力,这是由两幅鲜明的图画带来的。是贵金属的破裂和冷兵器的撞击,在两个极点上的张力。这不是“诗中有画”所能解释的。一般地说,图画是静态的、刹那间的,而这里的图画,却是“动画”,具有强烈的动作性。白居易超越前人和自己的地方,主要是用语言图画的动态,使旋律和节奏的动静交替得到充分的表现。这种动态和动静交替,不但表现为旋律的变动,而且表现为骤然的停顿和突然再度掀起的冲击力。这种突然停止和骤然掀起,不是孤立的,而是旋律的呈示和再现,因而就是再现也没有重复感:
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
这是第二次休止停顿,不但是响亮的,而且是破裂性的,把这种破裂和丝织品结合在一起,其声音和第一次的“冷涩”“凝绝”的幽暗不同,既不是突然的,也不是渐次的,而是高亢而凄厉的。在此背景上,第二次休止出现了:
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
这已经不仅是乐曲的停顿,而且是停顿造成的心理凝聚效果。听者的心被感染的状态并未消失,而是相反,依旧沉浸在那还没有结束的结束感之中。这种宁静的延长感,诗人用一幅图画来显现。这是一个空镜头,是无声的,又是静止的。江中秋月第二次出现了。这是不是重复了呢?《唐诗选脉会通评林》引唐汝询曰:“一篇之中,‘月’字五见,‘秋月’三用,各自有情,何尝厌重!”此人认为不重复,原因在于,“秋月”重见,各有不同的情感。第一次,“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写的是分别时的茫然和遗憾。而这里的“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则是另一种韵味,写众多的听者仍然沉浸在乐曲的境界里,这个境界的特点,就是宁静,除了这种宁静,什么感觉都没有,就连唯一可见的茫茫江月,也是宁静的。这恰恰提示了一双出神的眼睛。
白居易这首诗妙在把乐曲写得文采华赡,情韵交织,波澜起伏,抑扬顿挫,于无声中尽显有声之美,于长歌中间穿插短促之停顿,于画图中有繁复之音响。的确超凡脱俗,空前绝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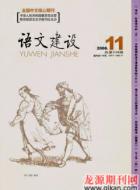
- 回归经典,练就佳作的现实指向 / 姚赛男
- 有米之炊仍须待巧妇 / 许 倩
- 2008年全国高考名言名句考查统计分析 / 桑 哲
- 说“被指” / 孙建强
- 这个标题要不得没 / 赵晓驰
- “凭什么”带来的尴尬 / 尹海良
- “假寐”释义辨析 / 陈祝琴
- “明”是而“照”非 / 王彤伟
- 《装在套子里的人》选文与原文的比较阅读 / 郑 艳
- 音乐的连续之美和中断之美 / 孙绍振
- 我给儿子发稿费 / 周国勇
- 推介写日记的理想方式:合作日记 / 武宏伟
- 现当代诗歌鉴赏的“四要” / 费淑艳
- 如何指导学生阅读鉴赏文学作品 / 张华娟
- 女性教师的语文课堂教学缺少什么 / 付 宁
- 关于重读经典的讨论 / 柯晓琳
- 名不正则言不顺 / 任为新
- 在预设与生成中提升教学智慧 / 温欣荣
- 《项脊轩志》教学实录 / 呼 君
- 《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教学设计 / 刘丹妮
- 《滕王阁序》教学设计 / 颜碧伟
- 语文阅读教学助读资料筛选策略例谈 / 李 琳 钟菊莲
- 三版语文教材中标点符号的规范问题 / 颜丽娟
- 小学语文教科书文化价值的取向与构成 / 朱家珑
- 论点摘编 / 佚名
- 李白、杜甫诗中的“月” / 蒋绍愚
- 温故知新 / 饶杰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