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语文教学与研究·综合天地 2011年第7期
ID: 140551
语文教学与研究·综合天地 2011年第7期
ID: 140551
浅论孔子的人格完善之路
◇ 黄澄华
作为影响中国几千年的思想巨人,孔子,他的智慧是无法估量的。他的“仁”与“智”思想都植根于人的本性,“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1]。这样,内外才能合二为一,成为随时可施行的准则,这种观点至今依然影响深远。
我们知道,儒学是孔子对春秋时期文化精神反思后建立起来的以西周初年形成的礼乐文化为基础的“仁”学思想体系。在“礼崩乐坏”的时代,先秦的哲人们普遍都有重建社会秩序、重建人文信仰的自觉,并以此为出发点确立他们自己的历史使命。这是对个体自我完善的道路探寻的开始,也就标志着人的觉醒的开始,而孔子的追求可能更早更完整些。《论语·为政第二》中孔子自述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这由年岁来描述个体成熟的不同阶段及状态的千古名言,常被用来解释孔子个体人格完善追求的最好佐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更成为个体的人与外在的社会完美统一的体现,令后世文人追随不已。
但是我们在充分肯定这一追求的完善时,不应忽视这一过程的形成实际上也是孔子“仁”学思想体系在人的问题上思考的结果,有其自身理论发展的逻辑必然性。
一.人的独立地位的确立,是个体自我完善的基础
对孔子的“仁”的理解,林语堂在《孔子的智慧·导言》中说,“孔子的哲学精义,我觉得是在他认定‘人的标准是人’这一点上。”[2]《说文解字》解释说“仁”时说:“仁,亲也,从人二。”古文字学家段玉裁注曰:“独则耦,耦则相亲,故字从人二。”可见,“仁”字的本义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亲密。而孔子将“仁”作为自己思想体系的核心,其指向仍然是人事。孔子说“仁者,人也”,明确地表明仁学的建构肇始于对人本身的认识和对人的本质价值属性的反省。[3]这种对人的自觉与关注正是孔子发现人与神与动物之区别而产生的理性认识,更难得的是这一理性的认识是建立在人的天然感情基础之上的。《论语》中对仁的记载,重要的有以下几条:
(1)、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雍也》)
(2)、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雍也》)
(3)、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
在这些条文中,“克己复礼”的行动纲领“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要求一切行动以“礼”为准绳,它更多要诉诸人自身的修养。孔子提出“仁者爱人”,这个“爱”字里,包涵着丰富的内容。
首先,这种爱与动物的本能之爱不同。《乡党》中记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爱人胜于爱物。“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为政》)可见孔子对人的本质有着清醒的认识,明确地区分出人与禽兽的差别,对两者的感情也是不平等的。孝与敬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孔子认为“君子谋道不谋食”(《卫灵公》),“笃信善学,守死善道”,这里的“道”也是指“人道”[4],他时刻提醒每一个知识分子,要有以道自任的精神,要超越个体的利害得失,“仁者爱人”,把这种精神推广至对整个社会的深厚关怀上。他还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微子》)人明显高出禽兽许多,其根本就在于人关注天然感情的精神层面,而非单纯的物质层面。
其次,这种“爱”又是可以主观努力取得或接近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颜渊》),虽然孔子也对生死富贵等事发出无可奈何之叹,“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宪问》)。但又认为人在听天命之前,一定要尽人事。他自信地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述而》)“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将人的现实使命与天意相连,这既是对天命的清醒认识,也是积极人生观的体现。它表明人立于天地之间,自是有其作用的,用孟子的话说就是“天生我材必有用”,“我欲仁,斯仁到矣”(《述而》),突出人的主体能力。同时,这种“爱”又是以家族和宗族为中心,由内及外,由近及远,由亲及疏辐射开来的有差等的爱。它植根于现实人生,是对人的行为具体化的规范。作为“弟子”应当“入则孝,出则悌”。至于圣人,那就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达到的道德高度了,平常的人能做到仁者已经很难得了。
所以说,“仁”是孔子仁学体系个体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同时,它又是道德修养自我完善的最终结果。为此,孔子提倡“学而知之”。他自己便是十五而“志于学”的。“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不学习有许多蔽端,会损害道德品格修养,不仅达不到目的,反而会走向反面。学习的最终目的是“下学而上达”,通过对道德知识和文化知识的学习,促进自己德行的完善,达到“文质彬彬”的理想人格。这不仅仅是孔子自己的修养之路,同样也是一种鼓励人向善而行的方式。
二.个体完善的过程是一个道德修养不断内化的过程
个体完善的过程也是一个道德修养不断内化的过程,它的行为准则就是“礼”。张岱年在《中国伦理思想研究》中反复强调,“道德所以为道德,在于不仅是思想认识,而更是行为的规范。道德决不能徒托于空言,而必须是见之于实际行动。”[5]因为“仁”是人的本质,是修己,是爱人的内在自觉性;“礼”是人们的行为准则,体现了社会对人的外在约束。若只有内在自觉而无外在约束,人人按自己的标准行事,就不能保持尊卑、上下、贵贱的秩序,就会引起社会混乱,那样离“仁”德就远了。因此,必须要“克己复礼”,以“礼”的准则行“仁”,以“仁”的自觉复“礼”,才能使“天下归仁焉”。
孔子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在漫长的一生中,他有自己“一以贯之”的道。虽然现存的资料不够准确地告诉后来人这“道”到底指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不是指具体的好学多智,也许仅是在学的过程中的一种信念,一种执着的精神吧!就像他自己所说有“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耳”。它并不能用一个“仁”、“礼”、“忠恕”等字来囊括的,因为这种精神是深存于孔子思想之中,并广泛地运用于生活的各方面,为学、为政都可见其踪。所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做一个“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公冶长》)的人。至于如何达到这一目标,孔子有自己的实现之路,就是“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实际上,孔子的所谓求学之路,就是把外在的“礼”的规范内化为“仁”的修养、并反映在行动上的过程。当然,“路漫漫其修远兮”,这并不是容易事,只能在不断的实践中得到提高。后世常称孔子之学说为“成德之教”,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更有学者将它称为是“成人”之路,如杜维明就说,“成年就意味着成人”,“对孔子来说,‘学’不只是取得经验的知识,也不只是在社会中使适当的行为方式内向化的方法,而是使自己成为自觉的人”。[6]
春秋之际,“礼崩乐坏”,孔子虽然一直强调恢复周礼,但混乱的社会政治局势,已使依靠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来推行其所提倡的“周礼”的设想流为空谈。在外在权威已失去其力量与作用的时代,孔子反身向内,用心理原则的“仁”来解说“礼”。故其学说之核心也逐渐由“礼”转向“仁”,这种转变的实质在于把复兴周礼的任务和要求直接去交给个人,要求个人自觉地、主动地承担这一任务,并把它作为个体存在的至高无上的目标和任务。在这种自觉的追求过程中,孔子将个人的道德完善提高到无上的地位,一切行为的最终目的都应当指向个体道德的完善。这种道德的完善是超越的、永恒的,是一切行为“发而中节”的内在依据,也是树立外在权威的主观保证,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说的正是这个意思。因此孔子所言之“不踰矩”的“矩”,当从道德方面加以阐释。“礼”之制定,亦植根于人内在自觉的道德追求。
三.自我修养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它也诉诸他人认同
从“志于学”到“从心所欲”,孔子的这成人之路,最后就是要达到一种和谐融洽的心灵境界,它表面上是个人修养过程的描述,是孔子人格完善的体现,实际上我们也不能忽视每一阶段的背后都指向他人,即在自我修养自我肯定的过程中,总也无法脱离人外在的因素。
“志于学”,许多人由“立于礼”,推出“学”就是学礼。这样理解也有一定道理,但我们也要看到,孔子虽自谦地声称,他只是传授文化的人而已,实际上他却是在改造礼的实践。[7]他的学不仅仅是学礼、成为一个守礼的卫道士,而是要通过学改变原始人性中的弱点,达到仁人或君子的理想人格。所以他的学的内容应该更加广泛。有人将它总结为六大方面[8],也许更准确些。当然,并非说人人都要成为一个完美的人、全能的人,孔子的本意也不在于此。“上学下达”,“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焉”等等,这里的每一句才见孔子的理想,学的目的是完善自我,它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才使到“三十而立”时,能形成一定的世界观与人生观,所谓“能自立于斯道也”[9]。“四十不惑”,则无所疑矣!面临的问题就是对所学的理解,并确立“志”的合理性,以及加以维护了。
到了“知天命”“耳顺”“从心所欲,不踰矩”的阶段,它一方面仍孜孜以求地“上学”,另一方面却诉诸于在任何外在的环境中,他都能保持良好的心态,从容的面对一切人与事。这里强调的修为,是如何面对他人的目光。也就是说,在个人的完善过程中,实际上并不能脱离世人的目光,这与道家的“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的心态是完全不同的。也正是这样的心态,决定了孔子求学之路是漫长的、长远的,它不可能是高高在上、超尘脱俗的,也不可能是一个封闭的过程。如果“内圣外王”[10]是孔子人格修养的终点的话,那我更相信,“内圣”与“外王”本身是不平等的,自我的修养要低于外在的体认,这种体认可以是别人对自己的认同,也可表现在对别人模仿、学习。所以,他一方面打破贵族对“礼”的垄断,把周礼规定的某些活动作内容、性质上的置换,即保留活动的形式,赋以新的意义和内涵,使更多的人能参预礼的活动。另一方面,孔子试图通过礼的内圣化和简化其外在形式把礼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庶民百姓,用礼的规范来提升他们的行为。[11]可以说,仁者,是孔子人格修养的起点,也是其终点,而中间过程却要求得到世人的认可,它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而是以仁的理想外化的过程中自我得到世人的认同为依托的,并循环不已的过程。也正因为如此,这种人格修养才具有永久的生命力,不至于僵化成为呆板的教条。后人如果忽视了这一点,无疑是离孔子的本意越来越远了。
总之,孔子对人的一生有着清醒的认识,“知天命”阐发的是其学说十分注重人,他把“知天命”放在自我修养历程的一个重要位置上,“仁”“智”“勇”俱全,不违天也不听命,才是人的立身处世应有的生命进程!
参考文献:
[1]孟子《中庸》出自《五经四书全译》[M],陈襄民等注译,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
[2]林语堂著《孔子的智慧·导言》[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5第一版,第9页。
[3]刘宗贤、王佃利《孔子仁学的双重建构——儒家人文思想发微》[A],选自《儒家伦理: 秩序与活力》[M,刘宗贤著,济南: 齐鲁书社, 2002
[4]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987.12。
[5]张岱年《中国伦理思想研究》[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4第1版
[6][美]杜维明《人性与自我修养》[M],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8第1版。
[7]《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之《自我的正统建构》[M],田根胜、余意主编,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
[8]参见匡亚明《孔子评传》[M],济南:齐鲁书社,1985.3第1版。第51页。
[9]《四书五经》[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5.7第1版,第43面。
[10]阎钢,《内圣外王——儒学人生哲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9
[11]潘富恩、徐洪兴、朱志凯主编《孔子思想研究》[A],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9第1版。摘自其中汤勤的《孔子礼学新探》,第297页。
黄澄华,广东揭阳职业技术学院讲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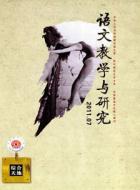
- 摸刀 / 刘庆邦
- 远去的美丽家园 / 陈青山
- 语文自学能力的培养 / 郑结铭
- 问题教学法在语文教学中的运用 / 李春亮
- 他山之石与本山之石 / 梅友成
- 注重语言文字理解能力的培养 / 沈文涛
- 循本导源 读写相长 / 尤昌镇
- 摭谈文言文的翻译 / 梁隆江
- 培养中学生良好的注意习惯 / 滕建波
- 诗歌教学的基点问题 / 周智
- 调动内因 促进学习 / 何能杰
- 走出文言文教学的困境 / 朱招兰
- 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和探究热情 / 邓励平
- 从标题入手探究语文学习的内涵 / 贺丙奇
- 留白:让语文教学充满艺术之美 / 马宏书
- 浅谈语文跨学科学习的特性 / 王立
- 语文教学中的美育途径 / 侯素秋
- 读与写的延伸探讨 / 吴春燕
- 快乐阅读 快乐写作 / 徐兰平
- 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审美教育 / 高二妹
- 强化文学教育 提升人文素养 / 汪小刚
- 关注学生 促进发展 / 李秀文
- 语文教学中学生审美能力的培养 / 李荣
- 让学生爱上语文课 / 王水清
- 让汉字教学真正走进语文课堂 / 刘纯清
- 以阅读促进写作能力的提高 / 王克勤
- 让好的阅读习惯在不知不觉中养成 / 张守华
- 情感是阅读教学的生命水源 / 周英萍
- 创新求异始于积累 / 王丽丽 乔霞
- 培养学生作文创新的能力 / 覃宁
- 一句话的美丽 / 陈兆刚
- 让学生作文由难变易 / 钟鸣
- 浅谈新课标背景下的作文教学 / 王小庆
- 提高初中生课外文言文阅读能力 / 王恒
- 如何培养初中生的阅读兴趣 / 韩娟
- 通过观察创建作文材料库 / 牛丽琴
- 农村中学课外阅读现状及思考 / 杨兆宝
- 学生作文素材的积累 / 侯明强
- 材料作文如何准确立意 / 张冬梅
- 如何让作文充满音乐美 / 姚慧
- 联系学生实际 指导阅读教学 / 栾小平
- 初中生作文创新能力的培养 / 金光明
- 语文阅读教学的策略 / 唐大元
- 一枝一叶皆文章 / 李红梅
- 由情入手提升阅读审美能力 / 张杰 王军峰
- 由一堂作文讲评课引发的思考 / 张红梅
- 阅读教学中的揣摩语言法 / 邹德华
- 写作能力培养的基本定位和主要途径 / 赵景异
- 探索小说阅读教学的方法与技巧 / 陈丽杏
- 阅读之水与作文之成 / 王艳林
- 怎样让课文走进作文 / 李成建
- 加强作文评改的针对性 / 张文钦
- 针对作文批改的一点探索 / 罗喜军
- 将学生的阅读兴趣引向经典 / 沈汝华
- 中学生语感能力的培养 / 周启德
- 构建高中语文高效课堂策略 / 尹钊东
- 高中科普文阅读的三个视角 / 吴神兵
- 《智取生辰纲》的情节艺术特点 / 万永红
- 利用网络构建开放式语文课堂 / 郝艳
- 《滕王阁序》与《兰亭集序》比较阅读 / 周霞
- 《沁园春.雪》的抒情艺术 / 高续华
- 语文课堂教学的提问技巧 / 钟华英
- 精心设置问题 提高课堂效率 / 龙贤
- 我教《差半车麦秸》 / 金利平
- 《广告创作》综合实践活动课例 / 李春梅
- 杜甫《登高》的诵读赏析式教学 / 张小平
- 注重导入环节 打造高效课堂 / 朱建波
- 引导学生有效参与语文智慧课堂 / 叶宝金
- 抓好管理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 宋海霞
- 《背影》一文艺术留白的探究 / 高德利
- 《我有一个梦想》演讲艺术浅析 / 陈华
- 构建初中学生自主成长教育模式 / 邓绍志
- 新课程背景下师生关系的重建 / 周多权
- 语文教学中问题导学法的操作浅析 / 徐大娟
- 活动单导学模式中的小组展示 / 黄丽芳
- 《济南的冬天》独特的艺术美 / 梁健
- 农村中学语文综合性学习的开展 / 刘永
- 简析《诗经.国风》中女性的爱情 / 陈诚
- 浅论孔子的人格完善之路 / 黄澄华
- 中学语文教学学案探讨 / 吴中侣
- 论余华小说中的农民形象 / 夏学明
- 中学语文教学的困境 / 秦宪亭
- 文言文教学中的问题及应对措施 / 王淑红
- 金牌备课组的成长之路 / 朱明强
- 中考古诗阅读题应对策略 / 周建祥
- 中考语文复习活动单设计摭谈 / 苏乔明
- 文言文阅读解题思路点拨 / 何永杰
- 探究式教学反思 / 叶士娟
- 语文教学中合理利用多媒体的探讨 / 陈仕娥
- 宽对其实也很美 / 肖木贵
- 实现语文的人文性是一个系统工程 / 朱耀明
- 在纽约的一天 / 陶逸民
- 课本插图功不可没 / 王辉
- 新课程背景下语文教师的文化素养 / 吕红
- 在学习中反思 在实践中成长 / 刘美廷
- 漫话影响师生关系的因素 / 田儒齐
- 爱与责任 / 单云方
- 诗三首 / 詹颖
- 一份录取通知书 / 王哲
- 科学管理谱新篇 / 陶玉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