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9年第7期
ID: 135867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9年第7期
ID: 135867
文学定篇的特点及存在方式
◇ 胡根林
在文艺界,文学经典化在很长时期内是个学术热点。人们认为文学经典化实际有两层含义:其一,过去时代那些文学作品,在刚创作出来时并不是经典,但它们在问世后引起了的强烈反响,并经受了时间考验;其二,在特定的文学的整体场景中,文学作品的面貌被后代重塑,具有了典范和标准的意义①。对文学“定篇”来说,这两层含义可以作这样的理解:其一,某一文学作品在刚选入语文教材时,并不具有“定篇”的性质,但选入以后受到广泛好评,经过一代又一代师生的教学,后来逐渐成了“定篇”;其二,在特定的语文教材中,入选的文学作品本不具有代表性,但经编选者的有意组合与阐释,具有了代表某一类文学作品的示范意义。前者表明“定篇”的形成过程及其动因,后者表明“定篇”在特定语文教材中的建构方式。
一
作为文学经典的“定篇”,其形成过程和建构方式,大致具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稳定性与流变性的统一
从形成过程看,文学“定篇”具有稳定性和流变性,是“定”与“不定”的统一。从具体篇目看,有些课文是作为“久经历史考验”的传统“定篇”保存下来的,得到各时期语文教材编者的普遍认同。如《皇帝的新装》《背影》《荷塘月色》《济南的冬天》《祝福》《药》《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促织》《美猴王》《鲁提辖拳打镇关西》《雷雨》等,体现了“定篇”稳定性的特征。但另一方面,文学“定篇”又具有“不定”性。这种“不定”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定篇”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过程”,具有一种构造性;二是“定篇”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们观念的更新,具有更改变动和再选择的特点。清代赵翼在《诗论》中曾说:“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从语文教材发展历史看,几乎所有的定篇都要面临“确立—打碎—重组”的过程。
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的《诗经》,其经典地位至今无人可以撼动。但在不同时代,受文学观和教材观的影响,其选入中学语文教材的篇目变化是很大的。以建国后人教版中学语文教材为例;1956年汉语、文学分科时期,《文学》教材选了不少《诗经》的篇目,初中第三册有《木瓜》《采葛》《君子于役》3篇,高中第一册有《关雎》《氓》《黍离》《伐檀》《蒹葭》《无衣》6篇。这些篇目反映了当时人们劳动、爱情、反对阶级压迫剥削和对生活的感受等多个方面。1957年“反右”斗争后,分科教材受到了批评,有人指责它“厚古薄今,脱离实际,脱离政治”,并质问“今天全国人民以无比的干劲建设社会主义,现行教材却编选了一些消极避世、闲情逸致、儿女情长的作品教育学生,这与今天轰轰烈烈的时代合拍吗?”②很快,这套教材被停止使用。取而代之的是类似政治性读本的1958年教材。1958年教材选文趋于政治化,所选多为当代作品,把《诗经》入选的篇目完全删去。其后,1963年人教版高中语文第五册、1978年第一册、1982年第一册、1990年第五册虽都选了《诗经》中的篇目,但在选篇上完全一致,都是《伐檀》和《硕鼠》。这两篇主题雷同,都反映阶级压迫和剥削内容,长时期以来成了语文教材以不变应万变的保留篇目。直至1996年以后,人教版语文教材的面貌才得到改观,其高中教材除了保留《伐檀》外,还增加了反映爱情生活的《静女》等篇。
(二)原生价值与教学价值的统一
从形成动因来看,文学“定篇”一方面具有突出的文学价值,另一方面也必然具有独特的教学价值。作为文学经典的“定篇”,其文学价值是无可置疑的。有研究者认为,一篇文学作品之所以能成为经典,其文学上必定具有如下价值③:1.在作品所表达的内容方面,以挖掘和表现人性的“深”和“广”为追求。向内,开拓和突进人的心灵和情感世界;向外,展现或涉及广阔的社会、历史和人生内容。2.在作品的表达形式方面,作为文学的组装“元素”和技术手段,文字特点、结构形态、视角选择、叙事方式、形象构成、意象营造、意境设置具有自身独特的追求。3.能激发读者改变艺术口味和习性,转换看取世界和艺术的思维和立场,激活深藏在人类心灵深处的艺术潜能和艺术感受力。4.独特而不可替代,通过对美的追求并在作品中塑造了美,具有“美学的尊严”(波德莱尔语)。对文学“定篇”而言,这些文学价值是其原生价值——作为一种社会阅读客体存在所具有的传播事实或情感信息的价值。但作为一个教学文本,它应该还具有独特的教学价值——即怎么传递这些事实或情感信息的价值。
文学“定篇”的教学价值体现为两个层面。其一,文化的接触。朱自清在《经典常谈》序中说,“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阅读经典的用处,就在于教人见识一番”④。法国通过让学生学习中世纪的英雄史诗、16世纪的狐狸列那的故事、17世纪的古典戏剧、18世纪启蒙哲学、19世纪的小说诗歌,使其“掌握法兰西文化的基本要素,并且形成鲜明的个性”⑤。日本通过让学生接触经典,加深对本国文化传统的关心,“扩展对经典作品的见解、感受和思考,培养喜爱经典作品,并借此丰富人生⑥”。其二,供学生效仿。作为“定篇”的经典,其“典范”之中包含着“可供效仿”的含义。由于文学经典本身既是一个时代文学的高峰,又是人类丰富的精神库存,因此,这种效仿可以是写作技巧、谋篇布局,也可以是审美要素、思想内核、精神意蕴。从精神文化这个层面上说,在我国传统文学经典之中,关注民族命运,热爱祖国,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主题,历几千年而不衰。从战国时代屈原的《离骚》,到汉代苏武被拘匈奴19年而不辱节,杜甫的忧国忧民诗篇,岳飞的精忠报国,文天祥高唱《正气歌》,顾炎武“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呼吁,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可谓代不隔绝,一路传唱下来,形成了中国文学一道感人至深的风景线。这些作品成为“定篇”,有助于使学生的爱国情、民族心坚定、纯洁、高尚起来。
(三)诗歌学与解释学建构方式的统一
从存在方式看,文学“定篇”既有诗歌学的建构方式,也有解释学的建构方式。所谓诗歌学和解释学,是指文学研究的两种基本模式。诗歌学研究原来属于语言学范畴。索绪尔结构语言学所提出的共时语言学理论,把语言作为一种功能系统来理解,从共时的角度观察语言,努力把这个系统中语言的形式和意义得以存在的规则和程式说清楚,也就是从语言的效果出发,说清楚这个效果是如何产生的。这个思路被文学理论家们所借鉴,并运用到文学研究中来。而解释学的模式则是从法律和宗教领域中借鉴的。人们试图对具有权威的法律文本和神圣的宗教文本加以解释,目的是对如何行动做出决定。
这两种模式在文学研究领域中得到确认是近年来的事。当今西方文学批评界活跃而有影响的理论家,美国结构主义文论家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o)在他的理论著作《当代学术入门:文学理论》(Literary Theory: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1997年出版)中提出,“在文学研究中也有一个经常被忽略的基本区别,就是两个课题的区别:一个根据语言学的模式,认为意义就是需要解释的东西,并且努力证明为什么意义会成为可能。另一个与其相反,它从形式开始,力图解释这些形式,从而告诉我们这些形式意味着什么⑦”。前者指的就是诗歌学,后者则是解释学。这两种模式在所取路径上是不同的,“诗歌学以已经验证的意义或者效果为起点,研究它们是怎样取得的。而解释学则不同,它以文本为基点,研究文本的意义、力图发现新的、更好的解释”,“以意义或效果为出发点的方式(诗歌学)与寻求发现意义何在的方式(解释学)有着根本的区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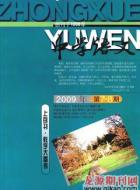
- 孙绍振漫论 / 潘新和
- 高中语文课程改革的若干要点及需要注意的问题 / 王本华
- 世纪之争:重读,还是重写? / 朱建军
- 文学定篇的特点及存在方式 / 胡根林
- 从钱梦龙“三为主”教育思想看新课程改革 / 潘冠海 陈 敏
- 语文教学:借助“工具”渗透“人文” / 欧阳芬 王家伦
- 孔子的教育之道(七) / 韦志成
- 论胡适的文学教育观 / 赵海红 张天明
- 语文课堂教学中问题情境的创设 / 何新华
- 化“综合性课程”为“语文综合性学习” / 陆 培
- 蔡元培美育思想对现代语文教育观的影响探析 / 柯华桥
- 浅谈朗读在语感教学中的作用 / 王 颖
- “文本解读”与阅读教学知识更新 / 荣维东
- 语文教学视角的地域文化 / 冯江明
- 语文阅读教学中的主问题设计 / 任明新
- 语文名师与当代语文教育范式的建构 / 陈元辉
- 中学语文课本中古典诗歌的人生智慧 / 李晓颖
- 语文教育与人的完整性建构 / 赵 蕾 曹明海
- 经世致用与诗意人生 / 吴智勇
- 与心灵接触的情感教育:语文教学的灵魂 / 赵 蕾 曹明海
- 矫正中学作文的浮躁之弊 / 石修银
- “细读”举隅 / 史绍典
- 怎样才能达到议论的深度 / 朱庆和
- 新课堂中对文本主旨解读的反思 / 茹红忠
- 为高中作文教学号脉 / 侯志林
- 语文课堂设计的文本意识 / 武立伟
- 苍凉,抑或温暖的叙说 / 高伦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