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10年第3期
ID: 136158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10年第3期
ID: 136158
文学教学的去魅与重构
◇ 胡根林
主持人简介:王荣生,语文课程与教学论博士,上海师范大学学科教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执行主持简介:胡根林,语文课程与教学论博士,上海市浦东教育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纵览2009年这一年语文教育界在文学教育教学方面所做的工作,有一种现象非常引人注意,那就是:文艺学、文学理论的研究成果被集中地、大规模地引入。《语文建设》连续发表了著名文艺理论家、北师大教授童庆炳先生的七篇文章,涉及到文学性、文学形式与内容、文学真实、文学审美、文学文体、文学解释等文学教育的诸多概念和问题。汪政、何平在《语文教学通讯》连续开设“新课程文本解读方法系列讲座”,共十讲,阐述了现代文学批评中的理论和方法,包括社会批评、原型批评、精神分析批评、叙述学批评、语言学批评、读者反应批评、生态批评等,并在每讲之后提供了解读实例。文艺学、文学理论的研究成果被集中地、大规模地引入,从直接效用看,有助于厘清文学教学中诸多模糊认识,对文学教学发展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而更深远的意义则是推动了文学教学知识除旧布新的进程。
然而,文学教学要去魅和重构,单靠知识上的除旧布新显然是远远不够的。一方面,知识的除旧布新并不等于直接“送来”,更重要的是“拿来”,而“拿来”之后还需要课程专家、语文教师和学生代表的集体审议;另一方面,知识的除旧布新似乎并不是文学教学的本质问题。即便现在所有的文学知识都得到了更新,文学教学的课堂未必就不同于既往而出现新面貌、新气象。如果说,文学教学知识的除旧布新解决的是文学教学内容问题,那么,当务之急还要解决“为何”“何为”这些问题。“为何”,就是文学教学到底是为了什么,它的目标是什么;“何为”,就是文学教学到底该怎么做,出路在哪。不明确文学教学的目标与方向,不思考清楚文学教学的方式与方法,即便引入再多、再好的知识,最后也会因为目标与内容的不一致,内容与方法的不统一而导致文学教学重走歧途,步履维艰。
关于文学教学的目标与方法,本来就是文学教育教学研究的老话题。在本年度的研究成果中,有部分论文涉及到,虽老话重谈,却也不乏新见。这里,我们拟选取两篇有代表性的论文进行评议。
一、审美与体验:文学教学的目标
[评议论文] 李维鼎《“无用”之“用”:文学教育的尴尬与出路》,原载《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原文提要] 中小学是文学教育的黄金时段。然而,语文独立设科百余年来,文学教育不断被挤压、被异化,终于铸成今日之“文学之痛”。《百年中小学文学教育史论》深入历史现场,展开深层对话。其突出特色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慧眼察演变,诊断出语文教育发展中长期存在的二元对立情势下的“钟摆式”痼疾;二是慧心识真谛,鲜明提出了在语言主体条件下、以审美为核心的文学教育之理念与策略。
李维鼎《“无用”之“用”:文学教育的尴尬与出路》一文,是为黄耀红的博士论文《百年中小学文学教育史论》(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8月出版)所写的书评。文章着重分析了该论文的两个突出特色,其一是慧眼察演变,诊断出语文教育发展中长期存在的二元对立情势下的“钟摆式”痼疾;其二是慧心识真谛,鲜明提出了在语言主体条件下、以审美为核心的文学教育之理念与策略。其中,对第二点特色的论析颇见力度,不仅厘清了黄耀红论文对该问题的论证思路,还辨析了其中关节点的缺失,为读者阅读起到了很好的引导作用。
强调文学教学过程要重视“语言”和“审美”,这种观点本身并不能见出多少新意。关键是我们为什么要重视这些要素,为什么要把它们作为文学教学的目标。这需要一个相对严密的逻辑论证。难得的是,黄耀红的博士论文对此作了论证,李维鼎的这篇书评则不仅辨析了这个论证过程,而且还对这个论证过程的不充分之处进行了辨析与补充。
因“语言”和“审美”之纠结主要在文学语言的本体地位,这里我们不妨大致梳理一下两位作者对这一问题所进行的论证:
黄:先确认“语言本体论”,认定语言既是内容也是形式,并且以俄国形式主义理论为佐证;然后在“科学语言”、“文学语言”和“生活语言”划分基础上,正面论述“文学语言”在文学教育、乃至于语文教育中的重要性,着重引述的是王富仁的“小语文”理论,也即“各种不同学科同时也在培养着学生写作不同学科的文章的能力,而只有直观的、直感的、情感的、审美的表达方式需要在语文课上进行学习”。
李:先确认“语言本体论”,认定语言既是内容也是形式;然后在“科学语言”、“文学语言”和“生活语言”划分基础上,指出“文学语言”的个性之所在乃是其陌生化,即“打破语言的正常节奏、韵律、修辞和结构,通过强化、重叠、颠倒、浓缩、扭曲、延缓等手段,让其与人们熟悉的语言形式相疏离、相错位,产生陌生化效果”,没有陌生化语言就没有文学,由此正面论述“文学语言”在文学教育中的重要性。
这里,我们看到,两位作者都遵循先一般后特殊,即从“语言本体论”论证转换到“文学语言本体论”论证的思路,最后要得出的结论都是文学语言在文学教育教学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本体性地位,欲为文学教学是审美的教学,从“咀嚼语言”始,到“品味语言”止这一观点张本。所不同者,黄耀红强调的是语文课的独担之任——“只有直观的、直感的、情感的、审美的表达方式需要在语文课上进行学习”,分辨的是语文学科和其他学科任务之差异;而李维鼎凸显的是文学教学的独担之任——学习“打破语言的正常节奏、韵律、修辞和结构,通过强化、重叠、颠倒、浓缩、扭曲、延缓等手段,让其与人们熟悉的语言形式相疏离、相错位,产生陌生化效果”的语言,分辨的是文学教学与非文学教学任务之差异。显然,前者还不能分辨语文课中文学学习与语言学习、文章(此处为狭义,与文学相对之篇章——作者注)学习之区别,一不小心,很可能将文学泛化,最后也就等于取消了文学教学;而后者抓住了文学语言的本质特点,分辨了语文课中文学学习的独特性,理清了文学教学的基本方向。显然,真正的文学教学,是在陌生化语言教学中学会审美,陌生化语言是“审美”之充分条件,“审美”则是赏析陌生化语言之自然结果。
关于“体验”,李维鼎也有很好的论述:
文学所提供的“现实”不是“直接的现实” 而是“虚拟的现实”;“虚拟的现实”其实是作者体验的、“形象性”的生成物。因为“体验”(以身体之、以心验之)本身是感觉的、心灵的、情感的,所以文学形象诉诸读者的,就主要不是理性的“认识”,而是感性的“情感”。这样,“体验”就联系着文学创作与文学接受。作者与读者的“体验”一旦由于阅读而对接,语言欣赏开始了,审美开始了。在这样的时候,过快、过多地强调“主题思想”、强调对于作者意图的追寻、强调文学知识和技巧的介入,都可能使审美者过快地离开作品所描绘的、充满生机的、生命张扬的现实生活图画,因而冲淡情感的感受和体悟,文学审美因此而遭受破坏。
这一论述精辟指出了文学教学中“体验”之必要性和运作机制。“体验”对于文学教学而言是必要的,因为文学提供的现实是“虚拟现实”,“虚拟现实”是作者“体验”之生成物,读者要获取,同样也必须要“体验”。“体验”的过程是读者和作者通过语言的对接,当语言欣赏开始的时候,也就是体验、审美展开的时候。在文学阅读过程中,教师适度地延缓这种体验过程,让学生尽可能地不离开文学作品描绘的生机盎然、丰富多彩的生活图景,维持一种审美状态,不仅可以增强作品的感召力和感染力,还可以使学生获取更丰厚的审美意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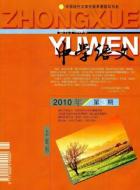
- 2009年度语文理论热点追踪(上) / 温立三
- 感悟汉语音韵之美 / 吕 雪 赵传栋
- 呼唤单元教学的涅槃(之二) / 王家伦
- 语文教师专业化素养摭谈 / 李新生
- 文学教学的去魅与重构 / 胡根林
- 中学语文教师专业发展路向探寻 / 陈元辉
- 美,何以流失? / 雷冬梅
- 关注学生心理,领悟抒情散文的美 / 黄妮妮
- 一曲和谐的赞歌 / 李爱梅
- 《春江花月夜》“四美”教学探索 / 明 智
- 说“X立方” / 朱 璇
- 开掘作文教学的人文清泉 / 魏根道
- 当艺术成为技术 / 钱春良
- 成语的二字缩略式 / 卢卓群
- “三先三后”作文法于作文教学之启示 / 张冬梅
- 把真性情带到考场作文中来 / 王小东
- “因缘”与“姻缘” / 任 艳
- 从古代议论文中学习写作技巧 / 薛 艳
- 提升语文教师的教学功力 / 杨仕威
- 妙笔巧用,风景如画 / 郭春伟
- 丢开教学的“臭脸子” / 汲安庆
- 轻轻的我走了 / 文 勇 孙绍振
- 读报,“让无力者有力” / 童县城
- 《泥人张》课堂教学实录与点评 / 余映潮 李文珍
- 从“温酒斩华雄”看“无中写有”的叙事谋略 / 杨小波
- 《氓》女主人公心理解读 / 田小华
- 苏教版的《想北平》怎么少了点“京味儿”? / 黄风雷
- 怎一个“趣”字了得 / 章国华
- “君看”还是“门前” / 夏峥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