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9年第7期
ID: 135870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9年第7期
ID: 135870
语文教学:借助“工具”渗透“人文”
◇ 欧阳芬 王家伦
20世纪末的那场语文“大讨论”中,受应试教学的株连,“工具性”成了众人口诛笔伐的对象,甚至有人认为“人文性”是语文的基本属性。而今,语文“新课标”认为“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结合,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是对那场讨论的总结。于是,“工具性”与“人文性”怎样结合就成了摆在语文教学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文道相加”“道以载文”“文以载道”是其中颇有代表性的三种意见。
一、工具性和人文性必须“融合”
无论是《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还是《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都认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结合,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但与其把它看成对学科性质的一锤定音,还不如把它视为对上世纪末关于语文教育大讨论的总结。”①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倪文锦教授一针见血地道出了语文学科特点的真谛。
关于语文“工具性”的内涵,语文是交际的工具、思维的工具、传承文化的工具早有定论;关于语文“人文性”的内涵,则诠释各异。但“工具性”与“人文性”之间的关系,就如古人所谓的“文”与“道”之间的关系,应该没有异议。
有人认为,语文课(阅读教学)就是“写作特点”和“中心意思”,令人生厌。这真令人莫名惊诧,文本(主要指记叙类和议论类的文本)的“写作特点”就是言语形式,是“工具性”的体现,即“文”的体现;“中心意思”就是言语形式负载的内容,是“人文性”的体现,即“道”的体现。语文课不讲“中心意思”和“写作特点”,那该讲什么?语文课分析“中心意思”和“写作特点”是天经地义,“写作特点”与“中心意思”之间的关系就是言语形式与言语内容之间的关系,就是“文”与“道”之间的关系。
于是,一些“文道结合”的语文课进入了我们的视野。一些语文教师设置教学目标时,第一课时的重点是使学生理解文本的“中心意思”,第二课时的重点是使学生掌握某一个“写作特点”,或者前后颠倒;对那些必须用一课时解决的文本,也是前半个课时解决“道”,后半个课时解决“文”,或者前后颠倒。他们认为,这样就是“文道结合”。可悲的是这些语文教师未曾理解“结合”的真谛,这个结合应该是水乳交融的结合,而不是简单的二元相加。这种结合,应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似的渗透,而不是“东边日出西边雨”式的简单相加。
二、借助“人文”无法掌握“工具”
为体现“新课程精神”,大量“很人文”的语文课吸引了我们的眼球。下面是笔者曾经观摩过的一堂语文课的概况,由一位教师借班执教《柳叶儿》(苏教版八年级课文)。文章讲述在三年困难时期,老百姓只能以柳叶充饥的艰难生活,表现了作者苦中作乐的情感。主要过程如下:
上课铃响,执教者就把该班原来的任课教师(一位三十余岁的女教师)和一位年近六十的资深语文教师请上讲台坐着,作为“嘉宾”。
第一环节:教师与学生讨论那个痛苦的年代,由那位资深教师介绍当年的艰苦情景。另外,执教者放了一段艰苦年代的录像。
第二环节:教师带领同学就“童心童趣,苦乐年代”进行讨论,重点是“作者写了什么苦,文中怎样体现的”和“作者写了什么乐,文中怎样体现的”。
第三环节:教师带领学生交流现代生活的苦与乐,先小组讨论,后全班交流。
这堂课,气氛较为活跃,教师如同电视节目主持人,大多时间内坐在“嘉宾”的对面,其形式不可谓不新鲜。然而,除了第二环节的一小部分与“文”直接有关外,其他环节尤其是占有三分之二时间的第一、第三环节早已变成了政治课!作为阅读对象的主体——文本,仅在第二环节让学生顺便翻了翻,其它时间内基本成了摆设。
我们知道,语文教学一方面要培养学生的读写听说能力,这是“工具性”的体现,即“文”的体现,具体为对文本写作特点的掌握;另一方面要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这是“人文性”的体现,即“道”的体现,具体为对文本中心意思的接纳。前者较为明显,后者则较为隐蔽。我们能想象授课教师的初衷,或许,他企图借助“人文”以使学生掌握“工具”,就是使学生通过对那个痛苦年代的了解,以明白文本“怎样体现”。但是,事与愿违,由于授课教师教学设计的偏差,那位资深教师的深情叙说和教学过程的安排早已吸引了学生,学生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去学习“文中怎样体现”,也就是说,学生根本没有理解文中的“道”是怎样体现的,语文课已不成为“语文”课,成了政治课。事实证明,任课教师企图通过“人文”使学生掌握“工具”的预设没有成功。
实际上,企图通过“道”来实现“文”的设想是难以成功的。当然,这里的成功指的是“语文”的成功。“如若说我们的语文是一座金字塔,那么‘人文性’就是塔尖,而作为工具性的语言文字便是塔基和塔身。”②攀登金字塔,岂能从塔尖开始!“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把语文比作一张毛皮,只能皮上附毛,绝对不能毛上附皮。
浙江师范大学王尚文教授说:“语文课程对学生进行人文教育,不能离开语文本体而必须强调渗透,只有这样,人文教育在语文课程中才有它独特的优势和价值,从而收到语文教育和人文教育相得益彰的效果,否则必将导致语文、人文两败俱伤。即使仅仅着眼于人文教育,语文教学也必须走在语文的路上。”③
从另一个角度说,虽然至今语文还没有一个公认的知识体系和能力系统,但在有事业心的语文教师心目中至少都有一个颇为幼稚颇为“山寨”的知识体系和能力系统,况且建构公认的知识体系和能力系统是任何一个语文教学工作者的任务。只有进行有序的教学活动,才可能取得成功。但是,难道语文教师应该和政治教师、思想品德教师“抢饭碗”,去建构“人文”体系吗?以无序带动无序,最后的结果只能是“无为”。
总之,“道”难以载“文”!
三、必须借助“工具”渗透“人文”
如果我们站在哲学的立场,从事物个性与共性的角度来阐释语文的性质,就可以看出:“人文性”是所有人文学科的共性之所在,“工具性”才是语文的个性之根本。在语文实际教学中必须把握住这个度,从而正确把握语文教学的目标及任务。语文必须永远姓“语”,也就是说,“工具”是语文的本分,必须借助“工具”渗透“人文”。那么,该怎样借助“工具”渗透“人文”呢?
首先,必须明白语文的教学任务。语文教学既不是汉语教学,也不是文学教学,而是“言语”教学,文学教学只是语文的一部分。所以,教学目标的设置必须以“文”为主,教学过程必须是逐步培养学生理解和运用语言文字的过程,即培养学生读写听说能力的过程;就阅读教学而言,当然是主要培养学生阅读能力的过程,具体体现为对文本写作特点的理解与把握,在这个基础上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至于领会文本的具体内容,不是终极目标。“仅仅关注课文‘说什么’,不是语文课;即使着眼于‘怎么说’,却旨在把握‘说什么’,也不是及格的语文课;只有以课文的言语形式为纲,自觉而明确地指向提高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才是真正的语文课。”④“言语形式是语文课立科之本”⑤。在语文阅读教学的过程中,阅读是一个“因文解道,因道悟文”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道”的培养是“副产品”。
其次,教学目标的设置一定要具体明确。还是以读写听说能力培养的中心环节阅读教学为例,课堂教学的目标一定要设在实处,其原则是“一课(课时)一得(文道各一)”。“文”的设置必须具体,而且能作教学后的评价;而“道”的目标设置可以也只能比较抽象。如只给一个课时教学鲁迅先生的《药》,就可抓住这篇文章的与众不同之处,设置的一对目标是“学习本文双线并行的结构”和“体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民群众的愚昧”。前者比较具体,课后可以用写作文的方式进行评价;后者较为抽象,无法测评。所以在具体教学中,只能以前者为主,在前者达标的基础上,考虑使学生对后者有所体会。事实证明,这样的教学是行之有效的。如果以后者为主,其结果必然是前后都无法达标,语文教学就成了一句空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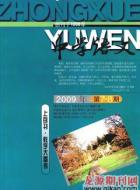
- 孙绍振漫论 / 潘新和
- 高中语文课程改革的若干要点及需要注意的问题 / 王本华
- 世纪之争:重读,还是重写? / 朱建军
- 文学定篇的特点及存在方式 / 胡根林
- 从钱梦龙“三为主”教育思想看新课程改革 / 潘冠海 陈 敏
- 语文教学:借助“工具”渗透“人文” / 欧阳芬 王家伦
- 孔子的教育之道(七) / 韦志成
- 论胡适的文学教育观 / 赵海红 张天明
- 语文课堂教学中问题情境的创设 / 何新华
- 化“综合性课程”为“语文综合性学习” / 陆 培
- 蔡元培美育思想对现代语文教育观的影响探析 / 柯华桥
- 浅谈朗读在语感教学中的作用 / 王 颖
- “文本解读”与阅读教学知识更新 / 荣维东
- 语文教学视角的地域文化 / 冯江明
- 语文阅读教学中的主问题设计 / 任明新
- 语文名师与当代语文教育范式的建构 / 陈元辉
- 中学语文课本中古典诗歌的人生智慧 / 李晓颖
- 语文教育与人的完整性建构 / 赵 蕾 曹明海
- 经世致用与诗意人生 / 吴智勇
- 与心灵接触的情感教育:语文教学的灵魂 / 赵 蕾 曹明海
- 矫正中学作文的浮躁之弊 / 石修银
- “细读”举隅 / 史绍典
- 怎样才能达到议论的深度 / 朱庆和
- 新课堂中对文本主旨解读的反思 / 茹红忠
- 为高中作文教学号脉 / 侯志林
- 语文课堂设计的文本意识 / 武立伟
- 苍凉,抑或温暖的叙说 / 高伦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