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7年第11期
ID: 356303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7年第11期
ID: 356303
文学教学的审视与反思
◇ 胡根林
(一)
【评议论文】潘新和《叶圣陶论文学鉴赏》(原载《语文建设》2006年第6期)
【原文提要】培养文学审美和鉴赏能力是语文课程标准一以贯之的要求。如何上好文学鉴赏课,提高学生的文学审美和鉴赏能力?叶圣陶所提供的关于鉴赏的含义、态度、主体、预备、途径、凭借、参考等7个方面的思想给我们提供了丰富而有益的启示。
叶圣陶先生在语文教育领域耕耘了长达76年,对我国语文教育工作中的利弊得失深切详明,所论中肯平实,涉及面广。其语文教育思想是一座丰富的矿藏,蕴藏着大量珍贵的对当代语文课改富有启迪意义的论述,需要我们深入开掘,不断探索。潘新和《叶圣陶论文学鉴赏》一文就是开掘所获得的成果。论文从鉴赏的含义、态度、主体、预备、途径、凭借、参考等7个方面对叶圣陶文学鉴赏思想进行了总结,对于一线教师上好文学鉴赏课,提高学生的文学审美和鉴赏能力提供了有益的养料。
这里我们就文中所论叶老“鉴赏的预备”做点分析。叶老认为文学鉴赏是需要一定的知识基础的。如果按知识的表现形态来分,他所提的是完整的知识概念,既包含语识(言述性知识),也包括语感(无意识知识)。
就语识而言,他有这样的阐述:“鉴赏本来是知解以上的事情,但预备知识却不可没有。一首好诗或一首好词,大概都有它的本事和历史事实,我们如果不知道它的本事和历史事实,往往不能充分领会到它的好处。……对于一篇作品,如果要好好地鉴赏,预备知识是必要的。作者的生平,作品的缘起,以及其他种种与这作品有关联的事件,最好能事先知道一些,至少也要临时翻检或询问别人。这种知识原不是鉴赏,却能做我们鉴赏上的帮助,不可轻视。”这里谈到的语识从大类上分,有关于作品的知识和关于作者的知识。作品的知识又可分为“本事”知识和“历史事实”知识。何为“本事”知识,何为“历史事实”知识,叶老没有给出下文,我们无从直接做出回答。结合语境和字面的意思,我们理解,所谓“本事”知识应该包含作品的缘起、与作品内容相关的故事(或典故的含义)等知识。(笔者按:“本事”一词源于孟子。孟子主张知人论世,强调读诗须论及本事,由本事而推求诗意,品评优劣。自此论出,遂成惯例。读《左传》《毛诗·序》可助读《诗经》,因为它们记载不少《诗经》本事。诗歌到唐一代极盛,许多诗作的产生都包含一段饶有趣味的故事。孟綮专门编著《本事诗》以搜集这些佚事逸闻。所谓“本事诗”,即以诗系事,事皆有本。由《本事诗》还孕育出另两种相关体例:宋代先后出现的诗话和诗纪事。)它强调的是与作品相关的“事”。“历史事实”知识和“本事”知识有交叉,但它更强调作品过去的情况,包含前人的评论、作品本身的遭遇等,更多是文学史的知识。而作者的知识主要指关于作者生平的知识。归结起来,叶老要求文学鉴赏必须具备的语识包含:关于作者生平的知识、关于作品缘起的知识、关于作品内容的知识,还有文学史的知识。
就语感来说,叶老这样表述:“不了解一个字和一个辞的意义和情味,单靠翻字典辞典是不够的。必须在日常生活中随时留意,得到真实的经验,对于语言文字才会有正确丰富的了解力,换句话说,对于语言文字才会有灵敏的感觉。这种感觉通常叫做‘语感’。”接着,他还专门举了夏丏尊一篇文章中的一段相关论述,论及“赤”、“夜”、“田园”、“春雨”、“新绿”、“落叶”等词在不同人心里的不同感觉。这说明,在他看来,文艺鉴赏所需的语感主要是词语感。对于句子感、语篇感或语境感,其文集中未见论述。
可以肯定,语文课程不是一门知识课程,但语文教学离不开知识教学。我们反对任何“反知识”和“去知识”的倾向。对于文学作品的教学来说,强调引导学生去读作品,去品语言,去感悟和体验,这是必要的。但不能因此而忽视了文学知识的教学。叶圣陶关于“鉴赏的预备”的论述给予我们的启示就在这里。
(二)
【评议论文】吴俊《浅析文学的形而上品质——以中学语文教材中的诗歌为例》(原载《阅读与写作》2006年第5期)
【原文提要】文学不仅要形象生动地描绘现实世界和表现人类的喜怒哀乐,而且要述说作家对世界人生的理解,乃至对人的存在的终极追问,具有形而上的哲学意味。作为文学特殊样式的诗歌,也具有这种特性。文学的形而上的品质往往溶化在具体生动的形象中,需要通过读者的再创造来加以呈现。
建国以来中学文学教育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20世纪50年代的一段时间语文课等于文学课,60年代文学教育销声匿迹,80年代文学教育复兴。目前正值语文新课改,各套中学语文新教材中文学作品的比例在加大,所占比例有的已超过60%;课程标准要求背诵的古诗文量在加大,要求课外阅读的文学作品量也在加大,这都显示了文学教学受到重视的一面。然而,在实际的课堂中,文学教学也存在某些偏至或误区,还需引起我们注意。
文学作为一种重要的艺术形式,既在形而下的层面向人们诉说人生的喜怒哀乐,具有消减世俗人生痛苦的娱乐效用,但它还是一种“重要的‘思’”(海德格尔语),是人类精神的深刻表现。亚里斯多德说:“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的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亚里斯多德:《诗学》)就是说,诗所揭示的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现实世界的本质和规律。对此,黑格尔在他的《美学》中讲述得更为形象生动。他说:“我们用哲学的方法把艺术的美和形象的每一个本质性的特征编成了一种花环。……艺术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娱乐、效用或游戏的勾当,而是要把精神从有限世界的内容和形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要使绝对真理显现和寄托于感性现象,总之,要展现真理。”因此,如果对文学作品的教学仅仅停留在读读背背,仅仅让学生自己去体验、感悟一番,那么,即便是经典的文学作品,其教学价值也会十分有限。《浅析文学的形而上品质——以中学语文教材中的诗歌为例》一文,虽名为“浅析”,所论也并非新见,但对中学语文教材中诗歌所作的形而上层面的分析,给我们的启迪却很多。它指出了当前包括诗歌教学在内的文学教学的一个普遍问题:不能深入挖掘作品的丰富意味,没有关注并分析作品背后形而上层面的意义。
分析这种缺陷造成的原因,有两个方面值得深思:
一、观念方面
大凡涉及文学教学目标的讨论,人们常有这样一个三段论:文学教育就是审美教育,审美教育就是情感教育,所以,文学教育就是情感教育。基于这种理念,文学教学的课堂上,人们就特别注重情感内容的分析,总是很详尽地分析作品通过写什么景抒发怎样的情感,或表达作者怎样的胸襟。
从理论上看,把文学教育归于审美教育,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错;但是把审美教育等同于情感教育,却有狭隘审美教育的嫌疑。审美教育是审美主体对审美客体进行感知、欣赏和评判的一种心理活动。作为一种主体性活动,有情感的参与、介入是题中应有之义,但并不是全部。一个完整的审美过程应当包括从感性到理性、从情感到知性的过程。它从感悟入手,在美感获得的初始阶段,排斥和忌讳一切理论的说教。但是,当这种自由的审美心态得到感性的满足后,就必须介入理性的思考,使之进入对审美对象理解、分析的更深层面,形成审美判断和审美评价,从而完成审美的全过程。所以,只有情感介入的审美是初级的审美,是不完整的审美;必须升华为理性审美,才是审美心理成熟的表现。长期以来,我们囿于情感教育的思维怪圈,似乎一谈文学作品背后的哲理含义或哲学意味,就是僭越,有违审美教育的本义;殊不知,只谈一个作品表达了作者什么感情或什么倾向,还只是文学审美教育的初始阶段,真正的文学审美教育还须引导学生追究作品背后形而上的对人性、人生的理解,对人存在价值的终极追问。
二、方法方面
与上述情感教育的观念相联系,人们强调对文学作品的整体感悟,极力否定文学教学中的文本分析,以为作品一分析就破坏了形象的完整性,就变得枯燥,失去情感的丰富性。这种看法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们对文学及文学解读方式认识上的进步。从文学文本来看,它具有模糊性、多义性、丰富性和复杂性等特点,很难只通过分析来达成理解。但问题是,文学作品的教学不分析行不行?任何文本细读都是分析,任何内容阐释都是分析。如果没有教师的分析,学生的阅读只基于一种自身的经验,那么,课内的文学教学和课外学生自读作品又有什么分别?学生对文本的鉴赏能力又怎么提高?
另外,单就诗歌教学而论,现代诗歌,不管是国外还是国内,都和浪漫主义所提倡的抒情性相悖,有种知性强化的特征。如文中提到的狄金森的《篱笆那边》,表达了作者对人类既本真又充满疑虑的两重性认识;还有像里尔克的《豹》,借对笼中困兽的观照,从哲学高度把握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与生命异化的痛苦;瓦雷里的《海滨墓园》、艾略特的《荒原》都是对时间、永恒与生存等超验问题的冥思。受西方现代派诗人的启悟,许多中国现代主义诗篇,也都做了同样的知性思考,如顾城的《远和近》、梁小斌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等等“朦胧诗派”、现代派诗人的作品。文中提到的韩东《山民》和海子的《秋》就是典型的知性作品。对于知性作品,如果不品味音节的嘹亮或嘶哑,不咀嚼字词句的丰富意味,不分析意象和意象背后所指,单从整体上去把握作品,不要谈深刻理解,就是能读懂就很不容易。
当然,我们这里不是有意去强调分析,而是说,对于文学教学,分析不仅是一种重要的方法,而且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过程。不加分析地否定分析方法对文学教学的意义,显然是很荒谬的。实际情况是,我们不能不要分析,关键是我们怎么分析。当代著名学者王元化先生在《论知性的分析方法》一文中,提出从知性过渡到理性,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克服知性分析方法所形成的片面性和抽象性,恢复事物的丰富性和具体性,达到多样的统一。他所说的“知性”,其实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抽象的“理性”,他称为“稀薄”的抽象。而他说的“理性”,却是并不脱离感性、与感性血肉同躯的一种理性。知性不能掌握美,但理性可以。在对文学作品整体感悟的情况下,只有通过理性的分析,才能真正理解作品,理解作品背后深刻的意蕴。那些一概否定分析的文学教学,才不太有可能引导学生发现美、掌握美。
(三)
【评议论文】郑晓刚《从分析到隐喻——诗歌教学范式的转型》(原载《语文教学通讯》2006年第10期)
【原文提要】诗歌语言是种隐喻语言。隐喻空间是学习主体“感知、体验、想象和理解”的空间,是充分个性化的空间,同时也是充分“过程化”的空间。隐喻视野下的诗歌教学就是要引导学生在解读“隐喻”的过程中,凭借诗歌语言隐喻空间,调整自我的认知和情感结构,为语文个性化学习奠定基础。
诗歌是文学作品中最为特殊的一类,其特殊首先体现在语言上。一般语言和诗歌语言都要受所属语言规则的约束。对一般语言而言,它所受的约束越多,所传达内容的信息量可能就越少;但诗歌语言却不这样,它所受约束越多(如字数、押韵和节奏),所传达的内容却可能越丰富。因为在诗中,所有的语言因素因为相互结合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结构,因而任何语言因素(包括所有外在形式因素)都可能产生意义。
索绪尔认为,语言由两个实体或两个互不相关的现实存在构成,即“能指”与“所指。“能指”指发出来的声音,“所指”指事物的意义。一个单字(单词)只有通过它与所在的同一种语言中的其他单字(单词)发生关系,才能具有它自己的意义,语言的形式体系正是由诸种因素建立起来的关系的总合。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应该是一种“构成”或“关系”,而非实体。乔姆斯基进一步指出:词在每种语言中的不同意义要根据它们所属的不同的对比系统而定。具体到诗来讲,诗区别于散文(广义的散文即非韵文)首先在于它所独有的格律与音韵等,它们为声音实体做出了规定,但对于所指并没有功能上的影响。因此,诗的“言语”(个别性传达行为)与“语言”(公共传达行为)应当是同构的,但其间存在美学意义上的差异,原因在于诗的言语从外部被赋予了有美学功能的纯声音装饰。诗有声音上的“乐感”,即使不求意义,光凭它也能带来怡悦,尽管这种“乐感”效果在诗中显然并不是唯一的最重要的因素,但却绝不可忽略。
除了语音层面(我们称之为“诗韵”的那些东西)的特殊性以外,语义的层面——词汇与语法也使诗获得了自身的独立性。诗在总体上总是显出一种普遍的常规特征,诗人们似乎原初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使信息载体(如物象)的可理解性变得暖昧不清。其中,“隐喻”是使普通语言转换成为诗歌语言的重要手段。普通语言和诗歌语言尽管是异质的,但其语式的内部结构却是完全一致的。“人悲伤”(名词联结形容词)与“思想哭泣”(名词联结形容词)的语式结构完全相同。这样看来,诗的隐喻所否定的“常规”主要是“所指”的规定性。诗否定日常思维的惯性(定势),并在语言结构内部通过对其所指关系的调整而达到了另一种肯定。
从上面两方面分析看,诗歌是通过语音与语义两个层面上的特殊性而获得其文体独立性的。因此,郑晓刚《从分析到隐喻——诗歌教学范式的转型》一文提出“诗歌语言是一种隐喻语言”,强调通过对隐喻的解读来发展人格的教学设计取向,是有其深刻性的。其意义主要是让学生在诗歌学习中通过审美体验去实现个性化发展。但由此也引申出值得商榷的两点内容:其一隐喻是诗歌语言的特征还是理解诗歌语言的手段?其二离开分析,一味强调隐喻,真能实现学生个性发展吗?
先分析第一个问题。我们前面谈到,诗歌之为诗歌,隐喻是其重要方式。诗歌通过隐喻而使语言超脱日常生活,并使所指暧昧不清,走出日常思维的惯性,实现诗人情感的独特表达。以此看来,隐喻显然是诗歌语言不同于日常语言的突出特征。那么,隐喻有没有可能同时成为理解诗歌语言的手段呢?诚如《从分析到隐喻》一文所指:“隐喻是以喻体和本体之间的相似性为基础的意义转移。通过喻体和本体的相似性表达本体无法表达的含义,从而生成新意义。”也就是说,要理解诗歌,理解其中本体的丰富意蕴,关键是要理解喻体。比如读“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要读出一种复杂的愁绪和生命的沧桑,非得对“杨柳”和“雨雪”这两个意象的内涵以及《诗经》广泛使用的比兴手法作一了解,否则,即便诗读百遍,也未必真能读出些什么。而让学生理解意象的内涵和比兴手法,所采用的基本方法是分析而非隐喻。更直接地说,通过隐喻来让学生理解以隐喻为特征的诗歌,前提是学生对喻体有充分的了解。但实际的情况是,进入我们语文教材的诗歌,其意象多有其经典性,这种经典性包含着复杂性和丰富性,需要教师的讲解和分析。这意味着,作为教学文本的某首诗如果有什么可教,这可教性很大程度上就体现为教师的讲解和分析。离开教师的讲解和分析,一味让学生体验、感受,这是学生自学就能完成的事,何须教师在课堂中循循善诱?一句话,隐喻不能成为诗歌教学的方式,至少不是主要方式。
再讨论第二个问题。这里先指出《从分析到隐喻》一文标题中的含混之处。就诗歌教学而言,与分析方法对应的似乎是体验(包含感受、理解、体验和想象等心理活动)方法而非隐喻方法。隐喻作为日常语言转化为诗歌语言的一种手段,它是一种艺术方法,而非教学方法。所以,更准确的表达应该是“从分析到体验”。其次,有必要谈谈分析和体验的关系。分析和体验的教学主体各有侧重,如分析侧重教师教,体验侧重学生学,这里暂且不作详细分析。我们关注的是,分析和体验的教学关系。语文新课改以来,我们看到不少论述这两者关系的文章,多数把它们置于非此即彼,水火不容的对立面来看待(郑晓刚《从分析到隐喻》一文也是如此,认为从分析到隐喻是诗歌教学范式的转型),这是一种误解。就像任何教师教的过程必然包含学生学的过程一样,分析的过程也必然包含体验的过程。很难想象,真正的诗歌分析,可以离开主体的体验。反过来也一样。任何体验的过程也必然包含分析的过程。只有体验没有分析的教学同样是不可想象的。那种囫囵吞枣的诗歌教学,那种除了诵读还是诵读所谓整体感知的教学,其效率是需要检讨的。其实,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把两者放在对立的位置看。就教学的基本流程看,分析和体验不过是其中两个重要环节。可以先分析后体验,也可以先体验后分析。分析中体验,体验中分析,这也符合一般读者读诗的流程。当然,在文学教学(包含诗歌教学)中,人们一片声地反对分析,从教学现状来看,并不是毫无道理。目前的语文课堂中,太多的机械的、生硬的、肢解式的分析,这种分析导致的标准化理解大大限制了文学应有的心灵空间,束缚了学生的想象力。但是,一种错误的分析方法并不就代表分析方法本身,否定错误的分析方法不能就此否定分析方法本身。真正的诗歌教学,总是需要分析的,不管是语音、结构和语义层的纵向分析,还是比较分析(如教余光中的《乡愁》,可以把这首诗和诗人同样以“乡愁”为主题的《乡愁四韵》比,也可以把它和席慕蓉的《乡愁》一诗比;甚至可以在古今中外更广的时空中,把“乡愁”作为人类普遍的情感,作一文学史的梳理)。只强调主体体验,强调整体感悟的诗歌教学,不见得真能让学生体验到什么,感悟到什么。在我看来,《从分析到隐喻》一文所举的探索性课例的教学片段(《苏轼婉约词赏析》)并非如文章所倡导的学生体验的结果,倒完全有可能是教师引导学生深入细致分析和领会诗歌之后的创举。
[作者通联:上海师范大学学科教育研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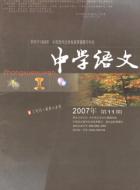
- “八面来风” / 史绍典
- 语文教育——开放学生的心胸 / 秦训刚
- 语文课程生态分析及其对策 / 杨邦俊
- “文本研习”“问题探讨”“活动体验”内涵界定 / 应慈军 林忠港
- 文学教学的审视与反思 / 胡根林
- 追寻诗意的课堂 / 张正耀
- 阅读教学应营造理性生命课堂 / 陈万清
- 采访苏武,我是苏武,我说苏武 / 葛福安
- 让阅读从理解走向创造 / 周 钰
- 让乡土文化资源与写作训练有机整合 / 杨继利
- 作文教学面临的困境与应对策略 / 王小春
- 自由诗之写作技巧 / 张兴武
- 一曲不朽的“女德”颂歌 / 刘 祥
- 穿越心灵之河的女子 / 冯迎道
- 从“发微”谈《剃光头发微》的构思 / 郑义广
- 背景、文本与拓展 / 吴宁亚
- 精心预设,有效生成 / 王 芳
- 课堂质疑中的教师行为策略研究 / 茹红忠
- 用“主问题形式”教《〈论语〉选读》 / 钱玲红
- 刍议语境中的词汇运用 / 王良圣
- 激活文言文课堂教学方法浅谈 / 赵长河
- “登录”、“登陆”补义 / 应学凤
- 形形色色的“~门”事件 / 谢政伟
- 谈谈词语的形象色彩 / 惠新猛
- 鲲鹏与“二虫”,谁更逍遥? / 董 鸥
- “歌台暖响”怎么解? / 刘党桦
- 《短歌行》探珠 / 罗祖学
- 领悟词句,离经辨志 / 徐先国
- “天”生我材必有 / 郭振海
- 新材料作文的审题立意 / 杨洪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