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研
教研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9年第7期
ID: 135872
中学语文·教师版 2009年第7期
ID: 135872
论胡适的文学教育观
◇ 赵海红 张天明
胡适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学者和教育家。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他首倡白话文,大力推进国语改革,这些都广为人知。实际上,胡适先生在文学教育方面也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提升了文学教育在中小学语文教育中的地位,准确定位了文学教育的目标,对于文学教育的途径也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这些观点和见解是我们现在从事文学教育研究和实践的重要资源。然而到目前为止,未见有人对胡适的文学教育观进行探讨。笔者试图在此对其进行较为详细的梳理,从而为我国当前的语文教育改革提供历史的借鉴。
一、文学教育的地位:语文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在看来,文学教育是中小学语文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此乃理所当然,但中国教育从隋唐起到民国初期都是以四书五经为核心,很难有文学教育的地位。吕叔湘就曾指出文学教育“自从唐宋以经术取士,至明清衍为八股,完全成为文字游戏,与文艺相去太远了。”①清末明初,近代中小学语文单独设科,语文教育依然缺乏文学教育的内容。文学教育重新回到中小学语文教育中,与胡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1922年,胡适发表《中学国文的教授》,首先提出“人人有懂得一点古文文学的机会”②,将文学教育的目标纳入到中小学语文教育之中。值得一提的是,《中学国文的教授》原是一次大会上的演讲词,在《新青年》上发表后,借助胡适和《新青年》在知识界的知名度,该文的观点受到普遍重视并引起了广泛讨论,对提升文学教育在语文教育中的地位有着先导作用。
对提升文学教育地位起关键作用的是一系列语文课程标准的颁布,而胡适是这一系列语文课程标准颁布过程中的核心人物。他不但直接组织、协调课程改革方案,还直接参与起草了一系列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包括1923年《高级中学公共必修的国语课程纲要》、《高级中学第一组必修的特设国文课程纲要(二)中国文学史引论》以及1929年《高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前两者被作为语文课程标准直接颁布。1929年颁布的课程标准与他起草的草案相比,只是被强行地加上了一些党政的内容,并加大了古文的比重,其它基本保持不变。1923年颁布的《高级中学公共必修的国语课程纲要》课程目标第三条“欣赏中国文学名著的能力”③,1923年颁布的《高级中学第一组必修的特设国文课程纲要(二)中国文学史引论》课程目标第三条“引起学生研究文学的趣味”④,1929年正式颁布的课程标准中有“继续培养学生欣赏中国文学名著的能力”⑤。而且,1929年语文课程标准是国民政府此后修订所有语文课程标准的蓝本。在这些课程标准中,文学教育都被列入语文课程标准中,使得文学教育被以国家教育政策的形式加以推广和实施,加强和巩固了文学教育在语文教育中地位。
二、文学教育的目标:培养学生欣赏文学的能力
文学教育的教学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文学知识教学,包括了文学理论知识教学和文学史知识教学;二是文学创作教学,包括了文学写作心智训练和文学写作技巧训练;三是文学欣赏教学。在文学教学中,这三者的关系并不容易处理,往往因文学教育理念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教学倾向。胡适在语文课程标准中提出,语文教育应培养学生“欣赏中国文学名著的能力”,“引起学生研究文学的趣味”,“继续培养学生欣赏中国文学名著的能力”,明确突出了文学欣赏的中心地位。同时,胡适削减了纯文学知识的教学,他在《中学国文的教授》中提出中学国文课程中应删去原有的“文学史”课程:“文学史更不能存在。不先懂得一点文学,就读文学史,记得许多李益,李颀,老杜,小李的名字,却不知道他们的著作,有什么用处?”⑥“文学史”课程以文学知识传授为主,删除文学史课程直接降低了文学知识在文学教育中的地位。对于文学创作,胡适并非如梁启超所指责的那样要把学生都培养成文学家,他认为文学创作是中学生多种写作方式中的一种,他把中学作文分为翻译、读书笔记、游览参观记载、专题研究、文学作品等。在写作中胡适认为关键是养成不同的习惯要求,如读书的笔记应“注重养成怀疑,不苟且、不潦草的习惯”;“一切作文的训练,切忌‘大题小做’,务必养成‘小题大做’的习惯”等等⑦。并没有对文学创作的技巧等方面有明确的教学要求。可见,胡适主张中小学文学教育以文学欣赏为主,以文学创作和文学知识为辅,符合中小学文学教育的实际需求,较好地处理了三者间的关系。
胡适主张文学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学生文学欣赏的能力,实质上就是着眼于对学生进行审美教育,从更深层次而言,这是一种自我意识的教育,主要源于胡适对文学启蒙价值的认识和对塑造学生健全人格的追求,他意识到“凡世界有永久价值之文学,皆尝有大影响于世道人心者也”⑧。他想借助文学这股影响人心的强大力量,把人从蒙昧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他掀起文学革命,致力于创作新文学,构建新文学体系,试图将为人生为自由为独立而创作的新文学,扎根于新一代国民的心底,然后再使他们萌生出自由、民主、独立的坚定信念,成为拯救中国的“不亡之因”。这是可行的策略,正如卡西尔所说,“艺术是一条通向自由的道路,是人类心智解放的过程。”⑨文学是作者主体生命的再现,这一内在属性天然地决定了它可以净化和提升学生的精神世界,可以把学生从外部世界挤向内心,赶进内心,让人从新的视角重新审视自己,从而成为一个独立、自主、人格健全的生命个体。当时中国正处于救亡图存的时代,一部分知识分子将目光转向了文化救国,教育救国,为拯救中国造就一批独立自主的新生力量已经成了时代的迫切需求。当文学教育自有的启蒙价值和时代的救国诉求紧密地相结合时,就更加凸显了通过文学教育培养新国民的时代使命和价值。
三、文学教育的途径:扩大文学作品的选材范围
文学教育要在中小学语文教育中真正占有一席之地,要实现提高学生欣赏文学能力的目标,语文课程标准的颁布只是先声,要想真正落实,胡适认为扩大文学作品的选材范围是不可缺少的一步。
由于中国文学教育的长期缺失,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没有进入教学领域,胡适尖锐地指出两千多年来学生学习古文,但古文的读本就限于那么屈指可数的几本,可谓中国之一大奇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自宋以来,直到最近世,竟无大改动,此亦是一件教育史实。”⑩胡适的批判是到位的,单调的读本只能培养出呆滞的学生,远不能达到培养学生健全人格的要求。胡适提出“宋人的白话小词,元人的白话小令,明清人的白话小说,都是绝好的文学读物。”{11}他认为近代的梁任公、康长素、严几道、章太炎等人的散文,都可选读。林琴南、朱树人、蔡孑民、吴稚晖的作品也可列入选材的范围,还认为章行严一派的古文最适宜于中学模范近古文之用。他批判了中国文人长期以来对新文体的轻视,认为中小学文学教育应该打破文体的局限。因为每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体,在那一个时代里它也许是最好的表达方式。但时过境迁,这一文体就有了自身无法改变的不足,于是又有了新的更适合表情达意的文体产生。所以选材就应该选择可以代表时代的文体。这就大大扩大了文学教材的选择范围,其中以小说体裁的入选为最突出的代表。因为小说一向是最被轻视的一种文体,用胡适的话说,“从前的人,把词看作‘诗余’,已瞧不上眼了;小曲和杂剧更不足道了。至于‘小说’,更受轻视了。”{12}小说能进入学生的阅读视野,这意味着各种文学体裁都进入了选择的范畴,大大扩大了文学教材的选择范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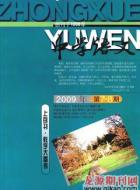
- 孙绍振漫论 / 潘新和
- 高中语文课程改革的若干要点及需要注意的问题 / 王本华
- 世纪之争:重读,还是重写? / 朱建军
- 文学定篇的特点及存在方式 / 胡根林
- 从钱梦龙“三为主”教育思想看新课程改革 / 潘冠海 陈 敏
- 语文教学:借助“工具”渗透“人文” / 欧阳芬 王家伦
- 孔子的教育之道(七) / 韦志成
- 论胡适的文学教育观 / 赵海红 张天明
- 语文课堂教学中问题情境的创设 / 何新华
- 化“综合性课程”为“语文综合性学习” / 陆 培
- 蔡元培美育思想对现代语文教育观的影响探析 / 柯华桥
- 浅谈朗读在语感教学中的作用 / 王 颖
- “文本解读”与阅读教学知识更新 / 荣维东
- 语文教学视角的地域文化 / 冯江明
- 语文阅读教学中的主问题设计 / 任明新
- 语文名师与当代语文教育范式的建构 / 陈元辉
- 中学语文课本中古典诗歌的人生智慧 / 李晓颖
- 语文教育与人的完整性建构 / 赵 蕾 曹明海
- 经世致用与诗意人生 / 吴智勇
- 与心灵接触的情感教育:语文教学的灵魂 / 赵 蕾 曹明海
- 矫正中学作文的浮躁之弊 / 石修银
- “细读”举隅 / 史绍典
- 怎样才能达到议论的深度 / 朱庆和
- 新课堂中对文本主旨解读的反思 / 茹红忠
- 为高中作文教学号脉 / 侯志林
- 语文课堂设计的文本意识 / 武立伟
- 苍凉,抑或温暖的叙说 / 高伦强
